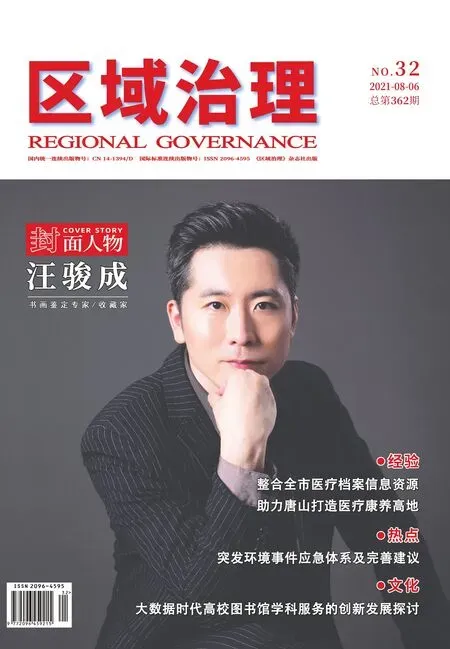論民法典中侵權(quán)責(zé)任編的權(quán)益保護(hù)范圍
四川省社會(huì)科學(xué)院 熊鶯
一、侵權(quán)法一般條款的立法變遷:從《侵權(quán)責(zé)任法》第2條到《民法典》第1164條
根據(jù)我國2009年頒布的《侵權(quán)責(zé)任法》第2條的規(guī)定:“侵害民事權(quán)益,應(yīng)當(dāng)依照本法承擔(dān)侵權(quán)責(zé)任。本法所稱民事權(quán)益,包括生命權(quán)、健康權(quán)、姓名權(quán)、名譽(yù)權(quán)、榮譽(yù)權(quán)、肖像權(quán)、隱私權(quán)、婚姻自主權(quán)、監(jiān)護(hù)權(quán)、所有權(quán)、用益物權(quán)、擔(dān)保物權(quán)、著作權(quán)、專利權(quán)、商標(biāo)專用權(quán)、發(fā)現(xiàn)權(quán)、股權(quán)、繼承權(quán)等人身、財(cái)產(chǎn)權(quán)益。”由此可見,2009年的《侵權(quán)責(zé)任法》對于侵權(quán)法保護(hù)的客體所采用的立法方式是概括加列舉式的。而2020年頒布實(shí)施的《民法典》第1164條規(guī)定:“本編調(diào)整因侵害民事權(quán)益產(chǎn)生的民事關(guān)系。”可知《民法典》對于侵權(quán)法保護(hù)的客體采取的立法方式屬于純粹列舉式的立法方式。應(yīng)當(dāng)說,《民法典》第1164條作為侵權(quán)法的一般條款相較于《侵權(quán)責(zé)任法》是有一定的進(jìn)步,的。首先,在《侵權(quán)責(zé)任法》第2條的規(guī)定中,其所列舉的權(quán)利并沒有一定的層次性,例如,生命權(quán)、健康權(quán)屬于具體的權(quán)利,但是該法條中列舉的用益物權(quán)、擔(dān)保物權(quán)卻屬于權(quán)利類型,并且所有的列舉項(xiàng)該法條均用頓號(hào)并列,表明了該法條的層次不清晰。其次,雖然《侵權(quán)責(zé)任法》第2條用了“等”字表明權(quán)益范圍的廣泛性,但是從文義解釋的視角看,“等”字所囊括的其他權(quán)益應(yīng)當(dāng)與前述所列舉的生命權(quán)、健康權(quán)等權(quán)利具有內(nèi)在一致性,因此反而限制了權(quán)益解釋的空間。《民法典》并沒有直接引用侵權(quán)責(zé)任法的規(guī)定,而是直接采用了概括式規(guī)定,避免了列舉法可能帶來的權(quán)益保護(hù)的不周延性,并且從體系解釋的角度來看,《民法典》在第一編總則部分的第五章對民事權(quán)利進(jìn)行了專章規(guī)定,因此1164條中的民事權(quán)益自然包括了總則第五章所列舉的權(quán)利,避免了在法條中對權(quán)利專門列舉帶來的繁瑣。
二、對“權(quán)益”一詞的解釋
從字面意思來看,可將“權(quán)益”一詞拆分為權(quán)力和利益,在民法這一特定視域下,侵權(quán)法中的權(quán)益可以理解為民事權(quán)利和民事法益。為何不是民事權(quán)利和民事利益?當(dāng)“權(quán)益”作為法律條款中的詞語時(shí),理應(yīng)將其放入法律視域下,因此將“利益”一詞上升解釋為“法益”更加符合標(biāo)準(zhǔn)。首先,對于民事權(quán)利的理解不需過多贅述,“權(quán)利”一詞已經(jīng)成為法律視野中的常用語,即已經(jīng)上升為法律明確保護(hù)的客體,當(dāng)然可以成為侵權(quán)責(zé)任編保護(hù)的對象,重點(diǎn)在于利益是否能夠上升為侵權(quán)責(zé)任編保護(hù)的對象。對于這一問題需要取舍決定,如果將所有的利益都作為侵權(quán)責(zé)任編的保護(hù)客體,勢必會(huì)導(dǎo)致法益的泛化,也不利于維護(hù)法律的權(quán)威性和穩(wěn)定性,因此,只能將能夠上升為法益的利益作為侵權(quán)責(zé)任編保護(hù)的對象。那么,何為法益?應(yīng)當(dāng)將法益解釋為“能夠獲得法律保護(hù)的利益”。這里需要注意一個(gè)問題,那就是因?yàn)槲覈浅晌姆▏遥瑳]有成文法對于需要保護(hù)的法益作出專門性的規(guī)定,對于民事權(quán)益受保護(hù),也只是在《民法典》侵權(quán)責(zé)任編中做了概括性規(guī)定,因此在具體的法益是否能夠受法律保護(hù)的問題上,需要法官在個(gè)案中依據(jù)自由裁量權(quán)來確定。
三、《民法典》侵權(quán)責(zé)任編保護(hù)的權(quán)利
《民法典》第1164條明確規(guī)定民事權(quán)益是其保護(hù)對象并采用概括式立法模式。根據(jù)《民法典》總則中第五章對于民事權(quán)利的規(guī)定,民事權(quán)利在分類上大體分為財(cái)產(chǎn)權(quán)利和人身權(quán)利。并且有些權(quán)利兼具人身與財(cái)產(chǎn)的雙重屬性,具有人身權(quán)和財(cái)產(chǎn)權(quán)的共同特點(diǎn)。典型的比如著作權(quán),著作權(quán)中的署名權(quán)就是人身性質(zhì)的權(quán)利,因其不可轉(zhuǎn)讓并且專屬于某個(gè)人,但是,出租權(quán)、表演權(quán)等即屬于財(cái)產(chǎn)性質(zhì)的權(quán)利。首先是人身權(quán)。人身權(quán)因其所具有的特點(diǎn),是與財(cái)產(chǎn)權(quán)對應(yīng)的,由此也被稱為“人身非財(cái)產(chǎn)權(quán)”。人身權(quán)與人身不可以分離,并且人身權(quán)沒有直接的經(jīng)濟(jì)利益。人身權(quán)又分為人格權(quán)與身份權(quán)。人格權(quán)包括姓名權(quán)、名譽(yù)權(quán)、肖像權(quán)等權(quán)利,被法律所確認(rèn)的人格權(quán)和民事主體的存在和消亡是緊密聯(lián)系的,身體、人格等作為民事主體存在的必要條件,均與人格權(quán)相聯(lián)系。權(quán)利主體因?yàn)橐欢ǖ馁Y格、一定的地位等會(huì)產(chǎn)生身份權(quán),身份權(quán)是依存于當(dāng)事人之間的各種身份關(guān)系而存在的權(quán)利,所以身份權(quán)也自然而然地隨著當(dāng)事人的身份關(guān)系消亡而消亡,身份權(quán)的主要類型包括親權(quán)、監(jiān)護(hù)權(quán)等。我國公民和法人的人身關(guān)系在法律上得以體現(xiàn)和反映,這就是人身權(quán)的產(chǎn)生基礎(chǔ)。人身權(quán)具有不可讓與的性質(zhì),所以人身權(quán)不具有財(cái)產(chǎn)內(nèi)容,人身權(quán)被侵害時(shí),救濟(jì)的方式一般是非財(cái)產(chǎn)的方式。其次是財(cái)產(chǎn)權(quán),財(cái)產(chǎn)權(quán)因?yàn)榕c人身權(quán)相對稱而具有物質(zhì)財(cái)富的內(nèi)容,物權(quán)、債權(quán)、知識(shí)產(chǎn)權(quán)都屬于財(cái)產(chǎn)權(quán),財(cái)產(chǎn)權(quán)還存在于婚姻和勞動(dòng)關(guān)系中,比如贍養(yǎng)費(fèi)、撫養(yǎng)費(fèi)、撫育費(fèi)等由于家庭成員之間的關(guān)系產(chǎn)生的財(cái)產(chǎn)權(quán),勞動(dòng)報(bào)酬、退休金、撫恤金等基于勞動(dòng)關(guān)系產(chǎn)生的權(quán)利。財(cái)產(chǎn)權(quán)在法律上表現(xiàn)為一定的社會(huì)物質(zhì)資料占有、支配、流通和分配。最后是其他合法權(quán)益,即人身權(quán)和財(cái)產(chǎn)權(quán)之外尚存在的其他合法權(quán)益,也屬于《民法典》侵權(quán)責(zé)任編的保護(hù)范圍。
(一)此種權(quán)利需為私法上的權(quán)利
將法律劃分為公法和私法是內(nèi)地法系對于法律的劃分法,調(diào)整國家與普通公民、組織之間關(guān)系以及國家機(jī)關(guān)及其組成人員之間關(guān)系的法律為公法。調(diào)整普通公民、組織之間關(guān)系的法律為私法。侵權(quán)責(zé)任編和物權(quán)等編的性質(zhì)是不同的,物權(quán)編調(diào)整的是直接的社會(huì)關(guān)系,即第一層民事法律關(guān)系。而侵權(quán)責(zé)任編是對第一層民事法律關(guān)系的再調(diào)整,是用來救濟(jì)民事權(quán)利的。因?yàn)榍謾?quán)責(zé)任編是對第一層民事法律關(guān)系的救濟(jì),所以平等主體之間的民事權(quán)力和利益才能被其所保護(hù),故其保護(hù)的權(quán)益只能是純私法領(lǐng)域的權(quán)益,而不是公法領(lǐng)域的權(quán)益。但有一個(gè)例外,那就是憲法上的權(quán)益被具體化,就有可能得到《民法典》侵權(quán)責(zé)任編的保護(hù)。而純粹公法上的權(quán)利是不受《民法典》侵權(quán)責(zé)任編保護(hù)的,比如受教育權(quán)等。
(二)具有侵權(quán)責(zé)任編上的可救濟(jì)性
我國《民法典》第1164條對于侵權(quán)責(zé)任編的保護(hù)范圍作了概括式規(guī)定,不同于2009年《侵權(quán)責(zé)任法》的列舉式加兜底式規(guī)定,并且在《民法典》總則部分的第五章專章對民事權(quán)利作了規(guī)定,可以說是進(jìn)一步明確了其保護(hù)范圍,但是在實(shí)踐中仍然存在很多案件,引發(fā)我們思考現(xiàn)實(shí)生活中真實(shí)發(fā)生的并由原告提出的各種具體的利益是否應(yīng)該上升為法益被法律所保護(hù)。例如,在山東的“親吻權(quán)”案中,被告吳某駕駛汽車撞傷了陶女士,導(dǎo)致她的上唇撕裂。由于嘴唇受傷,導(dǎo)致陶女士在與其丈夫親吻時(shí)心理有了障礙,甚至?xí)械娇謶郑c丈夫的情感交流也因此受到嚴(yán)重阻礙。陶某委托律師向法院起訴,要求吳某賠償他的身體權(quán)、親吻權(quán)、健康權(quán)以及財(cái)產(chǎn)權(quán)的損失。原告提出的親吻權(quán)在中國現(xiàn)行法律、司法解釋和行政法規(guī)中沒有相關(guān)規(guī)定,能否得到救濟(jì)?這就要看其是否具有侵權(quán)法上的可救濟(jì)性了。由于對身體權(quán)和健康權(quán)的法律保護(hù)已經(jīng)涵蓋了親吻的利益,所以這里的親吻權(quán)不具有侵權(quán)法上的可救濟(jì)性,不值得救濟(jì)。
(三)權(quán)利法定不是權(quán)利意定
我們應(yīng)當(dāng)承認(rèn),從社會(huì)生活的復(fù)雜和多樣性發(fā)展的趨勢來看,侵權(quán)責(zé)任編保護(hù)的權(quán)益范圍呈現(xiàn)不斷擴(kuò)張的趨勢,在比較法研究中也很熱門,因?yàn)樯鐣?huì)生活的復(fù)雜性致使人們無時(shí)無刻都面臨著遭受侵害的風(fēng)險(xiǎn),且風(fēng)險(xiǎn)和損害類型也在隨之發(fā)展變化,其擴(kuò)張趨勢大致表現(xiàn)為:從主要保護(hù)物權(quán)向保護(hù)人身權(quán)、人格權(quán)等范圍擴(kuò)張。傳統(tǒng)侵權(quán)責(zé)任的保護(hù)對象主要為物權(quán),但是隨著民事權(quán)利不斷豐富發(fā)展,侵權(quán)責(zé)任的保護(hù)范圍也漸漸從主要保護(hù)物權(quán)到保護(hù)知識(shí)產(chǎn)權(quán)等權(quán)利擴(kuò)張,甚至擴(kuò)大到對債權(quán)等相對權(quán)的保護(hù)上。為了防止權(quán)益的無限擴(kuò)大化,應(yīng)當(dāng)明確權(quán)利始終是法定的,不能是意定的,盡管侵權(quán)責(zé)任的保護(hù)范圍呈現(xiàn)不斷擴(kuò)張的趨勢,但是一定要防止“權(quán)利意定”,在堅(jiān)持“權(quán)利法定”的基礎(chǔ)上對利益進(jìn)行衡量,作出公正判決。
四、《民法典》侵權(quán)責(zé)任編保護(hù)的法益
民法調(diào)整各種社會(huì)生活關(guān)系,并形成各種民事法律關(guān)系,因此社會(huì)中的利益問題也就是權(quán)利和義務(wù)的問題。民法是權(quán)利契約,建立民法中各種制度的目的是界定和保護(hù)各種私權(quán)性質(zhì)的利益。保護(hù)私權(quán)是民法體系構(gòu)造的核心,在私法發(fā)達(dá)的社會(huì)中,人們對于自己私益的保護(hù)方法,是把自己的利益在私權(quán)體系中準(zhǔn)確定位。但是利益關(guān)系在社會(huì)生活中顯得雜亂繁多,不可能所有社會(huì)生活中的利益關(guān)系都能納入法律調(diào)整范圍。但是,如若有一部分的社會(huì)生活關(guān)系不在民法調(diào)整范圍內(nèi),此時(shí)就會(huì)產(chǎn)生一個(gè)問題:各種社會(huì)生活關(guān)系紛繁復(fù)雜,是否未納入權(quán)利體系的社會(huì)生活關(guān)系就完全不受法律保護(hù)?法律對于社會(huì)生活利益關(guān)系的保護(hù)是否局限于私權(quán)層次?民法法益的問題就此生發(fā)了:民法是否只是就人類社會(huì)生活依憑之權(quán)利部分加以規(guī)范?當(dāng)然不是。相較于事實(shí)問題來說,法律問題的范圍是更狹小的。如果只有權(quán)利的層次才受民法保護(hù),那么社會(huì)生活的穩(wěn)定以及法的正義、公平等目標(biāo)都將不能實(shí)現(xiàn),因此,民法應(yīng)當(dāng)是一個(gè)開放的體系,并且隨著社會(huì)的不斷發(fā)展,更多的利益將會(huì)被納入民法的保護(hù)范圍。民法中的法益同時(shí)存在著法律因素和社會(huì)因素,在法律因素上,法典的核心地位與權(quán)利的定型化為我國內(nèi)地法系所強(qiáng)調(diào),其為民法法益確立了基本的法律前提,但是由于社會(huì)生活始終處于不斷變化中,各種利益關(guān)系不可能被清晰明確對歸入法典,此即民法法益存在的社會(huì)基礎(chǔ)。和民法法益最接近的概念是民事權(quán)利,二者的對象都是市民生活中的一定利益,在內(nèi)地法系民法中,某種利益能否獲得民法保護(hù)的關(guān)鍵在于其是否納入了成文法典中,但是內(nèi)地法系權(quán)利定型化的做法與復(fù)雜的社會(huì)現(xiàn)實(shí)間始終存在著矛盾,因此民法在價(jià)值目標(biāo)和法律技術(shù)上必須進(jìn)行變革,因而民法從近代民法向現(xiàn)代民法不斷邁進(jìn)。現(xiàn)代民法的調(diào)整保護(hù)范圍不再局限于定型化的民事權(quán)利,民事法益也逐漸納入民法的保護(hù)范圍內(nèi),當(dāng)然,對于法益的保護(hù)程度始終不及民事權(quán)利。因?yàn)榉ㄒ嬷皇抢嬖诿穹ㄉ祥g接和模糊的反映,法益還只是處于權(quán)利保護(hù)的“邊緣地帶”而已。
將權(quán)利分為應(yīng)然權(quán)利和實(shí)然權(quán)利是對權(quán)力的一種劃分方法。應(yīng)然權(quán)利是一種預(yù)備性的權(quán)利,是權(quán)利主體應(yīng)該享有的或應(yīng)該獲得的。實(shí)然權(quán)力則是指權(quán)利主體真正實(shí)際享有或是獲得的權(quán)利。在此還應(yīng)討論一個(gè)法定權(quán)利,法定權(quán)利即規(guī)定在規(guī)范性法律文件中的權(quán)利主體應(yīng)該享有的或獲得的權(quán)利。但法定權(quán)利不一定是實(shí)然權(quán)利。因?yàn)橐?guī)定在法律文件中的權(quán)利不一定能真正在現(xiàn)實(shí)生活中為權(quán)利主體享有或獲得。法益存在于權(quán)利之外,是法律主體享有的受法律保護(hù)的利益。《民法典》第1164條中民事權(quán)益中的利益,若能歸于法益的范疇,是應(yīng)該保護(hù)的。利益的范圍很寬泛,如果要讓某種特定利益有被法律保護(hù)的必要性,需要通過權(quán)衡,但是人的理性和社會(huì)生活的復(fù)雜性始終存在著一定的矛盾,此種矛盾性在立法者身上也是存在的,因此概括性立法策略就有運(yùn)用的空間,此種方式可以對將來需要保護(hù)或現(xiàn)在需要保護(hù)的但未能上升為權(quán)利的法益進(jìn)行保護(hù),對立法者的理性缺陷進(jìn)行了彌補(bǔ)。社會(huì)法的觀念認(rèn)為法益是應(yīng)予保護(hù)的利益,因此得出法益是一種應(yīng)然權(quán)利的結(jié)論。
五、結(jié)論
《民法典》第1164條明確了侵權(quán)責(zé)任編的保護(hù)范圍,該條通過對民事權(quán)利進(jìn)行概括性規(guī)定,并輔以《民法典》總則編中的第五章對于民事權(quán)利的專章規(guī)定,肯定了物權(quán)、債權(quán)、知識(shí)產(chǎn)權(quán)、股權(quán)等受《民法典》保護(hù)的民事權(quán)利納入侵權(quán)責(zé)任編的保護(hù)范圍,有利于權(quán)利宣示,也有利于法官的司法適用,同時(shí)有利于《民法典》侵權(quán)責(zé)任編適應(yīng)社會(huì)發(fā)展變遷,實(shí)現(xiàn)對民事權(quán)益的全面保護(hù)。但是在社會(huì)實(shí)踐中,對于侵權(quán)責(zé)任編保護(hù)的民事權(quán)益范圍仍然存在許多分歧。本文通過對相關(guān)概念的簡單辨析,試圖進(jìn)一步明確“權(quán)益”的范圍邊界。對于社會(huì)生活中的各種利益是否上升為法益的判斷,對于法官的判案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筆者認(rèn)為,對于權(quán)利的保護(hù)應(yīng)適用于《民法典》侵權(quán)責(zé)任編的一般規(guī)定,并且保護(hù)程度應(yīng)當(dāng)略高于對于法益的保護(hù)。而對于利益的保護(hù),首先,法官應(yīng)當(dāng)綜合考慮社會(huì)各種因素,并參照其他民事法律規(guī)范是否有零散規(guī)定,結(jié)合對其保護(hù)的必要性和緊迫性的判斷,確定該利益到底是否值得保護(hù),若值得保護(hù),其保護(hù)程度也值得考慮,一般利益的保護(hù)程度應(yīng)略低于對法定權(quán)利的保護(h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