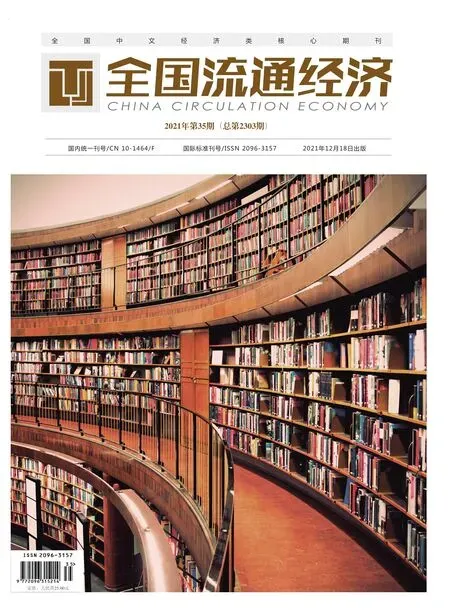業績期望差距研究綜述與未來展望
趙紅霞
(暨南大學,廣東 廣州 510632)
一、引言
戰略領域的學者往往討論企業的成功決定因素,研究企業戰略選擇的驅動因素,然而現實狀況中,企業并不總是成功的,組織衰退乃至失敗的現象隨處可見。中國作為新型經濟體正面臨正式和非正式游戲規則的根本性和全面性變化即 “制度轉換”[1],逐步完善的制度環境和快速發展市場經濟使得企業生存成長的環境充滿不確定性與復雜性[2]。在動蕩的市場環境下,大多數企業的經營情況會產生波動。企業對自身經營業績和經驗的總結將影響其后續的生產經營活動,特別是企業戰略變革選擇。企業通過什么途徑分析經營業績,如何解讀業績期望差距,采取什么措施應對業績反饋是個值得探究的話題。
二、業績期望差距的概念和測量
1.概念
由于企業是目標導向型組織而組織決策者是有限理性的[3],即會簡化地對某一業績維度設定一個滿意性的業績期望水平作為評估標準。業績期望水平由目標(標準)和比較點(參照點)組成[4],可以是“組織過去的目標,組織過去的業績,以及其他類似組織的過去的業績”[3]。業績期望差距是企業將企業實際業績與期望水平進行比較而發現的差值大小。企業管理者會對業績期望差距進行解讀和評價[5,6],影響后續的決策行為。當差值為正時,即企業當年的實際業績達到甚至超出了業績期望水平,業績期望差距被稱為“業績期望順差”。在這種情況下,企業管理者往往會認為前一階段的經營是成功的。反之,當差值為負,即企業實際業績低于業績期望水平,業績期望差距被稱為“業績期望落差”。此時,企業管理者會認為前一階段是失敗的。面對不同的業績期望差距企業決策者會采取各種戰略決策以響應。
2.測量
業績期望差距的實質是將業績期望水平與企業實際業績相減的到的差值。測量的關鍵在于衡量業績的財務指標的選取以及業績期望水平的選取。
學者通常選取總資產回報率(ROA)來衡量企業的業績,因為其容易被各利益相關者獲取,并且可以充分的評價企業的盈利能力。也有學者采取銷售利潤率(ROS)或者凈資產收益率(ROE)作為企業業績的衡量指標。
業績期望水平是決策者認為滿意的最小結果,是感知成功和失敗之間的邊界線[7],包含了關于公司未來狀態的不同信息,這些期望將塑造決策者對公司未來保持優于或低于業績的可能性的認知形象[8],但是參照物的選擇會引起偏差。根據不同的參照點,主流研究將業績期望差距分為歷史業績期望差距與行業業績期望差距。歷史業績期望水平是基于時間維度,根據企業往年的實際業績記錄進行預測,其預測方式是將企業前一期的實際業績和前一期的業績期望按不同比例加權,采用遞歸度量公式進行計算: Ai,t-1=β1Pi,t-2+ (1-β1) Ai,t-2其中,Ai,t-1表示企業在t-1年的歷史業績期望,Pi,t-2表示企業在t-2年的實際業績。Ai,0為i企業在第0期的歷史業績期望,由第 0 期的實際業績代替。β1表示在計算當年業績期望時,上一年的實際業績與上一年的預期業績之間的權重,取值范圍為[0,1]。大多數學者選擇β1=0.6 對歷史業績期望進行測量,也有學者考慮到不同權重的影響,選擇β1=0.5等權重進行穩健性檢驗。歷史業績期望差距(Hi,t-1)是指i企業在第t-1期的實際業績水平Pi,t-1與i企業第t-1期的歷史業績期望水平Ai,t-1的差值,計算公式為:Hi,t-1= Pi,t-1-Ai,t-1。為了方便后續研究,國內外學者通常會采取構建截尾的連續性變量的方法來度量歷史業績期望落差。具體做法為將企業的實際業績與歷史業績期望水平相減,如果實際業績低于歷史業績期望,即Pi,t-1-Ai,t-1<0時,則判斷為企業處于期望落差狀態,取I1=1;如果實際業績高于于歷史業績期望,即Pi,t-1-Ai,t-1≥0 時,則判斷為企業處于期望順差狀態,取I1=0 。令歷史業績期望落差HPFi,t-1=|I1(Pi,t-1-Ai,t-1)|,即將歷史業績期望落差取絕對值,而高于歷史業績期望的取值為 0[8,9]。
行業業績期望則基于社會比較維度,主要根據同行業企業業績的平均水平來進行預測,即通常采用行業業績的中位數或者平均業績測量[10,11],體現企業在行業中的地位及競爭力。計算公式為: IEi,t-1= β2IPi,t-2+ (1-β2)IEi,t-2,其中,IEi,t-1表示企業在t-1年的行業業績期望,IPi,t-2表示企業在t-2年的行業實際業績中位值。β2表示權重,取值范圍為[0,1]。行業業績預期差距(Si,t-1)則表示企業當年的實際業績Pi,t-1與行業預期業績IEi,t-1之間的差值,計算公式為:Si,t-1= Pi,t-1-IEi,t-1,同樣可進行截尾來度量行業業績期望落差。
三、業績期望差距與組織響應的關系
企業管理者會根據業績期望差距的大小進行分析,業績反饋所帶來的信息解讀會有助于解釋企業前一階段的經營狀況和表現,并可能改變風險偏好和搜索行為,進而影響組織決策行為[12],即體現為“業績反饋——組織響應”的決策模型。
1.理論視角
關于組織如何響應業績期望差距,學者往往結合不同的理論視角加以解讀。大致分為以下幾種情況:(1)問題搜尋視角:企業通過評估和解讀業績期望差距,發現企業存在的問題并利用這些信息來開展搜索行為以找到解決方案[13]。(2)風險承擔視角:前景理論預測決策者在收益領域(高于業績期望水平)規避風險,在損失領域(低于業績期望水平)尋求風險[14]。“威脅—剛性”理論則認為業績低于業績期望水平對于企業組織而言是一種威脅。決策者感知威脅,可能感到壓力和焦慮,進一步縮小認知,全力應對威脅,表現出信息處理限制以及控制限制即更加機械化和集中化的,缺乏靈活性的僵化狀態。即企業在期望落差狀態的決策趨于風險規避,不太愿意改變和嘗試,更依賴于常規和行為的一致性[15]。(3)管理者特征視角:高階理論指出當企業實際業績高于業績期望水平時,“成功”狀態容易催生高管自負,進而增強組織的積極響應行為[16]。此外,根據注意力基礎觀的觀點,企業的戰略決策者的理性是有限的,企業的業績差距會影響組織或管理者注意力的配置方向,進而影響制定戰略行為和戰略決策[17,18]。當企業可能會失敗時,決策者將他們的注意力從期望轉移到生存上。(4)組織學習視角:組織學習理論的一個中心思想是,組織從經驗中學習,并根據其業績對實踐、戰略和結構做出改變[19]。決策者的學習和行動模式取決于他們組織的實際業績與他們的業績期望水平的不同程度。高于業績期望水平的滿意結果促進從早期經驗中提煉汲取教訓,業績未達到期望時則強調學習他人的經驗[20]。
2.組織響應行為類型
國內外學者在期望差距與企業行為決策關系研究方面主要關注戰略調整、創新創業活動等多種企業戰略決策。連燕玲等(2014)指出業績期望落差與實施戰略調整的程度呈正相關。賀小剛等發現家族企業將隨著業績期望差距的增大而選擇進行創新[10]。大多數學者認為在期望順差下,企業會減少創新投入和變革行為。而在期望落差越大,企業挽救業績的動機越強,創新投入越多[21],但有部分學者則認為落差會導致企業決策者承受更強的心理壓力和資源困境,產生威脅剛性最終導致創新投入減少。還有學者認為期望落差和創新投入并非線性關系[22]。
3.業績期望差距異質性
目前國內外多數學者直接探討業績期望差距對企業戰略決策的影響,把兩類期望業績囊括在業績評估標準,并未做嚴格區分。部分學者強調單一業績期望差距的影響,如Kacperczyk等(2015)認為組織在同行業競爭處于下風時,冒險性變革增加[14]。另一部分學者將歷史期望和行業期望分別賦權而組合成為總體的期望[23]。只有少部分學者注意并區分了歷史業績期望差距與行業期望差距的異質性[12,24,25]。如Baum和Dahlin表明,在美國貨運鐵路行業,行業業績反饋比歷史業績反饋在降低事故成本方面具有更強的作用[20]。
4.多維度業績期望差距與組織響應的關系
隨著研究的深入,業績期望差距的各類特征,如業績期望差距的強度、多目標以及持續時間等受到國內外學者們的關注。
業績期望差距的強度指企業實際業績與目標期望水平業績的差值大小,是學術界研究的主要課題之一。其對于企業的決策行為的影響關系,學術界尚存在不同的看法。大部分的學者認為業績期望差距的強度與組織響應存在線性相關關系。特別是當企業業績低于業績期望水平時,管理層會趨向于實施戰略變革等風險性較大的措施來改善企業當前的業績[26]。區別于簡單的線性關系,Ref與Shapira則指出業績期望差距與進入新市場存在倒U型關系;國內吳炯等學者聚焦家族企業的代際傳承,發現傳承前的業績期望差距與傳承后創新活動間存在顯著的倒U型關系[27]。
早期關于業績期望差距的研究中,僅僅簡化的關注單一目標的目標期望水平。而廣泛的企業實踐表明,企業管理者的決策過程更為復雜,存在多目標的業績反饋機制。梁肖梅等學者將其總結為獨立模型、注意力轉換模型、自我增強模型和關聯模型[6]。管理者會設立多個目標,如利潤率目標、擴大規模目標、長期業績目標和短期業績目標等。這些目標可能相互獨立,同時影響企業的決策行為。管理者也可能根據企業實際情況對多個目標排出優先級,將注意力優先放在某一目標上,特別是當企業瀕臨破產時會更關注生存目標。另一方面,管理者自身的認知偏差也會影響其選擇性得強調某一目標[28]。此外,企業不同的目標可能也會存在關聯,如企業擴大規模可能也會對企業利潤率有促進作用。
現有研究也關注到了業績期望差距的時間特征,考察了企業的業績期望差距持續時間、業績的變動性等。李溪等(2018)學者發現持續時間較長的業績期望落差會促進企業進行創新性探索[21]。也有學者指出持續的業績期望落差會增加管理者的風險承擔傾向。此外,還有學者關注一段時間內業績的變動性。在業績期望順差狀態,更高的業績變動性會使管理者認為當前較高的業績是不穩定的;反之,在業績不如意時,更高的業績變動性則會強化其在解讀業績反饋時的自我增強意識。
四、總結和未來研究方向
隨著對業績期望差距概念和特征的認識不斷深化,近年來國外對于業績期望差距的研究已取得較為豐富的學術成果。與蓬勃發展的實踐相比,國內學術界對于業績期望差距的理論探索才剛剛起步,可提升空間很大。未來研究者可以參考以下方向:
第一,更深入的揭示基于不同參照點的業績期望差距之間的異質性。大多數研究通常將歷史業績期望差距和行業業績期望差距視為理論和經驗上一致的[29]——對戰略決策具有相似的影響,鮮有嚴格區分不同類型的業績期望差距帶來的影響。由于業績期望差距涉及過程機制復雜、應用情境多樣。不同的業績信息來源,經過不同的認知和組織過程過濾,會相應地影響公司的行為和選擇。未來研究可以更多地識別基于不同參照點的業績期望差距對于組織響應行為的內在性質差異。
第二,拓展研究情景。企業的經營發展是一個動態的過程,對于業績期望差距的解讀也與組織內外部環境、行業等情景緊密聯系。未來學者可以關注家族企業情景中經濟目標與非經濟目標的沖突與協調,在家族成員追求和維護社會情感財富的情景下,業績期望差距對于家族企業管理者決策行為的作用路徑是否有改變?在國有企業具有提升利潤率、保障就業率等多個目標的情況下探究業績反饋機制也是個有趣的話題。此外,不確定性的外部環境也會對企業管理者的決策行為產生影響。如近兩年席卷全球的新冠肺炎疫情給大多數企業帶來強烈沖擊,不少企業經營受阻,甚至走上破產清算的道路。未來研究者可以關注在疫情危機下經營困境的企業基于業績反饋信息又會如何決策。
第三,拓展研究方法。基于數據可得性,現有研究大多數使用二手數據進行實證研究,特別是上市公司數據使用較多。未來研究可以通過實地走訪和問卷調查等方式獲得一手數據進一步探索。此外,實證檢驗是將組織響應視為業績反饋的既定事實,雖然現有研究者通過將解釋變量滯后一期來減少反向因果等內生性問題,但關于業績期望差距對企業決策行為的作用路徑仍尚不清晰。未來研究可以通過匹配具體恰當的案例,運用扎根等案例分析方法來打開業績期望差距到組織響應過程的黑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