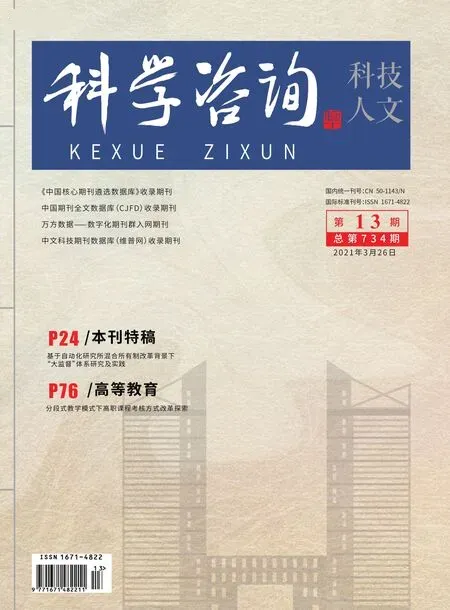超聲造影在前列腺癌診斷中的研究進展
張尚彬 劉 川
(重慶醫科大學附屬第二醫院 重慶 400010)
在2018全球癌癥篩查中,在全世界男性中,前列腺癌發病率在所有惡性腫瘤中位于第二,也是第五大癌癥死亡原因。美國的前列腺癌的發病率甚至已經超過肺癌,一舉成為嚴重危害男性健康的第一位腫瘤[1]。在我國,前列腺癌男性惡性腫瘤的發病率位于第6位,雖然發病率低于歐美國家,但近年來發病率呈現迅速上升趨勢[2],已成為男性泌尿系統中發病率最高的惡性腫瘤[3],而且我國前列腺癌患者檢出時前列腺癌疾病分期分級與西方發達國家存在較大差別。在西方發達國家,新發現的前列腺癌患者中91%的患者為臨床局限型前列腺癌,可行根治性手術,在接受標準治療后預后好,5年生存率接近100%。而在我國,新發的前列腺癌患者中在確診時僅有30%為臨床局限性患者,其余均為局部晚期或廣泛轉移的患者,這些患者無法接受前列腺癌根治性手術治療,預后較差,導致我國前列腺癌死亡率明顯高于西方國家。因此,提高前列腺癌早期檢出率尤為重要[4]。
當前,確診前列腺癌的金標準是病理學診斷。對可疑PCa患者首選經直腸超聲(Transrectal ultrasound,TRUS)引導下系統穿刺活檢。盡管前列腺穿刺活檢是在超聲引導下進行的,但通常無法確定實際的腫瘤進行活檢。單純系統穿刺可能會錯過或降級很大一部分前列腺癌[5],常規系統穿刺無法避免地會存在一定假陰性率,高達22%-47%的PCa在初次穿刺中漏診[6]。前列腺系統穿刺活檢是診斷前列腺癌的最常用方法,但其隨機性可能導致對早期前列腺癌的診斷不足,隨著醫學影像學的不斷發展,加入在影像學指導下的靶向穿刺活檢策略可能提供更實用的解決方案。多種新型影像技術如超聲造影、實時彈性技術、前列腺組織掃描、經會陰粒子植入模板引導定位活檢、基于多參數MRI引導下的靶向技術等開始應用于臨床[7]。
多項研究表明,基于多參數磁共振成像(MRI)引導下的靶向穿刺成為檢測前列腺癌的一種可選擇方法。MRI上的可疑病變可以在MRI指導下或MRI/US融合指導下準確采樣[8][9][10]。但是,MRI引導的靶向活檢是一種昂貴且耗時的解決方案,仍然僅限于少數幾個醫療機構使用,還需要特定設備和軟件,無法大范圍推廣。此外,并非所有患者都適合進行MRI成像。金屬植入物,起搏器或幽閉恐懼癥是MRI的禁忌癥。
近年來,隨著超聲影像學的發展,超聲造影技術已廣泛應用于臨床多種器官的研究,CEUS是一種新型檢查技術,它能有效地顯示細小和低速血流,還可動態觀察血流動力學的變化,顯示和區分正常組織以及病變組織的血流灌注情況,并引導前列腺穿刺。近年來,超聲造影技術(CEUS)的高特異性及高敏感性在多種臨床實質性腫瘤的檢測中已被證實[11][12][13],國內外均有文章表明超聲造影下前列腺靶向穿刺活檢單獨或聯合系統穿刺活檢可提高前列腺癌檢出率,本文結合最新文獻,將超聲造影在前列腺癌診斷中的現狀及進展作以下綜述。
一、超聲造影原理及造影劑
超聲造影能夠很好地評價前列腺癌的血管構成、腫瘤形態及與周圍組織結構的關系,增強超聲對腫瘤微血管的顯示能力,是近年來具有里程碑式意義的超聲技術,也是目前的研究熱點之一[14]。超聲造影通過造影劑和生理鹽水混合震蕩后會產生大量的微泡,微泡在外周靜脈、毛細血管內停留,與紅細胞充分接觸后,形成許多血液氣泡界面,通過對超聲波的反射、吸收、折射等效果,可以使得微泡所在部位的回升信號加強,從而改變回聲的信號,使腫瘤凸顯出來,加強檢測效果[15][16]。前列腺惡性腫瘤的生長需要豐富的毛細血管來供應養分,前列腺惡性腫瘤為了獲取更多的營養物質,會促進外周和內部產生新生血管,從而增加血流灌注,超聲造影使得增加的血流顯影,從而與正常組織區分出來[17]。
造影劑對超聲造影而言至關重要,造影劑是有外殼包裹的微氣泡。第一代超聲造影劑的微氣泡內主要成分為空氣(如Albunex、Levovist等),缺點是比較容易破裂,持續時間短,效果較差,目前大部分已被淘汰;第二代超聲造影劑的微氣泡成分主要為惰性氣體(如Sono Vue),其穩定性相對較好,在血液循環中維持時間較長,效果較好,目前使用最為廣泛。
二、超聲造影的影像學特點
前列腺癌的二維超聲圖像多種多樣,且一種超聲圖像可能與多種病變結果一致,從而使得二維超聲影像診斷前列腺癌的準確率較低,前列腺惡性腫瘤的生長需要豐富的毛細血管來供應養分,前列腺惡性腫瘤為了獲取更多的營養物質,會促進外周和內部產生新生血管,從而增加血流灌注,超聲造影使得增加的血流顯影,從而與正常組織區分出來。
周琦[18]等人的研究發現,30例經病理證實的前列腺癌患者和50例前列腺增生患者術前均進行了超聲造影檢查,在前列腺癌患者中,超聲造影圖像表現為強化不均勻,病灶部位強化明顯加快,在時間-強度曲線上表現為上升支陡直,呈快速上升型;而在前列腺增生患者中,超聲造影呈均勻強化,上升支較為低平。前列腺癌和前列腺增生患者的造影圖像在基礎強度間方面表現類似,但是在始增時間、峰值強度、達峰時間、強度變化以及單位時間內灌注強度變化率方面有較大差異。這表明超聲造影可以區分前列腺癌和前列腺增生病灶的強化特征,從而在前列腺癌病灶的診斷中起著重要作用。
陳惠莉[19]等人研究表明,經直腸前列腺CEUS,從繪制TIC曲線分析中發現內腺造影增強早于外腺,且峰值強度高;增生結節中內外腺未見明顯差異,內、外腺良性分別表現為與周圍內、外腺實質同步灌注的均勻增強模式,癌結節在外腺表現為增強強度高于內腺前列腺組織及周圍外腺前列腺組織,且與外腺組織相比呈快增強、快消退特點。
孫小林[20]等人對26例前列腺癌患者進行超聲造影檢查,總共34個結節中發現有30個結節為前列腺癌,其余4個為增生結節,30個前列腺癌結節中有25個呈高增強,明顯高于正常組織。超聲造影能夠對前列腺癌內病灶的血流情況進行評估,引導穿刺活檢,超聲造影圖像表現為前列腺內腺早于外腺開始增強,且達峰值強度的時間也較短,增強強度較高。經直腸超聲造影可以鑒別前列腺癌和前列腺增生組織并判定病變范圍,從而提高前列腺穿刺的準確率。
綜合當前的研究,總結前列腺的CEUS表現有如下特點:1.超聲造影下前列腺組織增強及消退均早于周圍組織表現為“快進快出”“高增強”的病灶;2.超聲造影血流信號異常區域增多,有的呈高流速、高阻力血流,或觀察到不對稱血管結構;3.癌灶的時間一強度曲線下面積大于正常前列腺組織。
三、超聲造影在前列腺癌穿刺中的應用
1989年,Hodge等首次報道了經直腸超聲(TRUS)引導下6針前列腺穿刺活檢術,6針系統穿刺法的假陰性率比較高,漏診率最多可達20%,而穿刺針數越多漏診率越低。為了提高陽性診斷率,最簡單的辦法是不斷增加穿刺針數,隨后出現8、10、12、13、14、18、20甚至22-24針的飽和穿刺技術。但隨著穿刺針數的增加,術后感染、血尿、便血等并發癥發生的概率升高。目前,前列腺癌診斷多采用10+X針或12+X針的系統飽和穿刺法。研究表明,10針以上穿刺的診斷陽性率明顯高于10針以下的穿刺,但隨著穿刺針數的增加,患者的痛苦也隨之增加。因此,尋找一種采用較少穿刺針數但可獲得較高陽性率的方法非常重要。而CEUS可以滿足這個要求。
Halpern等人在301例患者中比較了CEUS靶向活檢與系統活檢。CEUS引導的活檢發現癌癥的可能性是系統活檢的2倍。但是,靶向活檢漏診了20%的癌癥,通過系統活檢即可發現。他們得出結論,盡管CEUS引導下的活檢對癌的檢出率更高,但仍需要系統的活檢[21]。Sano等使用CEUS對41例患者進行了12針系統和靶向活檢。他們還表明,以CEUS定位的活檢發現的癌癥明顯更多[22]。
Frauscher等人將對CEUS靶向穿刺與系統穿刺進行了比較。在CEUS組中,從造影劑增強區域進行了5次或更少的活檢,在系統穿刺組中,進行了10次活檢。在230例患者中,檢出PCa的有69例(占30%),CEUS的有56例(占24.4%),系統穿刺的有52例(占22.6%)。他們得出的結論是,當使用CEUS引導的活檢時,用較少的活檢可以獲得相同的檢測率[23]。在2005年,Pelzer等人執行了CEUS和系統穿刺的組合方法來研究對PCa檢測的影響。他們的結果顯示檢出率與較少的活檢相當[24]。以上研究得知,CEUS可以提高前列腺癌檢出率,減少穿刺針數,但系統穿刺的作用仍不可忽略。
伍卓強等研究顯示CEUS單針陽性率及Gleason評分高于常規系統穿刺組患者[25];黃志鵬等人研究發現相較于系統穿刺,CEUS能獲得更高有臨床意義的前列腺癌檢出率(38%vs26%),且陽性針數率更高(44%vs18%)[26];Zhu Yunkai等人研究表明,在一項納入1024名可疑前列腺癌患者的前瞻性隊列研究中,在378名PCa患者中,有326名(86.2%,326/378)被診斷出有臨床意義PCa。CEUS的有臨床意義PCa檢測率為28.7%(294/1024),高于SB(25.3%,259/1024,P=0.000)[27],Mitterberger等人在1776名男性隊列中報道,CEUS的總體PCa檢測率顯著高于系統穿刺[28]。這些研究表明,CEUS不僅在前列腺癌檢出率方面明顯優于系統穿刺,同時在有臨床意義前列腺癌檢出率方面也更有優勢。
四、結束語
在我國,前列腺癌是危害老年男性身體健康的常見惡性腫瘤,且發病率逐年提升,大部分患者發現疾病時已有局部晚期或廣泛轉移,因此,提高前列腺癌早期檢出率尤為重要。
隨著超聲影像學的不斷發展,結合影像學、圖像處理、人工智能等技術的超聲造影下靶向穿刺技術以其高精確性、較少的穿刺針數和較低術后并發癥越來越受到重視,將在前列腺惡性腫瘤的診斷中將發揮越來越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