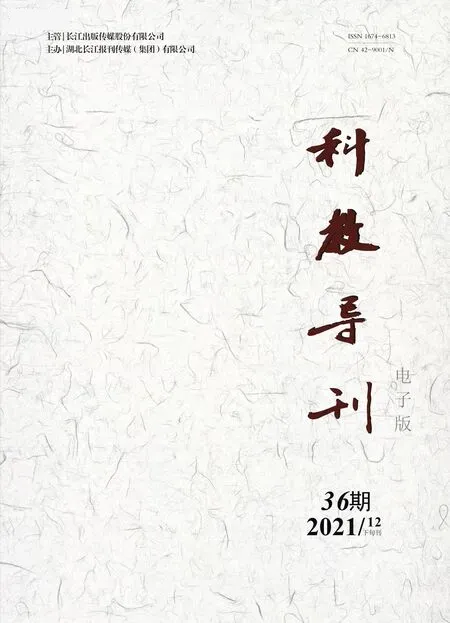對話視野下體育院校師生關系淺析
王曉一
(吉林體育學院 吉林·長春 130022)
對話是探索人類所面對的各種沖突原因的一種方法,且對話能夠幫助我們解決眾多社會問題。事實上,當個體嘗試去發現他人的觀點和視野,個體的想法將變得更有智慧,從而避免與他人的沖突。哈貝馬斯指出,關注對話并非為了在爭論中取勝,而是在于提升個人的理解與福祉。被譽為對話理論之父的馬丁·布伯首先提出了“我與你”的對話關系,布伯認為,“我”和“你”是一個整體,不能被分開,沒有“我”便沒有“你”。“我”和“你”共存。在“我與你”的對話關系中包含著尊重、確認(confirmation)和包容(inclusion)。
伽達默爾(1993)相信當雙方積極促進達成“真相”時,對話便會發生。在本研究中,對話有著雙重含義:首先,它是指師生在課堂教學中的互動交談;其次,它包含了對話理論中“對話”一詞的精神和內涵。基于這種觀點,當教師旨在促進學生通過深度思考來解決問題時,對話便會發生。然后,學生能夠通過參與對話建構知識,同時感知到來自教師的平等信任、尊重與合作。
師生關系是師生在教育教學中形成的關系,它包括師生地位、角色、對彼此的態度、行為等的交往特征。為實現完成某種教學任務的目的,師生關系直接影響教學結果。
體育院校中的師生關系包含兩個方面:一方面,教師和學生的地位形成了教學活動中的角色關系;另一方面,教師和學生之間的交往互動形成了一種心理關系。這兩種關系緊密相連。但是心理交往關系優先于角色關系,成為師生關系的基礎。這兩種關系構成了師生關系的特殊性。
基于對話視野下的師生關系應包含教師和學生在課堂的對話行為中所形成的社會關系、人際關系和心理關系。對話行為是課堂教學的主要媒介和首要互動行為。因此研究對話行為可以作為研究師生關系的切入點和基礎。
1 教師存在的意義
高校教師因其所服務的群體,導致其在教育目的和目標上與初等教育工作者的區別。高校教師應該成為激發他人潛能的人,教師能夠通過教學活動促進學生思考,幫助學生挖掘其內在的潛能,并在學生迷茫時給予指導并賦能。教師在與學生交往互動中應保持其獨特的教學和人際交往風格,但在教學這一特定場域中,無論何種風格,都應有助于實現教育的終極目標。
印度哲學家克里希那穆提認為教育的意義在于通過教育使個體既不恐懼,也不執著于安全感。這樣,個體便能夠自由的探索、觀察和學習,迎接挑戰,從而變得有智慧。使學生成為“終身運動者、問題解決者、責任擔當者和優雅生活者”。
2 教練型教師
相比于傳統意義上的教師,或者理論教師,筆者更愿意將體育院校的教師稱之為教練型教師。教練存在的前提是相信人的潛能,只有這樣,選手才能進步和成長。教練可以通過對話幫助選手找到自我的狀態,并且鼓勵他們自己去承擔成長的責任。
當代對話理論之父馬丁·布伯認為:“一名真正的教師最成功的時候,是當他沒有有意識地嘗試去教,而是自發地在其生活中行動出來,這樣他便贏得了學生的信任,當學生獲得了自信,他抵抗被教育的力量便發生了一種神奇的改變——他接受教育者作為一個人。他覺得自己可以相信這個人......在想要影響他之前首先要接受他。”馬丁·布伯的理論對教育領域有非常重大的貢獻,他一再強調:“教育領域完全是對話性的”。
布伯認為,教育者需要不斷的提醒自己,每個人將其與生俱來的存在帶入現實中,對于個體、教育、甚至整個生命來說,都通過對話而變得富有意義。布伯強調:“教育中的關系是一種純粹的對話關系”。
布伯的理論在運動領域也同樣適用。教練的目的是幫助選手建立覺察感,目標和自信。而不是替對方解決問題、羞辱他或是給他壓力。
教練需要讓選手意識到自己才是責任主體,自己才是需要解決在運動中遇到的各種問題的人。教練需要做到懸置。懸置是質性研究方法中的概念,指研究者在研究開始前不能像量化研究那樣進行任何的猜想、假設或者預判。因為一旦猜想、假設或者預判,就會對選手產生引導性行為,責任主體便又轉移到教練身上了。那么,教練需要做什么呢?教練首先需要提問,讓選手覺知,從而產生更多的感受和思考。在對話中,教練才能真正的意識到選手也是一個完完整整的人,才能去接納他、尊重他,并且信任他。這時,便形成了互惠互利的師生關系。
3 體育院校師生對話的特點
筆者通過大量的田野式觀察和訪談,獲得了體育院校課堂中師生對話的第一手材料,通過質性研究方法,對所收集的材料進行編碼、整理和分析,總結出如下結果。
3.1 霸權主義對話與建構主義對話
在本研究中,霸權主義對話表現為兩類:發出指令和話語壟斷。這一特征主要表現為教師開展“講座式”教學,積極開展知識傾倒。在這種情況下只有教師發聲,甚至有時會學生參與課堂對話。教師的關注點多傾向于教學內容和教學進度,以及課堂紀律。然而,當教師采用霸權主義對話(單邊對話)的時候,其往往期待學生能夠成為安靜的觀眾或沉默的溝通者。
在本研究中,建構主義對話主要表現為理解、適當的權威、共情和增能等四個方面。這一特征表現為師生之間開展親和的對話行為。在建構主義的對話行為中,教師能夠理解學生作為學習者,因此其知識系統呈現碎片化而非有系統的體系;通過適當的權威對學生展開積極的,有建設性的指導;共情體現為教師能夠有彈性的掌握課堂節奏,并鼓勵以學生為中心,以學生為主導的知識探索;最重要的是在建構主義對話行為中,教師能夠激勵學生,喚醒其內在的潛能。
3.2 話語權
在霸權主義的對話中,教師占話語的主導地位,控制對話過程,壓抑學生的對話需求。而在建構主義的對話中,教師通過贊賞思考行為、積極肯定和反饋,以及任務式教學和基于問題的教學方法,鼓勵學生發起對話行為。
在教學過程中有一個非常重要的點,即教師不能一味給予,應適當向學生“索取”。這種“索取”能夠為學生賦能,提升學生在教學活動中的價值感和自我效能。伯姆(1996)認為當學生展現出探尋的精神時,對話有助于促進學生的這一品質。因為對話的過程不是為了獲得答案,而是為了挑戰思維。
3.3 機械式對話與交誼舞式對話
機械式對話表現為,在對話過程中,教師與學生只進行較淺層次的對話,如強調紀律、知識點,給予指令或批評。總之,教師與學生的情感連接較少,學生也無法從教師那里獲得較有建設性的信息。
交誼舞式的對話表現為在對話過程中,時而教師主導,時而學生主導,師生通過富有意義的對話和鏈接來完成教學活動。
3.4 對話的目的:應試型與能力培養型
以應試為目的的對話,教師更關注學生的成績、標準答案和應試策略。以能力培養為目的的對話則更注重培養學生的能力、技能和思維方式。教師通過對話來激發學生在元認知層面的思考。教師在教學過程中鼓勵學生大膽猜想,經常采用任務式教學法或基于問題解決的教學法。教師鼓勵學生嘗試,接納學生犯錯誤,并認為犯錯是學習和成長的必經之路。
4 總結
透過課堂師生對話,筆者發現課堂中存在大量霸權主義和單邊對話形式,以教師為中心、以完成教學進度為中心的現象仍較為常見。但課堂中仍不乏積極的溝通者,通過對話激勵、啟發學生。不同的對話類型反映出教師的執教風格和教學理念。布伯指出,教師應通過分享來影響他的學生,而不是干預他們的生活。換句話說,教師應與學生進行平等的對話,而非隨意地強迫學生接受教師的觀點。本課題研究將繼續對教師不同的對話風格進行深入分析,探索構建和諧師生關系的現實路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