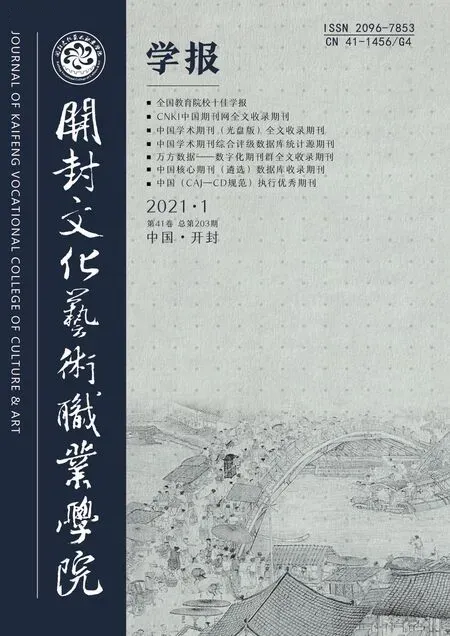儒家典籍中的“君子”概念釋義
戴雅婷
(沈陽師范大學 馬克思主義學院,遼寧 沈陽 110034)
“君子”是先秦文獻中極為常見的一個詞,諸子學說中有大量關(guān)于“君子”的表述,如《莊子·天下篇》中“以仁為恩,以義為理,以禮為行,以樂為和,熏然慈仁,謂之君子”。又如《墨子》中“君子不強聽治,即刑政亂”。儒家典籍中出現(xiàn)“君子”一詞的頻率最高,以儒家經(jīng)典之一《論語》為例,根據(jù)楊伯峻先生的統(tǒng)計,“君子”一詞在《論語》中共出現(xiàn)了107次,而《論語》全文不過11 700余字,可見“君子”概念在儒家典籍中的重要性[1]。對儒家典籍中“君子”概念的釋義,不僅是了解先秦時期君子觀的客觀需要,而且是把握儒家思想精髓的重要手段。
一、“君子”概念的淵源分析
“君”“子”二字合稱,最早可以追溯到《尚書》。在此之前,并沒有“君子”的概念。方維規(guī)在《概念史研究方法要旨》中指出“一個概念總是概念群中的概念”[2],把握“君子”概念誕生前“君”“子”二字的概念,是剖析“君子”概念淵源的必經(jīng)之路。《甲骨文合集釋文》中有不少關(guān)于“君”字的記載,如“多君弗言”“余告多君曰”,根據(jù)今人的研究,“君”指的是地位尊崇的大臣。由此可見,“君”字的本義和人的身份有關(guān)。有一定身份的人,才能稱為“君”。“子”則有子嗣和宗子兩層含義。就子嗣而言,由《說文解字》中記載的“十一月,陽氣動,萬物滋”和段玉裁《說文解字注》中記錄的“子者,滋也。滋者,言萬物滋于下也”可知,滋生后代稱為“子”。“子”字在商代卜辭、銘文中較為常見,除了有子嗣的意思外,也多用作“子某”“某子”“小子某”。根據(jù)日本學者島邦男的觀點,此處的“子”指的是與王室同姓的族長。在宗法制度下,王為大宗,其余為小宗,小宗在大宗面前自稱“小子某”,所以“子”也有地位的含義。春秋戰(zhàn)國時期,隨著士階層的崛起,“子”成為士階層的尊稱,諸子百家中孔子、孟子、莊子、韓非子中的“子”便是此義。西周初期,“君”“子”二字合稱,是有位之人的代稱,如《酒誥》中的“庶士有正越庶伯君子”一句,其中庶士、有正、庶伯、君子并列,為官員統(tǒng)稱。
二、儒家典籍中的“君子”概念解讀
(一)有位之人
從“君”“子”二字的概念解讀中可以發(fā)現(xiàn),無論是“君”還是“子”,均蘊含身份、地位之義。因此,“君子”一詞誕生之初,也表達身份地位的意思,指代有位之人,即通常所說的貴族。盡管孔子以后的儒家典籍多從道德層面來闡釋“君子”,但早期的儒家典籍,如《尚書》《詩經(jīng)》,其中的“君子”多指有位之人。
《尚書》中共3 篇有“君子”一詞,分別為《酒誥》《召誥》和《無逸》。西周建立后,周公旦封康叔為衛(wèi)君。鑒于商紂王驕奢淫逸而亡國的教訓,周公旦告誡康叔只有祭祀時才能飲酒,并寫成《酒誥》。《召誥》是召公奉命營建洛邑時所作,記載“予小臣敢以王之仇民百君子越友民”,其中“予”為召公自稱,“仇民百君子越友民”則是和召公一樣的臣民。根據(jù)清代學者孫星衍在《尚書今古文注疏》中的注釋,“百君子”指的是“王之諸臣與群吏”。由此可見,“君子”身負王命,有一定的管理之責。《無逸》中的“君子”更能體現(xiàn)“君子”的身份屬性,如“嗚呼!君子所其無逸!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則知小人之依”一句中“君子”與“小人”并列,“小人”需要從事農(nóng)業(yè)活動,為平民階層,“君子”則是在位者。周公創(chuàng)作《無逸》的目的是告誡成王不能貪圖享樂,要體驗平民的艱辛。
《詩經(jīng)》中“君子”出現(xiàn)的次數(shù)更多,從其含義來看,也多指有位之人,如《詩經(jīng)·國風·魏風·伐檀》中的“彼君子兮,不素餐兮”,意思是那些為官的老爺啊,可不能白白地吃閑飯啊。又如《詩經(jīng)·小雅·巧言》中的“亂之又生,君子信讒”。“君子”代表有位之人,在其他學派的著作中也可以找到例子,如《墨子》中的“君子不強聽治,即刑政亂”,意思是管理者不積極治理,便會出現(xiàn)混亂的局面。
(二)有德之人
早期儒家典籍中“君子”指的是有位之人,而隨著時代的不斷發(fā)展,“君子”的概念也發(fā)生了變化,逐漸從有位之人轉(zhuǎn)變?yōu)橛械轮恕L貏e是孔子以后,“君子”成為有德之人的統(tǒng)稱,有位之人的含義逐漸消失。當然,“君子”概念的轉(zhuǎn)變經(jīng)歷了一個漫長的過程,并且在這一過程中,“君子”的概念往往視語境而定,可能指有位之人,也可能指有德之人。事實上,“彼君子兮,不素餐兮”中的“君子”已經(jīng)具備了德性元素,因為它要求身居高位的君子能夠體恤民情,不肆意盤剝百姓。從歷史的角度來看,“君子”具備德性元素與殷周之際的巨大變化有很大關(guān)系。王國維在《殷周制度論》中指出:“中國政治與文化之變革,莫劇于殷、周之際。”[3]殷商重鬼神輕人事,認為統(tǒng)治階層的權(quán)力源自天命。周朝繼承了殷商的天命觀念,同時也更加注重臣民的禮樂教化。而作為統(tǒng)治階層的“君子”,自身的德行直接關(guān)系到統(tǒng)治秩序的穩(wěn)定,這為“君子”概念從有位之人轉(zhuǎn)變?yōu)橛械轮说於藞詫嵉幕A。
在“君子”概念的轉(zhuǎn)變過程中,孔子發(fā)揮了至關(guān)重要的作用。盡管“君子”一詞在西周已經(jīng)出現(xiàn),但正是孔子創(chuàng)立的儒家學派使“君子”一詞推而廣之,并成為中國古代社會理想人格的代名詞。儒家典籍中的君子德性是一個包容性非常強的體系,如《論語·學而》中的“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謂好學也已”,意思是做一個君子,應當飲食不求飽足,居住不求舒適,對工作勤奮敏捷,說話要小心謹慎,主動去接近有道德、有學問的人。《論語·里仁》中的“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意思是君子注重的是道義,小人注重的是利益,以義利關(guān)系對“君子”和“小人”作了區(qū)分。《論語·泰伯》中“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動容貌,斯遠暴慢矣;正顏色,斯近信矣;出辭氣,斯遠鄙倍矣。籩豆之事,則有司存”。這句話指出“君子”應當注重嚴肅容貌、端正臉色、注意語氣三個方面的內(nèi)容。
三、儒家典籍中“君子”概念變化的原因
(一)天命觀念的變化
“君子”能夠指代貴族,和天命觀念有關(guān)。人類社會早期,認識自然和改造自然的能力非常弱,天成為人們尊崇的對象,天命是統(tǒng)治者政權(quán)的合法性來源,統(tǒng)治者荒淫無道會引發(fā)天命的合法性危機[4]。夏朝末年,統(tǒng)治者昏庸,老百姓喊出了“時日曷喪,予及汝皆亡”,這是對上天不公的吶喊。《詩經(jīng)》中,怨恨上天的詩句更多。周朝中后期,王室衰微,百姓生活困頓,《詩經(jīng)·大雅·桑柔》中有“天降喪亂,滅我立王。降此蟊賊,稼穡卒癢”的感慨;《詩經(jīng)·小雅·雨無正》中則有“浩浩昊天,不駿其德。降喪饑饉,斬伐四國”的質(zhì)問。老百姓對天命的懷疑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君子”作為有位之人的合法性。
(二)士階層的崛起
士階層的崛起是“君子”概念從有位之人轉(zhuǎn)變?yōu)橛械轮说闹匾蛩亍N髦懿捎米诜ㄖ贫群头址庵贫龋熳訛榇笞冢髦T侯為小宗,小宗可以繼續(xù)分封。分封不僅會賜予諸侯爵位,而且要劃分土地。隨著時代的不斷發(fā)展,諸侯國內(nèi)部的大夫、士數(shù)量不斷增加。諸侯國內(nèi)部有限的土地與不斷增加的大夫、士的數(shù)量形成了鮮明的對比,由此便出現(xiàn)了許多有爵位、無封地的士。同時,春秋戰(zhàn)國時期,諸侯間競爭極為激烈,以血緣為紐帶的貴族統(tǒng)治已經(jīng)無法適應時代發(fā)展的需要,不少諸侯國進行了政治體制改革,實行更為高效的官僚制度,這讓許多平民躍升為管理者,促進了士階層的崛起[5]。“君子”內(nèi)涵的轉(zhuǎn)變是一個持續(xù)性、漸進性的過程,時代環(huán)境的變化使得“君子”作為“有位之人”的社會基礎發(fā)生了動搖,而儒家學派的興起則促進了“君子”從“有位之人”向“有德之人”轉(zhuǎn)變。先秦典籍,特別是孔子后的儒家典籍,士與“君子”多為同義,如“士不可不弘毅”。
結(jié)語
“君子”概念從先秦宗法制度中產(chǎn)生并成熟,諸子百家中關(guān)于“君子”的描述非常多。早期的“君子”指有位之人,儒家從仁的思想出發(fā),對“君子”概念作了變革,使“君子”從有位之人轉(zhuǎn)變?yōu)橛械轮耍赖鲁蔀椤熬印钡暮诵囊x。促進這一轉(zhuǎn)變的因素有很多,既和天命神權(quán)的解體有關(guān),又與處于高位的“君子”的失位有關(guā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