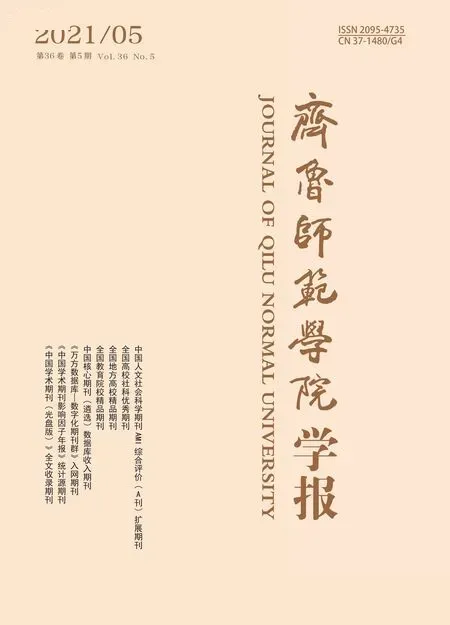現代新儒家哲學的教化意蘊
——以梁漱溟、熊十力、馬一浮為中心的考察
金 楠
(江蘇師范大學 教育科學學院,江蘇 徐州 221116)
自近代以降,西方思潮與觀念的涌入給當時中國學界造成了不小的“思想混亂”。現代新儒家主義者的出現,不僅體現了其對中華文化的堅守,同時也溝通了中國傳統儒學與西方思想,在某種程度上緩和了中國的文化精神與學術傳統所面臨的危機。梁漱溟、熊十力、馬一浮作為一個文化共同體,與他們的后生一起,構成了現代中國學術發展歷程中特殊的文化部落。他們的學術與思想帶有強烈的時代精神與救亡圖存的使命感,在充滿變數的近現代中國,三位先生治學躬行,為生民立命,為往圣繼絕學,為遭受危機與挑戰的中國文化發聲,為身處變局與困境的中國社會尋找出路。
一、不安的時代:現代新儒家思想資源的歷史語境
西潮東漸以前,中國的發展基本遵循一種“在傳統中變”(change with tradition)的模式[1]1。近代中國身處“數千年未有的大變局”,面臨著前所未有的民族危機、社會危機、文化危機。存在了兩千多年的以儒家道統為核心的社會秩序也遭受到來自各個層面的沖擊與挑戰。中西文化之間的膠著,催生了深層次的政治變革與社會轉型,影響著近現代中國的格局與走向。
(一)社會動蕩與文教變革
“亂”與“變”成為近現代中國社會的主要特征,在列強洋槍大炮的逼迫和西方思潮的席卷下,近代化的進程也隨之啟動。在張之洞和袁世凱等人的直接推動下,存在了一千三百多年的科舉制度被廢除,而這一舉動成為中國近代史上最為重要的體制變動之一。自科舉制設立以來,它與儒學一道,為中國封建社會提供了穩定的政治和社會秩序。而這一集文化、教育、政治、社會等多方面功能的基本建制(institution)的解體[1]110,對于晚清社會的格局和結構都產生了微妙的變化。
在眾多歷史學與社會學視閾下的社群(community)研究中都提出了這樣一個觀點,就是科舉制度的崩潰所導致的直接后果就是“四民社會”的解體。對四民之首的“士”而言,科舉的廢除使得實現社會階層跨越的機會越來越少,再加上西潮的沖擊,“士”階層爆發了心靈危機。盡管當時的晚清政府作出了辦新式學堂、推行新學制等改革舉措,但由于與科舉制廢除的節奏“失衡”,導致了全國教育被煮成了一鍋“夾生飯”[1]114,“士”階層對于當局所重建的教育秩序和選才制度已失去了信心。
許紀霖認為:“在傳統中國社會, 士大夫是四民社會的中心。”[2]73-90,3但在這一時期,一方面,“士”階層對晚清政府在教育改革的作為缺乏認同;另一方面,“士”階層在社會變局中也越來越“邊緣化”。那么, 到了近代以后,他們是否還能繼續支撐著社會的重心,答案無疑是否定的。知識分子們不僅僅再也不能像以前那樣享受“社會特權”和“文化威權”以及支撐社會的重心,而且在這個群體的內部也發生了微妙的分化與轉型。中等社會的士人已經與那些具有既得利益的、體制內的士大夫發生了分化, 一種是像梁啟超這樣的在體制之外靠輿論起家的新式士大夫, 而另外一部分是接受了新學教育的知識分子[3]425。
(二)思潮涌動與權勢轉移
馮契曾說:“從鴉片戰爭開始的近代一百余年間,中國的思想界不斷掀起軒然大波,形成了思潮蜂起、波瀾壯闊的歷史圖卷。在短短百年間,特別是在十九世紀末至二十世紀前半葉的數十年間,如此多的思潮紛呈涌動,在數千年的中華文明史上可以說是沒有前例的,它集中地體現了中華民族在近代歷史條件下,思想的空前活躍,爭鳴的空前激烈,精神的迅速高揚。”[4]35實際上,19世紀到20世紀,西方自身也是充滿變化的,這種變化不僅僅是工藝和科技上的進步,更是制度和觀念上的更新。這些在中國士人們的眼里,都是西方“強大的秘訣”。所以,“向西方學習”這個共識似乎成了晚清時期的主旋律。
隨著中西方交往的深入,中國士人開始陷入了思考。近代中國之敗,根在何處?嚴復曾將其歸結成一個簡單的達爾文主義的公式:物競天擇,優勝劣敗,適者生存。說到底,在士人們的心目中,中國文化的低劣性才是導致潰敗的根本原因。從此,西方文化的優越觀在中國士人的心中逐步建立起來,甚至出現了“稍知西學,則遵奉太過,而化為西人”的現象[5]177。對于這一現象之本質的思考,胡適曾將其概括為“中西兩個文明之爭”[6]383。在這場競爭中,中國對西潮的沖擊顯得毫無“還手之力”,再加上帝國主義對中國文化控制的野心之強,通過對傳教士的鼓動,廢除中國的“國學”,以達到絕中國之種性的目的[7]475。這樣一來,中國文化所處的尷尬境地使得這場文化競爭的勝負毫無懸念,中國傳統的地位也岌岌可危。
西方思潮的涌動和文化競爭的失敗導致近代中國的思想、學術以及社會都呈現出一個正統衰落、邊緣上升的大趨勢,處處提示著一種權勢的轉移[1]2,一種新的思想秩序正在被建立起來。出于“救國”的考慮,中國傳統曾在那時被知識分子們過分地負面解讀,甚至形成了將中西方文化進行對立的局面。自清季始,“保國”與“保教”之爭使得士人們陷入深深的文化自卑之中,心態的緊張催發了外在的激進,致使“國粹”的各個方面都受到質疑甚至是否定。梁啟超在那時已經注意到“馬克思差不多要和孔子爭席,易卜生差不多要推倒屈原”[8]45。中國文化系統遭受了前所未有的沖擊與破壞,一時竟存在被全盤否定的風險。
(三)理論躊躇與學術轉向
王汎森認為,自清道光以來,中國思想界便進入不安定期,每一種學問都因內外的挑戰而產生了分子結構的變化[9]1。這種不安定在近代以來就顯得及其明顯。五四運動之后,由于袁世凱稱帝和張勛復辟,造成了知識分子們以及整個社會心態的恐慌,以儒家為代表的中國本土思想遭到了無情的打壓,處于一種完全被疏離的狀態。再加上科學主義的輸入和知識分子們對其的擁護,中國的思想界陷入了長期的理論躊躇與價值混亂的狀態。
然而在這個時期,卻促使了新儒家主義者的出現。在社會急劇的變遷中,人們的思想被新的理論裹挾而脫節于舊的傳統,面臨著嚴重的思想危機。人們開始想知道“他們屬于何處,他們是誰,要到何處去”這一些系列的問題。即由于當時政治秩序與價值觀念的巨變,社會缺乏這種文化認同,新儒家思想恰恰能為當時知識分子們所面臨的意義、精神、道德、價值等危機提供一種可行的解決方案。他們急于與“過去”之間重建有意義的延續,來解除時代的變遷震撼,并在自我之中定住方向[10]786。而對于文化認同的理解,在新儒家主義者看來,是更加有助于闡明新儒家思想中“能將中國的思想遺產與西方的民主科學共存”之特點。對于如何處理儒學和科學之間關系以及如何正確對待科學,成了新儒家主義者們孜孜以求的問題。
在此基礎上,新儒家開始對中國哲學進行重建。“哲學要回答時代的問題。”[4]343這是馮契對中國近代哲學理解的一個基本點。那么對于近代來說,時代的問題是什么呢?就是關于中國“該向何處走?”的問題。其本質就是中國文化發展的世界語境問題[11]139。通過對自身文化的審視,樹立起重新在世界范圍內安頓中國文化的目標。新儒家對于中國哲學中一些根本問題重新思考既是順應了中國哲學發展的邏輯與趨勢,又回答了時代所提出的問題。
二、梁漱溟的關切:人心、社會與文化
人生與社會的問題,這是梁漱溟一生當中最關心的兩個問題。本著“問題中人”的態度,他致力于分析轉型中的近現代中國的種種矛盾,并將一些思想成果進行了實踐,以達到他心目中關于做人之道與社會改造的設想。他寄希望于鄉村改造和教育實驗,同時吸收西方憲政文化和中國儒家思想,努力探索出適合中國發展的道路。
(一)人的改造:擴大教育的空間與可能
在早期對于人心的認識上,梁漱溟認為人心中只有本能與理智之分。從巴甫洛夫的觀點出發,梁漱溟認為高等動物之所以頭腦發達、身心協調,是因為與生俱來的本能中的“機械性”在后天的生活經驗被改造,而這個改造的前提,是基于理智的實現。在他看來,這兩個要素在某種意義上構成了一種“對立”的關系,理智成了一種“反乎”本能而存在的東西。在個體生長的過程中,作為與生俱來的“專業化能力”,本能在一開始便具有指導個體進行基本活動的作用,但具有“逐漸淡褪”的意味;反之,理智塑造人的經驗與智慧,卻有“愈加生長”的特點。此“一長一消”,構成了生命的完整歷程,同時也消融了本能中“僵硬”之處,將其轉化成經驗與智慧,并留下了創造的可能與潛能[12]50。
在后期,梁漱溟吸收了羅素在《社會改造原理》中的觀點,將“靈性”納入到人心的基本要素中去。羅素指出,靈性與本能、理智之間的平衡,構成了個體和諧生活的前提[12]80。同時,靈性作為情感與道德的精神來源,是個體“形上追求”的起點。梁漱溟則認為此概念帶有“神秘氣味”,故將羅素“靈性”的觀點加以改造,賦予其“理性”的概念。在他看來,“理性”指向“情理”的生成,屬于道德情感的范疇。而“理智”卻為觀察事物客觀實在的一種能力,稱之為“物理”。在這里,他還形象地把毛澤東《論持久戰》中的論述作為例子,認為書中提出的“靈活性、主動性、計劃性”實為理智之作用,而對于革命戰——正義、反革命戰——非正義的對應將其定義為理性之作用。最后得出:“理智者人心之妙用;理性者人心之美德。后者為體,前者為用。”的結論[12]83。
對于理智和理性的思考,使得梁漱溟在此之中挖掘出了教化的意義,也給教育創造了空間與可能。作為“宇宙間頂可寶貴”的東西,理性之“反乎愚蔽”與“反乎強暴”的概念為人類的開明與國家的和平提供了可能。在中國,對于理性精神教化的源泉來自于儒家的理性精神。長期以來,儒家精神以“自省”為核心,通過對人不斷地教化,養成個體之理性,以構建和諧社會。至此,梁漱溟認為,個體理性之塑造對于中國未來的前途影響深遠。
(二)社會的改造:鄉村教育組織的建設與功用
梁漱溟找到西方近代各種主義興盛的源頭,發現不管是自由主義或是社會主義的出現,都是出于其對集團過強干涉的反動而來[13]24。而“集團生活”作為西方國家所構成的基本要素,長期以來在中國卻從未出現。這也進一步解釋了為何中國沒有形成基督教式宗教的原因。那么究竟是怎樣的一股力量一直維系著中國社會幾千年來社會秩序的穩定?這個答案在梁漱溟看來就是倫理。而中國的倫理始于家庭,所以中國倫理本位的社會將家庭作為基本單位,同時構建了以君臣、父子、夫妻、朋友為基本社會關系的倫理秩序,形成了以家庭關系為重的倫理社會。
但在近現代中國,社會的崩潰使種種秩序與倫理處于分崩離析的境地,幾乎喪失了國家建構與社會建構的能力。而同時期的丹麥,農村合作社的成功,使得整個國家的經濟迅速發展,基礎教育與基層政治得到了充分的建設與完善。梁漱溟注意到了這一點。與丹麥一樣,作為典型的農業國家,中國的農村應作為社會改革的發力點。他把希望寄托于對于鄉村組織的重建,設計出一個既以“倫理情誼為本原”,又帶有“純粹理性”的教育化組織[13]146。這種構想來源于杜威《民主主義與教育》中關于教育與社會關系的觀點,梁漱溟認為人類的教育與人類的社會為同一件事情,原因就在于:無論哪一種社會組織,只要他骨子里含有社會性或使人能參與他骨子里的活動,那么這種社會對于在里面參與的人,都是有教育的效力的[13]148。
另外,對于鄉村教育組織的設計不僅是梁漱溟對于解決中國問題所提出的方案,更體現了梁漱溟對于教育的社會作用的思考。鄉農學校不只作為講學、求學的地方,也發揮著基層組織自治、民主的作用。一方面,向農民傳授知識與技術,提高農業生產的專業化與科學化,完成農民的基礎教育與繼續教育;另一方面,通過對鄉村學校中“鄉約”的構造與實施,充分發揮基層的民主,讓“鄉村里的人自己解決鄉村的問題”[13]18。在這里,我們不僅看到了梁漱溟描繪的一幅理想社會的藍圖,也看到了梁漱溟教育思想中將基層的教化與治理并重的深層意蘊。
(三)文化的改造:取西方之長以求自身發展
文化競爭的失敗,成為近現代中國社會所面臨的最大危機。對于如何審視自身的問題,如何為中國尋出路,成為那個時代最重要的問題。西方強大、中方落后的事實讓知識分子們不得不格外青睞科學與民主。但梁漱溟卻認為中西的差異不是發展程度上的不同,而是文化路向的不同。他以“意欲”說來分析東西文化的根本差異,認為西方科學與民主的精神來源于他們“向前要求”的意欲,所以西方在征服自然、改造自然上領先于中國;而中國以“調和”“隨遇而安”的意欲向自然妥協,故在中國從未出現過 “塞恩斯”與“德謨克拉西”兩大異彩的文化[14]6。
通過鄉村教育實踐,梁漱溟看到了中國社會發展的窘境,而教育在社會改造之過渡時代未能盡其社會之功用。“社會之功用”為“推進文化改在社會之功”,實則是將社會改造與文化保存的雙重作用賦予教育。作為一種“溫和且影響深遠”的方式,梁漱溟將教育看作為影響社會改造與文化保存的重要因素。由于近現代中國社會經濟的落后與物質生活的匱乏,梁漱溟也主張現代中國人應該追求科學與民主的價值觀念。但中西文化路向上的根本差異使得這項工程存在著難以調和的矛盾,于是問題就變成了如何以孔子和儒家的文化、孔子和儒家的生活態度來中和輸入進來的西洋文化的問題[23]102-115。再具體一點說,就是如何在孔子儒家的根干上也能開出科學、德謨克拉西和物質文明的花[15]253。但遺憾的是,梁漱溟并沒有作出具體的回答,只是一昧地提倡“孔子的生活態度”,這也成為當時思想界對其批判的主要原因。
但在梁漱溟眼中,傳統的“根”是好的,“老道理”是站的住的。為了打開中國文化的新局面,同時保住“傳統的根”,他將“鄉村建設”的理論起點設定為“從創造新文化上來救活舊農村”,意圖解決中國之深層問題。例如在《社會本位的教育系統草案》中,他認為中國社會改造的實質為取現代文明之長以求自身文化之長進。在《曲阜大學之提議及其籌計進行》中,他指出“辦曲阜大學的旨趣是想取東方的——尤其是中國的學術暨文化各方面做一番研討昭宣的功夫,使之與現代的學術思想能接頭”[16]248。
三、熊十力的詮釋:生命、德性與倫理
熊十力作為20世紀奠定中國新儒學思潮形上基礎的重要人物,一生都致力于溝通中國傳統學術思想的古今以回應西學的沖擊。在儒學價值系統崩壞的時代,他努力重建儒學的本體論,重建人的道德自我,重建中國文化的主體性[17]64。他將儒、佛、道三種思想打通,融于中國傳統哲學中最能彰顯內在精神的心學,建構起“新唯識論”哲學體系,成為現代新儒家主流思想的理論依據。
(一)本體與心性:個體生命的健動
熊十力認為,對本體的討論乃是哲學的首務,也成為其思想體系的邏輯起點。在他看來,本體論并非一種玄思,或者只是尋求外在的真理;他主張,本體的追尋乃在彰顯人類文化與宇宙之生生不息(Creative Transforming)的終極根源[9]816。作為宇宙的真源,本體是天地間一切事物發展的起點;同樣,要解決一切問題,也必須回到本體上來。故只有能證會本體的哲學,才是真理。“吾學貴在見體”證明了中國哲學中“對本體的超越”的特點,而西方科學只是停留在認識論的層面,缺乏本體的見解,這被熊十力看作是中國哲學優于西方科學之所在。
本體為萬理之源、萬德之端、萬化之始[18]358,有著生生、健動的氣息。“恒轉”與“能動”是本體的特點,本體之實也在于“恒轉”和“能動”。而生命之變可概括為“翕辟成變”,“恒轉之現為翕,而幾至不守自性,此貪便是二,所謂一生二是也。然恒轉畢竟常如其性,決不會物化的。所以,當其翕時,即由辟的勢用俱起,這一辟,就名為三,所謂二生三是也。前來已說,所謂變化,只是率循相反相成的一大法則,于此可見了。”[19]99由此可見,本體的變化與生命的健動指向一致。故本體論亦有生命論的意味。
本體之變為宇宙萬物變幻之根源,生命之翕辟為個體的精進健動創造了內在動力。在熊十力看來,實現這種健動需要基于心性的勢用。心性的勢用則表現為個體對本心的反求,內化成對個體生命力的激發。熊十力的本體論涵蓋了生命與心性的范疇,同時也為個體的內心與生命的發展指明了一種方向。個體的存在以生命為本,以健動為力,而教育的基本作用就是為個體實現存在的可能與意義,所以教育的目的應當關涉一種對個體內在的、健動的生命力的激發。
(二)性修與內圣:成己之德的形塑
心者即性,是本來故。心所即習,是后起故[19]105。熊十力一再強調“見體”,也是為性修成己所用。于個體而言,“見體”意味著對天性與本心正確的認識。然而人的生命與天性具有不可改變的限制與差異,使人無法充分地“認識你自己”。這種認識的缺失與對自身限制的不滿足會使人轉向對外物的追求,熊十力將其稱之為“習心”。“習心”與天性一道,構成“染習”,形成人與人、人與社會的交往。他又認為“染習”為惡的根源,會不可避免地帶來“貪、嗔、癡”三毒,個體很容易受到蒙蔽,被物化之流所驅使,無法真正地“成為你自己”。
何以成己?這是儒家“內圣”學說討論的重要問題。而熊十力認為成己的最根本的辦法就是超越“貪、嗔、癡”對人的限制,回歸本真。只有對外物貪戀的放逐、與外界仁善的相處和將外體魅惑的破除才能使得個體真正地證悟本體,實現內圣。對于成己的具體辦法,熊十力十分認同《中庸》提出的“格物致知”。在他看來,致知應當作為一切知識的統合,從而以致知統合格物, 同時在道德理性的范導下來安排知識, 以知識融入道德, 使知識活動成為一個有價值參與的整體[20]29-30。
可以看出,熊十力認為成己的本質就是依靠知識對于道德意志的內化力量,所以成己說實則為一種涵養內心與道德的學說。這與中國傳統儒家的“良知論”意蘊相符。對照蘇格拉底提出的“知識即美德”的命題,不難發現,西方文化德性論的理路是知善止惡,東方文化則化知識為德性,走上了一條為善止惡的道路[21]31-42。在東方文化中,德性作為人存在的基礎品格,德性的樹立當為教育的首要之義、應有之義與內在之義。
(三)治化與外王:社會倫理的建構
政治建設與社會治理影響著一代人的安身立命,是近現代知識分子們最關切的問題。作為幾千年來建構社會秩序與政治形態的綱領,儒家的治化理論仍被熊十力所認同。他將六經中的治化理論進行重新總結,歸納出治化論的形上基礎、邏輯起點、具體方式與終極目標。“仁以為體”作為形上基礎,是治化的根本要義;“格物為用”作為邏輯起點,統合人的一切德行;“成恕均平為經”“隨時更化為權”“利用厚生”“本之正德”“政齊刑,歸于禮讓”“以人治人”作為治化的具體方式,為治理社會提供了具體方案;“萬物各得其所”“終乎以群龍無首”作為治化的終極目標[22]581,描繪了一幅人類社會的理想藍圖。
從熊十力對治化對象的重新推衍中,可以看出其理論展開的角度與層次。自然、人、政治是治化的主要對象,而這三者存在著天然的、密不可分的聯系。自然的治化意味著改造自然,即正確地處理好人和自然的關系;人的治化代表了對人的改造,以教化而正人心、明明德;政治的治化則表示社會治理與國家建構。從本體論的角度出發,宇宙與萬物為本體,生命與心性也為本體,所以人與自然的治化是同根同源的。這二者的和諧治化一旦實現,政治的改造就會卓有成效,并助推理想社會的形成。理想的社會中的人會被賦予合理的自由與權利,轉而人也會以正義與仁愛對待自然與社會,這便是真正的“外王”。
那么在人與自然治化的進程中,需要合乎怎樣的依據?《禮記》曾云:“禮者,天地之序也。”對此,熊十力提出:“禮者以天理為源,其源深遠。故人之為禮,有本而不可亂也。”[23]656“禮”作為社會倫理的尺度,是人一切活動的出發點與落腳點。但“禮”的素養又不為人天生具有,并且會隨著后天私欲的漸長而消弭。他將禮制的重建寄希望于人文教育,通過教化的方式實現人的治化。在他看來,教育不僅僅是學習科學知識,培養通才,更重要的是要教人以“人生的智慧”。他強調學習哲學的作用,不僅是為了個體參透中國哲學中窮盡宇宙的奧義,領會“圣人之德”,證悟本體與本心,更是為了在個體的生命活動中能夠踐行“圣人之德”,以實現真正的“外王”。
四、馬一浮的踐履:復性、六藝與書院
在西學知識主義教育的沖擊下,教育的“傳道”之義在馬一浮看來已全然喪失。他倡導治學的“道體合一”,以學問銜接德行,即將“德性之知”置于“聞見之知”上[24]12,最終實現大智慧的秉持。“復性”一詞是馬一浮教育哲學中最核心的理念,通過對宋明理學的自覺繼承與體悟,逐步建立起了以“復性立人”與“六藝教育”為主要特征的教育理論與教學實踐的思想體系。
(一)復性歸本:立人的終極關懷
孟子曾首創“復性”學說,此后唐代李翱所作《復性書》在孟子的基礎上進行了更深刻的闡釋。作為人性的應然狀態,仁善之心的恢復是個體治學與修行的終極目標。傳統儒家力求將“尊德性”融入“道問學”,體現了德性與德知的“知行合一”的特點,實則是將學問的探求與道德的踐行相結合。馬一浮認為性德為人所固有,但如若人不進行修證,性德就無法顯現。性起于修,修全在性。只有以性德求修德,才能見性復性。結合宋明理學的工夫論,他緩和了心性與躬行之間的緊張,梳理了本性與工夫之間的關系,確立復性對于個體實踐的形上地位。
中國近代教育的發展曾深受西方知識觀的影響。西方強大的事實使人們相信只有科學技術的知識教育才能促進國力的發展。人們將對知識與理性的渴求訴諸于教育,知識的學習應當是教育的首要目的。甚至,人們開始相信“可以充分利用知識和技術來管理這個星球”,“知識按照人們的良好愿望正在增長”[25]476,對效率和實用的盲從讓教育的“教育性”意義蕩然無存。中國人自古以來都有以陶養身心、修養工夫為本位的求學治道精神,而這在當時深受西方知識觀影響的中國社會,似乎已被淡忘。
從根本上講,西方科學的涌入,科技理性的膨脹,人文價值的喪失,道德意識的危機加速了近現代中國傳統教育模式的解體。家庭與個人倫理本位的價值系統的崩塌也使人們不再重視個體的價值。面對真實的社會狀況,馬一浮提出復性應當為教育的本義。他看到了個體改造后的力量,也唯有改造個體,才會實現整體層面的民族革新。以復性立人,意在改變現代教育中出現的重知識而輕個體的局面,重視個體本身的治學與德行,以個體建設紓解救亡圖存之困難,重拾儒學傳統的內圣外王之道。
(二)六藝之道:授人以經典國學
六藝之教固是中國至高特殊之文化[26]23。馬一浮將儒家六經改稱“六藝”,并認為六經是中國思想的經典源頭,是中華文化的最高級形態。但六經在近代中國學術界的地位曾岌岌可危。胡適提出的“國故整理”就是倡導對國學經典的客觀研究與繼承。馬一浮在《復性書院簡章》中強調:“書院之設,為專明吾國學術本原,使學者得自由研究,養成通儒。”[27]41他將六藝之學上升到國學的高度,予以經典解釋,縱橫學術史觀,以發揚國學之學。同時,國學教育使得國學與國民接頭,達到保存與繼承國學的目的,讓國粹經典“飛入尋常百姓家”。
馬一浮融攝儒佛,申發出“六藝論”的文化哲學[17]110。而“六藝論”的形上根據發韌于他的“性德”說,即如何將實現復性與陶養個體合二為一,達到性修不二的境界。“仁”是諸種德相之首,能夠涵養眾多德相;六藝為經典之首,能夠通達古今國學。“以《詩》主仁,《書》主知,《樂》主圣,《禮》主義,《易》明大本是中,《春秋》明達道是和。”[26]17每一本經典都代表一種德相,六藝之學的完成就是性德的實現。六藝之學的意義不僅僅只存在于學術層面,更重要的是,它生成了六藝之道,呈現出真、善、美的價值世界,使人安頓了生命,成就了自身。
不僅如此,馬一浮還認為六藝之學可統攝西方的一切學術。他的觀點大體為:“自然科學可統于《易》,社會科學可統于《春秋》,文學、藝術統于《詩》《樂》,政治、法律、經濟統于《書》《禮》,此最易知。”[26]18在他看來,六藝為西方之學術本原,倘若以六藝先入為主,再學習西方的科學技術,就不僅可以調和中西文化中的矛盾,還可以保得民族性的完整。以今天的觀點看,“六藝統攝西學”的說法可能有失偏頗,但考慮到馬一浮身處的背景——五四以來的全盤西化,這種聲音在那個時代無疑起到了振聾發聵的作用,似乎又可以理解他身處國學與民族困境中的良苦用心。
(三)書院成教:育人的實際踐行
近現代的教育變革緣起于對西方教育思潮沖擊的回應,但改革后的教育模式與制度多與西方相近,或者很大程度上就是以西方制度為模型仿照建立。在此之前,書院教育扮演著主流教育機制的角色,自唐初設立以來,不斷地發揮著教化國民與文化傳承的作用。壬寅學制、癸卯學制、壬子癸丑學制的推出改變了以書院教育為主導的格局,課程的變革使得西方科學技術知識成為學校教育的主要內容。“讀經”的廢止,使得儒家經典正式退出了教育的舞臺,現代學校的建立淘汰了書院教育這一存在了一千多年的教育模式,現代教育體制在舉國通行。
馬一浮曾呼吁在國民高等教育中保留通儒院這一機構,意在以國學為本,與西方文化展開溝通與對話,但遭到了蔡元培的反對。考慮到當局無意再提國學教育,也無意維護國學的地位,為挽救國本,繼承絕學,馬一浮在四川樂山開辦了復性書院。他一改過去取地點為名的方式,將書院的宗趣作為書院的名字,體現了他的辦學理念與目標。為了保持復性書院的純凈,馬一浮在《書院之名稱旨趣及簡要辦法》中明確指出:“書院為純粹研究學術團體,不涉任何政治意味。凡院師生,不參加任何政治運動。”[25]1169而復性書院的教學內容,則以六藝之學為主。秉承著重建義理之學和養成通儒的愿景,馬一浮對六經進行了重新詮釋,并將其融入書院的課程中。在講學過程中,他竭心盡力,了解每一位學生心中所想,解答諸生求學之惑。為的是使諸生豎起脊梁,做一個堂堂正正的人,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可以說,復性書院的辦學不僅是復興民族精神、民族文化的艱難嘗試,也是馬一浮等儒學大師們為當時身處困境的國學所尋的可能出路。
近現代中國思想與學術的發展深受中西與古今之間的裹挾與纏繞。在社會轉型、時代變遷與國家建構的浪潮中,中國教育的制度建設、宗旨厘定與實際踐行也經歷了大大小小的變革。教育是時代中意識形態的產物,是民族文化延續的源泉,在西方現代教育思潮席卷中國之際,梁漱溟、熊十力、馬一浮三位先生對儒學的重新思考與建設,對中國文化的回歸與堅守,對人文教化事業的實踐與探索成為我們應對時代挑戰、建立獨立話語、尋求中華民族文化身份認同以及構建具有中國特色教育理論的重要思想資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