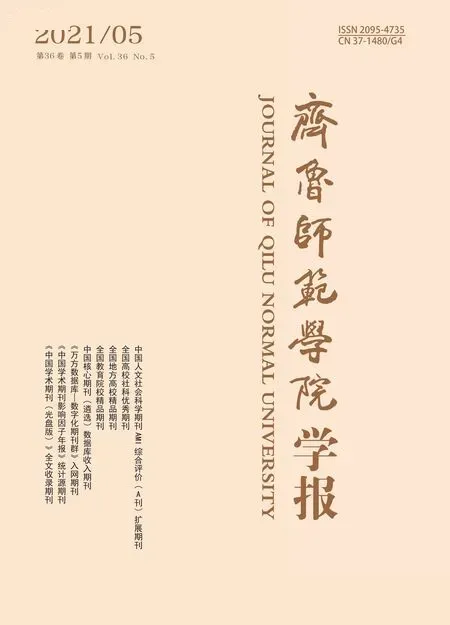從奇形異貌圣事角度再論《史記》的實錄
張學成
(江蘇護理職業學院,江蘇 淮安 223005)
《史記》是實錄的典型代表,劉向、揚雄贊許為“實錄”,班固在《漢書》中轉述劉向、揚雄二人語,稱司馬遷“善序事理,辨而不華,質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故謂之實錄”[1]2738。劉勰在《文心雕龍·史傳》中評價《史記》有“實錄無隱之旨”的特點[2]206。“實錄”和“善序事理”其實就是中國史官秉筆直書優良傳統的具體體現。司馬遷著史的主要目的為“通古今之變”,無論是“本紀”的“序帝王”,“世家”的“記侯國”,還是“表”的“系時事”,“書”的“詳制度”,“列傳”的“志人物”,全都是敘事。“序”,敘述,即敘事。“善”有技法高超之意。司馬遷著錄《史記》的最終目的為“成一家之言”,就是要在記敘歷史的發展變化中闡明歷史發展演變的內在規律,表明自己的思想和認識,這就是理。關于《史記》實錄的特點,幾乎成為歷代學者的共識。
班彪班固父子、揚雄、劉勰、劉知幾等學者對《史記》的撰著雖有微詞,然而事實上《史記》一書已然無可爭議地成為中國正史的楷模標范,這無疑是中國文化史的偉大創造,無論如何都不能抹殺司馬遷的偉大貢獻。
一、神怪記載的闡釋
我們在研讀《史記》時卻意外地發現,在《史記》中竟然存在大量似與“實錄”不相符合的矛盾性描寫,筆者姑且將有關描寫概括為“奇形異貌圣事”。司馬遷尊崇孔子,將自己的編史敘史與孔子的編著《春秋》相類比,這本身就是對孔子的景仰和禮贊。“子不語怪力亂神”,孔子對怪神等的態度若何,這不是本文要論述的范疇,我們暫且不論;如果以孔子作為標榜,那么司馬遷在《史記》中也不應該有怪力亂神的記錄敘寫,但事實上,在《史記》中似乎神神怪怪的人事并不少見。
我們先看《五帝本紀》中的黃帝:黃帝,“生而神靈,弱而能言,幼而徇齊,長而敦敏,成而聰明。軒轅之時,神農氏世衰。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農氏弗能征。於是軒轅乃習用干戈,以征不享,諸侯咸來賓從。而蚩尤最為暴,莫能伐。炎帝欲侵陵諸侯,諸侯咸歸軒轅。軒轅乃修德振兵,治五氣,蓺五種,撫萬民,度四方,教熊羆貔貅貙虎,以與炎帝戰於阪泉之野。”皇帝作為中華民族共同的祖先,他生而神靈,長而敦敏,教練熊羆貔貅貙虎,征伐蚩尤炎帝,自然具有超凡的神力。
再來看幾個始祖誕生的記載:
《殷本紀》中的契:“殷契,母曰簡狄,有娀氏之女,為帝嚳次妃。三人行浴,見玄鳥墮其卵,簡狄取吞之,因孕生契。”
《周本紀》中的后稷:“周后稷,名棄。其母有邰氏女,曰姜原。姜原為帝嚳元妃。姜原出野,見巨人跡,心忻然說,欲踐之,踐之而身動如孕者。居期而生子,以為不祥,棄之隘巷,馬牛過者皆辟不踐;徙置之林中,適會山林多人,遷之;而棄渠中冰上,飛鳥以其翼覆薦之。姜原以為神,遂收養長之。初欲棄之,因名曰棄。”
《秦本紀》中的秦之始祖大業:“秦之先,帝顓頊之苗裔孫曰女脩。女脩織,玄鳥隕卵,女脩吞之,生子大業。”
這些記載,如契、后稷、大業的出生,都與部落始祖的出生有關。《呂氏春秋·恃君覽》:“昔太古嘗無君矣,其民聚生群處,知母不知父,無親戚兄弟夫妻男女之別。”[3]741-742郭沫若認為:“原始的人只知有母而不知有父,這在歐洲是前世紀的后半期才發現了的。但在中國是已經老早就有人倡道了。”“黃帝以來的五帝和三王的祖先的誕生傳說都是‘感天而生,知有母而不知有父’,那正表明是一野合的雜交時代或者血族群婚的母系社會。”[4]13、20母系氏族社會時期圣王多感天而生,“感天”而生是假,難以確定父親是真。母系氏族社會時期,沒有實行一夫一妻制,唯一能確認的是生母,難以確定生父。對此,孫作云有更詳細的解說:“周人知道他們的女老祖宗姜嫄無夫而生子,但到《二雅》時代,他們已經是文明人了,再不敢正視這種野蠻事實,便把這種極原始的風俗說成了靈異,說姜嫄履‘帝’跡而生子。但我們知道,在原始社會里根本就沒有上帝信仰的,——上帝是階級社會的產物,是人間有了統一的帝王以后,反映到天上,天上才有這樣統一的上帝。因此,肯定地說,說姜嫄履帝跡而生子,顯然是后代的訛傳、或作詩的人的故意粉飾。”[5]6
我們再來看漢文帝的出生:“始姬少時,與管夫人、趙子兒相愛,約曰:‘先貴無相忘。’已而管夫人、趙子兒先幸漢王。漢王坐河南宮成皋臺,此兩美人相與笑薄姬初時約。漢王聞之,問其故,兩人具以實告漢王。漢王心慘然,憐薄姬,是日召而幸之。薄姬曰:‘昨暮夜妾夢蒼龍據吾腹。’高帝曰:‘此貴徵也,吾為女遂成之。’一幸生男,是為代王。”(《外戚世家》)
還有漢武帝的出生:“王太后,槐里人,母曰臧兒。臧兒者,故燕王臧荼孫也。臧兒嫁為槐里王仲妻,生男曰信,與兩女。而仲死,臧兒更嫁長陵田氏,生男蚡、勝。臧兒長女嫁為金王孫婦,生一女矣,而臧兒卜筮之,曰兩女皆當貴。因欲奇兩女,乃奪金氏。金氏怒,不肯予決,乃內之太子宮。太子幸愛之,生三女一男。男方在身時,王美人夢日入其懷。以告太子,太子曰:‘此貴徵也。’未生而孝文帝崩,孝景帝即位,王夫人生男。”(《外戚世家》)
以后文帝、武帝的出生與始祖神話的記載性質明顯不同,這是時代社會發展的必然結果。《史記》有關記載零星,并不多見,但《高祖本紀》卻是例外,有關劉邦的神奇怪異的記載非常集中。
二、關于劉邦的神怪記載
《高祖本紀》:“父曰太公,母曰劉媼。其先劉媼嘗息大澤之陂,夢與神遇。是時雷電晦冥,太公往視,則見蛟龍于其上。已而有身,遂產高祖。”
劉邦雖然有父有母,但“感天而生”的思維告訴我們,劉邦與上古時期許多部落始祖的出生具有統一性,這其中的內在邏輯就是劉邦絕非常人。正因此,最后能成為漢朝的開國君主。班固《白虎通義》云:“圣人皆有表異。”[6]然后舉了帝嚳駢齒、舜重瞳子、禹耳三漏、皋陶馬喙、湯臂三肘、文王四乳等各種圣人異表的例子。《史記·孔子世家》載:“孔子,魯襄公二十二年而孔子生。生而首上圩頂,故因名曰丘云。字仲尼,姓孔氏。”(《孔子世家》)孔子生下來頭頂部就呈圩狀。何謂“圩”?四周高中間低的地形。因孔子為圣人,所以一生下來就與眾不同。《史記·項羽本紀》在“太史公曰”部分,司馬遷感嘆道:“吾聞之周生曰:‘舜目蓋重瞳子’,又聞項羽亦重瞳子。羽豈其苗裔邪?何興之暴也!”《史記集解》注:“《尸子》曰:‘舜兩眸子,是謂重瞳。’”意為眼中有兩個瞳仁,現代醫學和光學理論告訴我們,真正的重瞳子現象不可能存在。眼睛構造的客觀規律告訴我們,人眼絕不可能生有兩個瞳孔。如果果真如此,那就一定是生了嚴重的眼病,患了這種眼病還能成為一代梟雄,那就真是天方夜譚了![7]93不過,在中國歷史上,重瞳子的記載卻屢見不鮮。《晉書》卷二十二記載呂光“及長,身長八尺四寸,目重瞳子,左肘有肉印”。《梁書》卷十三記載沈約“左目重瞳子,腰有紫志,聰明過人”,沈約更為神奇,一個重瞳,另一個正常。《隋書》卷六十四記載魚俱羅“相表異人,目有重瞳,陰為帝之所忌”。直到《明史》中還有類似記載,“明玉珍,隨州人。身長八尺余,目重瞳子”(《明史》卷一百二十三)。這基本形成了共識,史書作者相信重瞳子的存在,這是固定的沿襲說法,其中真義,很多人包括正史作者都不一定了解,其已成為對神異之人的固定化敘事。司馬遷所記非常審慎,自己說的非常明確,只是聽別人說,并不是說他已經相信這種說法,從現代意義上對神話傳說的細節進行分析,犯了以今律古的錯誤,顯然并不合適。
這種現象規律也印證在劉邦身上。劉邦父母為布衣出身,并不神奇,也不高貴,但“圣人異表,圣人異貌”的思維告訴我們,身為開國之君的劉邦身上一定有許多不尋常之處。這里告訴了我們劉邦極為神奇的出生,神奇絕非偶然,而是多見,在一個人身上多見既久,也就成了平常。接下來,司馬遷就反復摹寫劉邦的“異貌”:
高祖為人,隆準而龍顏,美須髯,左股有七十二黑子。
常從王媼、武負貰酒,醉臥,武負、王媼見其上常有龍,怪之。
劉邦長相與眾不同,“隆準”,高鼻梁。“龍顏”,這是比喻說法,說劉邦長著像龍一樣的長面容。因此后代往往諛稱皇帝面貌為“龍顏”,皇帝高興稱“龍顏大悅”,不高興稱“龍顏大怒”,觸犯了皇帝稱為批逆龍鱗。“美須髯”,須為下頜之須,髯為兩頰之須,大致相當于今天的絡腮胡子。“左股”,左邊大腿上長著七十二顆黑子。一個人如果具備了上述一點即可算特殊,而那么多神奇怪異之征集中到一人身上,豈非咄咄怪事?高祖“好酒及色”,“常從王媼、武負貰酒,醉臥,武負、王媼見其上常有龍,怪之。”劉邦“龍蛇”附體,非同常人,嚇得武負、王媼“折券棄責”,折斷券契,不再要賬,常行此法,高祖既得酒喝,又少花錢,還神化了自己,可謂一舉多得。
從上述記載可以看出,一般開國君主往往都非同尋常,此等例子在劉邦之前已多有之,而后世亦常多見。《后漢書》上說,東漢光武帝劉秀“美須眉,大口,隆準,日角”,胡須眉毛是美的,長著大嘴,也是高鼻梁,“日角”,額骨中央部分隆起,形狀如日(《后漢書·光武帝紀》)。舊時相術家認為此為大貴之相。額頭中間骨頭隆起,暗示劉秀和真龍之間存在著血緣關系,而在隋文帝楊堅的傳記中就有點離奇過分了。《隋書》說他出生時頭上長角,“遍體鱗起”,手掌上有“王”字,上肢長,下肢短(《隋書·帝紀一》)。以現代人的眼光看,楊堅絕對屬于畸形兒,這種描寫倒不像是神話,而是異化了,十足怪物,怎能稱帝?
劉邦擁有迥異于常人的多樣“異貌”,還有常人所沒有的種種“異行”:
高祖為亭長時,常告歸之田。呂后與兩子居田中耨,有一老父過請飲,呂后因餔之。老父相呂后曰:“夫人天下貴人。”令相兩子,見孝惠,曰:“夫人所以貴者,乃此男也。”相魯元,亦皆貴。老父已去,高祖適從旁舍來,呂后具言客有過,相我子母皆大貴。高祖問,曰:“未遠。”乃追及,問老父。老父曰:“鄉者夫人、嬰兒皆似君,君相貴不可言。”高祖乃謝曰:“誠如父言,不敢忘德。”及高祖貴,遂不知老父處。
高祖以亭長為縣送徒酈山,徒多道亡。自度比至皆亡之。到豐西澤中,止飲,夜乃解縱所送徒。曰:“公等皆去,吾亦從此逝矣!”徒中壯士愿從者十余人。高祖被酒,夜徑澤中,令一人行前。行前者還報曰:“前有大蛇當徑,愿還。”高祖醉,曰:“壯士行,何畏!”乃前,拔劍擊斬蛇。蛇遂分為兩,徑開。行數里,醉,因臥。后人來至蛇所,有一老嫗夜哭。人問何哭,嫗曰:“人殺吾子,故哭之。”人曰:“嫗子何為見殺?”嫗曰:“吾子,白帝子也,化為蛇,當道,今為赤帝子斬之,故哭。”人乃以嫗為不誠,欲告之,嫗因忽不見。后人至,高祖覺。后人告高祖,高祖乃心獨喜,自負。諸從者日益畏之。
相面一事難以明說,但與高祖計謀有關應無大的問題。“及高祖貴,遂不知老父處。”我們可以從兩方面來理解:一是漢高祖是言而無信、忘恩負義之人。如果相面老人存在,說明劉邦一貫言而無信,這與滴水之恩、涌泉相報的韓信形成鮮明對比,是不折不扣的諷刺。二是該故事本就是杜撰而來,只有劉邦家人參與,別人不曉,相士本不存在,又如何能報恩呢?
當然司馬遷在記載這些奇聞異事的同時,用曲筆隱語告訴了讀者其中的奧秘之所在。如“左股有七十二黑子”,除劉邦和呂后外,似乎沒人可查證黑子的具體數目。高祖貴為天子,有龍顏異象,在酒店內多次“龍蛇”附身;此處又有斬蛇之舉,可見劉邦與一般北方人的極為怕蛇大不一樣,“龍蛇”是劉邦的“心愛”之物,非常之人才可行非常之事。“好酒及色”是原因,“常從王媼、武負貰酒,醉臥,武負、王媼見其上常有龍”是過程,最終的結果是“兩家常折券棄責”,所以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騙吃騙喝也。斬蛇,一者可能與酒有關,因此有“酒壯慫人膽”之說。一者可能是劉邦與親近之人合作搬演的一出戲。老嫗之子被殺僅老嫗一人之語,無人可證。所言赤帝子與白帝子都應是劉邦事先授意安排的產物。
異行,即神事,如果與劉邦以后的貴為天子聯系起來,那就成了圣事。我們可以將《史記》中圍繞著始祖、帝王、圣人的神神怪怪的記載概括為“奇形異貌圣事”的描寫。雖然我們前面作了客觀審慎的分析,但對一個具有嚴肅態度、嚴謹精神的文史大家來說,寫了這么多神神怪怪的東西,總是難以理解,其實這都是司馬遷的實錄。在《五帝本紀》中司馬遷說得非常清楚:“學者多稱五帝,尚矣。……而百家言黃帝,其文不雅馴,縉紳先生難言之。……余并論次,擇其言尤雅者,故著為本紀書首。”無獨有偶,在《蘇秦列傳》中也說:“然世言蘇秦多異,異時事有類之者皆附之蘇秦。……吾故列其行事,次其時序,毋令獨蒙惡聲焉。”《刺客列傳》:“世言荊軻,其稱太子丹之命,‘天雨粟,馬生角’也,太過。”《大宛列傳》:“《禹本紀》言‘河出昆侖。昆侖其高二千五百余里,日月所相避隱為光明也。’……《禹本紀》《山海經》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之也。”由此可見,看似荒誕不經的描寫,定是其來有自;比如來自于《詩經》《山海經》《左傳》《戰國策》等書的記載,而且《史記》中所記已經是經過雅化選擇后的結果,這同樣是實錄。同理,關于劉邦的一系列神神怪怪的描寫,也絕非史公一人之杜撰,是另一種意義的實錄,作為本朝的開國皇帝,當朝皇帝的曾祖父,不論從司馬遷的角度來說,還是從史學家的職業道德來說,都必須尊重事實,講求客觀實錄,所有記載都要求有來源出處。雖然在其他文獻中難以找到有關材料,這種實錄,應該來自于楚漢爭霸以來百姓一直口耳相傳至子長生活年代的各種傳說,這自然也是實錄,這是與前一類有所區別的另一種意義的實錄。如果就實錄問題對司馬遷進行批評,那就是苛責了,不單不能指責,反而我們應該佩服肯定司馬遷,由于他的這種獨特意義的實錄,給我們留下了那么多有意思、更有意義的史實史料。
三、互見法觀照下的真實態度
對于上述圍繞著劉邦而發生的“奇形異貌圣事”的描寫,司馬遷的態度是什么,著作中并未明言,只是客觀實錄,并不表明自己的態度。如果只是如此,那必定低估了司馬遷的智商。在《史記》中司馬遷有一種塑造人物、靈活安排材料的方法,那就是互見法。
一般認為,“互見法”就是司馬遷在《史記》中開創的組織安排材料以反映歷史、表現人物的一種寫作方法;即將一個人的事跡分散在不同地方,而以其本傳為主,或將同一件事分散在不同地方,而以一個地方的敘述為主。蘇洵認為互見法的根本特征是“本傳晦之,而他傳發之”。筆者一直認為,司馬遷非常高明,他的高明表現在很多方面。性質相同的事情在不同處有記載,因為涉及人物不同,事件不一,所以,記載程度就不一樣,有的只有表沒有里,有的有表有里。通過它們之間的聯系,透過表象看本質,通過別的地方的本質也能搞清楚有的地方的表象,即一個地方的問題的答案能夠用來解釋另一個地方的問題[8]123。這正是互見法的靈活運用。
圍繞著劉邦記載的如此多的奇形異貌圣事,我們前面已經提及,這是另一種意義的實錄,是對當時社會現實的實錄。那么司馬遷對這些神異之事的真實態度是什么呢?我們在解開謎底之前,首先來看與之有著密切聯系的兩則故事。
《田單列傳》先敘田單家世,再敘田單之不被人重視,后來在逃亡的危急關頭,田單“令其宗人盡斷其車軸末而傅鐵籠”,這就見出田單的富有智謀和超前意識。而此小小改造之舉保全了田氏宗族,同時也使得他在國難之時揚名于世而得以成為即墨將軍,正是因為此次的牛刀小試,才有了后面奇謀的運用,在即墨之戰中以火牛陣而出奇制勝,最終一舉收復了七十余座城池,光復了國家,自己也被封為安平君。
因為前邊的特出表現,田單被任命為齊國孤城即墨的將軍。“燕昭王卒,惠王立,與樂毅有隙”,田單利用這個機會,使用反間計,使燕國免掉了樂毅。田單“縱反間于燕,宣言曰:‘齊王已死,城之不拔者二耳。樂毅畏誅而不敢歸,以伐齊為名,實欲連兵南面而王齊。齊人未附,故且緩攻即墨以待其事。齊人所懼,唯恐他將之來,即墨殘矣。’”意為樂毅狼子野心,竟然想占齊地自立為王。燕王竟然就相信了,于是派騎劫代替樂毅。深得軍心、善于指揮的樂毅一走,再加上燕軍士兵長期離家,即墨久攻不下,這樣就為齊創造了有利條件。
田單乃令城中人食必祭其先祖于庭,飛鳥悉翔舞城中下食。燕人怪之。田單因宣言曰:“神來下教我。”乃令城中人曰:“當有神人為我師。”有一卒曰:“臣可以為師乎?”因反走。田單乃起,引還,東鄉坐,師事之。卒曰:“臣欺君,誠無能也。”田單曰:“子勿言也!”因師之。每出約束,必稱神師。
此處“神人為師”的記載頗耐人尋味,值得我們認真深入研究。關于田單之事,《戰國策》亦有記載,《史記》詳記逃亡、固齊、復齊,對田單復齊之后所記非常簡略;而在《戰國策》中則恰恰與之相反,詳記復齊之后,對復齊過程則至為簡單,僅曰:“燕攻齊,取七十馀城,唯莒、即墨不下。齊田單以即墨破燕,殺騎劫。”“燕攻齊,齊破。閔王奔莒,淖齒殺閔王。田單守即墨之城,破燕兵,復齊墟。”[9]451、461司馬遷所據若何,暫時不清楚,但可以肯定的是,必非杜撰,一定有記載依據。我們著重分析“神人教我”“神人為師”之事,此處記載得如此具體生動真切,因此所有讀者都至為清楚,這就是典型的裝神弄鬼。
無獨有偶,《陳涉世家》中亦有類似記載。陳勝、吳廣決定起事前,找占卜之人預測吉兇,占卜之人知道他們的意圖,說道:“足下事皆成,有功。然足下卜之鬼乎!”這哪里是占卜,這不就是明明白白地裝神弄鬼糊弄人嗎?負責占卜的還是凡人,沒有足夠的說服力和影響力,在那個時代,鬼神具有更大的影響力。于是陳勝、吳廣用朱砂在一塊白綢子上寫了“陳勝王”三個字,塞進別人用網捕來的魚的肚子里。戍卒買魚回來煮食,發現了魚肚中的帛書,在鬼神文化發達的時代,這樣的事情自然而然就引起了大眾的跪拜臣服。陳勝的頭上罩上了神圣的光環,這無形中讓人感覺陳勝做王是上天的旨意。接下來,趁熱打鐵,陳勝又暗派吳廣到駐地附近一草木叢生的古廟里,在夜里燃起篝火,模仿狐貍聲音叫喊道:“大楚興,陳勝王。”戍卒們在深更半夜聽到這種凄厲的鳴叫聲,都非常恐懼;恐懼之余,一個神化的得到上天庇佑的超人形象就深入人心了。一系列工作做下來,以后的起事就順理成章地易如反掌起來。
徐朔方認為:“《史記》關于劉邦的種種無稽之談都不是作者為了盡忠漢朝,為了鞏固漢朝的封建統治而捏造出來的。項羽、韓信、張良以及其他人物的傳記也混雜著性質相近的軼事。司馬遷曾經親自訪問了劉邦、項羽的起義地區,當時在偉大歷史事件過去之后不過七八十年光景。自覺不自覺地經過夸張、附會、以訛傳訛的流傳過程,最后形成這些封建迷信的傳說。它們應是司馬遷的調查所得,一些更加‘不雅馴’的說法可能已經被他淘汰。”[10]7這種理解,我們認為部分成立,從互見法的使用我們可以知道,主要的原因并不在此,絕非自然形成,而是有意為之。
劉邦母親劉媼與神結合而生劉邦,劉邦左邊大腿有七十二顆黑子,劉邦酒店醉酒后龍蛇附身,還有劉邦斬蛇起義、劉邦所居之處有龍虎之氣等等神奇的描寫,司馬遷對這些明顯荒誕不經的糊弄人的鬼把戲進行了“實錄”。為什么叫“實錄”呢?因為,司馬遷必定也不相信這些唬人的東西,但在司馬遷所生活的時代,這應該是漢統一天下的過程中以及統一以后漢朝百姓口耳相傳、婦孺皆知的事情,司馬遷不得不“如實”記錄。而在《淮陰侯列傳》中韓信被殺,表面上看是犯了謀反罪,而實際上這也是另一種意義的“實錄”,“當時爰書之辭,史公敘當時事但能仍而載之”[11]315。“爰書”,即當時的司法文書,就是當時審案判案的文書。蕭何、曹參、陳平、周勃、周亞夫、樊噲等人的傳記都明確清楚地證明了檔案文書的存在,而韓信作為大漢朝第一冤案,“爰書”自然是檔案文書的一部分,政府部門的檔案文書記載得清清楚楚,史書作者不得不“如實”記載,而對于這個功高蓋世英雄的悲慘遭遇,司馬遷是有自己的評判的。
劉邦神怪之事,田單神人教我之事,陳勝吳廣魚書狐叫之事本身都是神神怪怪的記載,性質上具有緊密的聯系,完全可以歸于互見法的范疇,但不同處的記載程度不同,我們通過別處的“里”,如田單故事、陳涉故事的真相本質,就能知曉劉邦神怪現象表象的現實本質之特性。劉邦神化自己的出生,關于劉邦身上種種神奇的描寫,是為了神化自己,同樣是為了達到田單、陳涉的目的——給自己披上一層神秘的面紗,為了麻醉蒙蔽廣大的人民群眾,一句話,就是為了達到“君權神授”的目的。
《左傳》中說得好:“國之大事,在祀與戎。”“戎”指軍隊、戰爭,槍桿子里面出政權,這個道理大家都懂;“祀”指祭祀,通過宗教把大家的思想控制起來,就是狠抓意識形態。“天人感應”是漢代重要哲學課題,董仲舒大力提倡之。董仲舒認為:“天者,萬物之祖,萬物非天不生。”[12]410“天之生萬物也,以養人。”[12]151自然,劉邦為母親感天神而生——“感生”,這樣做的目的是神化了自己的出生,自己不是凡人,為上天所生,從而給自己戴上了一個神圣而神秘的光環。
在科學并不發達的古代,編造這樣的奇聞異事,非常容易讓人相信。百姓相信的結果就是神化了自己。一般說來,開國皇帝神化自己的目的非常明確,因皇帝是上天之子,前代皇帝照樣是上天之子,那么,這個權力是上天所賦予的,普通人無權輕易奪去,有資格決定改朝換代的只有至高無上的上天。因此,赤帝子斬白帝子的故事,告訴我們劉邦的代秦建漢是上應天命,這叫君權神授。這就進一步告訴人們,由秦到漢的天命的交接是合法的,已經得到了上天的應允,老百姓自然就得乖乖順從、臣服。
再如:
秦始皇帝常曰:“東南有天子氣。”于是因東游以厭之。高祖即自疑,亡匿,隱于芒、碭山澤巖石之間。呂后與人俱求,常得之。高祖怪問之。呂后曰:“季所居上常有云氣,故從往常得季。”高祖心喜。沛中子弟或聞之,多欲附者矣。
此處之“氣”,指氣數,主吉兇之氣。古代方士稱可通過觀云氣預知吉兇禍福。“天子氣”即預示將有天子出現之氣。秦始皇擔心天子氣對自己的統治有害,于是東游以鎮住其氣。
以上描寫明顯受到了古老文化傳統中的“天人合一”觀念,以及“感生異貌”思想的影響。無疑,從科學的角度來看,這些記載確屬無稽之談。但是我們并不能因此說司馬遷的《史記》不合“正史”之要求。這用“實錄”史觀解釋不過去,只能說,這種傳奇性的記載體現了司馬遷“愛奇”的追求。如果我們理性分析一下,就會發現此種做法又不僅僅是“愛奇”而已。因為在司馬遷生活的時代,上述神奇古怪的故事傳說應該眾口傳誦、婦孺皆知。司馬遷非常清楚,此類事件純粹子虛烏有,但司馬遷又不得不“如實”記錄。因為劉邦的表面上離奇古怪的事情從根本上來說還是劉邦自己一人的“獨創”,算不上嚴格意義上的好奇。所以從這個意義上來說,這又是客觀的實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