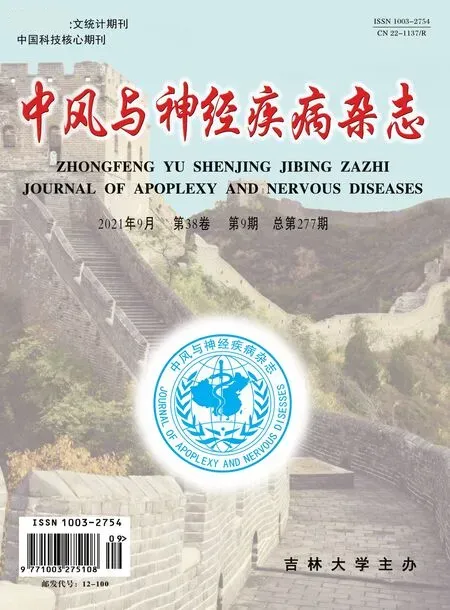特發性面神經麻痹的研究現狀
2021-01-03 10:50:01韓颶倩綜述溫世榮潘玉君審校
中風與神經疾病雜志
2021年9期
關鍵詞:研究
韓颶倩綜述, 溫世榮, 潘玉君審校
特發性面神經麻痹(idiopathic facial nerve palsy,IFP),可表現為面部肌肉無力、癱瘓,舌前2/3味覺減退,聽覺過敏或耳后疼痛,耳部及面部皮膚感覺障礙[1]甚至繼發結膜或角膜損傷,部分患者會經歷復發,遺留嚴重的后遺癥,甚至需要整形或手術的干預,影響了生活質量。過去的幾年中,研究者們進行了大量的研究,現就病因、復發情況、治療及預后標志物等相關信息綜述如下。
1 概 述
特發性面神經麻痹亦稱為面神經炎或貝爾麻痹,是非特異性炎癥所致的急性單側周圍性面癱,須排除先天性綜合征、創傷、腫瘤、醫源性損傷、中耳炎等感染性疾病方可診斷。發病機制涉及神經水腫、壓迫、缺血和變性等,癥狀通常在3 d內達高峰。IFP為周圍性面癱最常見的原因,占60%到75%[2]。國外報道發病率為(11.5~53.3)/10萬[3],發病年齡及性別無差異。
2 病 因
2.1 遺傳因素 國內外已有多篇文獻[4,5]對家族性面神經麻痹的譜系圖進行了描述,認為它是常染色體顯性遺傳,特點是低外顯率或可變外顯率,即家族性面神經麻痹可能是繼發于遺傳性人類白細胞抗原(human leukocyte antigen,HLA)的自身免疫性疾病。盡管2.4%~28.6%的IFP具有遺傳性,但目前使用高分辨率染色體微陣列分析,尚未能檢測到候選易感位點[6],需要進一步應用全基因組外顯子組進行測序。
2.2 面神經管解剖結構異常 使用CT和MRI成像測量不同節段面神經管直徑的研究顯示面神經管最窄的部分為迷路段和鼓室段[7,8]。Celik等[7]發現患側顳骨面神經管迷路段平均寬度明顯小于健側,而其它節段無顯著差異。……
登錄APP查看全文
猜你喜歡
體育科技文獻通報(2022年3期)2022-05-23 13:46:54
天津外國語大學學報(2021年3期)2021-08-13 08:32:18
遼金歷史與考古(2021年0期)2021-07-29 01:06:54
科技傳播(2019年22期)2020-01-14 03:06:54
遼金歷史與考古(2019年0期)2020-01-06 07:45:20
民用飛機設計與研究(2019年4期)2019-05-21 07:21:24
電子制作(2018年11期)2018-08-04 03:26:04
汽車工程學報(2017年2期)2017-07-05 08:13:02
國際商務財會(2017年8期)2017-06-21 06:14:14
電子制作(2017年23期)2017-02-02 07:17: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