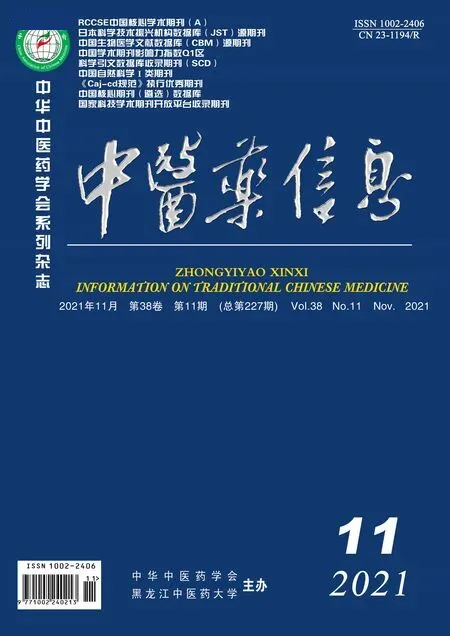《外臺秘要方》所見仲景方證考
楊頔,田永衍
(1. 甘肅中醫藥大學,甘肅 蘭州 730000;2. 河西學院絲綢之路中醫藥研究中心,甘肅 張掖 734000)
仲景《傷寒雜病論》,于東漢末年問世不久便由于兵火戰亂遭到散佚,雖經王叔和等后世醫家整理以及北宋校正醫書局的校訂幸存下來,但宋本《傷寒論》《金匱要略》與仲景之舊已有一定差異。所以考察唐代以前《傷寒雜病論》的流傳情況對《傷寒雜病論》的研究具有重要意義。
《外臺秘要方》一書,為唐代學者王燾所撰,約成書于公元752年(唐玄宗天寶十一年),是一部卷帙浩繁的大型醫學方書,也是與《千金方》和《醫心方》相似的一部大型醫學總集。由于王燾援引了許多唐以前失傳的典籍,可謂“上自神農,下及唐世,無不采擷”,故其文獻價值與史料價值顯得尤為珍貴。通過對《外臺秘要方》中所存仲景方證的考辨,可以探尋目前為數不多對此類方證的流傳記載,對比差異,結合史實,從而窺見仲景學術思想在唐代前后的發展及其對后世醫學的啟示意義。
1 《外臺秘要方》中仲景方證條文考
目前存世的《外臺秘要方》版本較多,保存比較完整的當屬靜嘉堂本。但由于尚無條件見到原本,而且影印本字跡模糊,部分不易辨識,故本研究以近年來流傳較廣,藏于中國中醫科學院圖書館的明程衍道刻本為底本校勘,2011年由中國醫藥科技出版社出版的《外臺秘要方》為據。仲景著作原文,則參考2005年人民衛生出版社整理出版的宋本《傷寒論》和《金匱要略》。
《外臺秘要方》直接引錄了唐代以前的醫書和諸家言論共56 種,加上間接引用,不下百種之多。據筆者統計,當中明確指出直接引用仲景方證的條文有74條。其中包括內容基本與宋本《傷寒論》《金匱要略》相一致的方證;在方論內容、方劑使用等方面不盡相同的方證;以及仲景佚文方證。茲分述如下:
1.1 《外臺秘要方》與《傷寒雜病論》方證條文內容基本一致者
方證的方劑名稱與藥物組成基本相一致的共有47 條,分別為小建中湯、大承氣湯、小青龍加石膏湯、大柴胡湯、柴胡加芒硝湯、柴胡桂枝湯、半夏散及湯、白虎加人參湯、真武湯、桂枝湯、桂枝去桂加茯苓白術湯、梔子豉湯、大陷胸丸、大柴胡湯方、半夏瀉心湯、文蛤散、小陷胸湯、甘草瀉心湯、大陷胸湯、白散方、葛根湯、百合知母湯、百合雞子湯、豬膏發煎、麻黃醇酒湯、柏葉湯、硝石礬石散、牡蠣湯、蜀漆散、豬苓散、小半夏湯、小半夏加茯苓湯、大半夏湯、黃土湯、烏頭赤石脂丸、抵黨烏頭桂枝湯、越婢加半夏湯、桔梗白散、栝樓薤白白酒湯、三物備急丸、調胃承氣湯、桂枝附子湯、當歸生姜羊肉湯、豬苓湯、四逆湯、甘草干姜湯和炙甘草湯。
上述方證條文在宋本中對校考證,我們可以發現兩點:一是王燾引述仲景方證時采用的稱謂為“仲景論”“仲景《傷寒論》”“張仲景傷寒論”“仲景”“張仲景”五種,但經考證發現,其在內容上不但包含了宋本《傷寒論》的內容,還包括了宋本《金匱要略》的內容,換言之,王燾所見即為傷寒與雜病部分的一個合集版本;二是從東漢末年到唐代時期,《傷寒雜病論》在傳抄的過程中,除了毀損、脫文、妄增等令讀者難以卒讀的因素,還有人為有意修改潤色的現象存在。如:
《外臺秘要方·第二卷·傷寒狐惑病方四首》:又瀉心湯,兼療下痢不止,心中愊堅而嘔,腸中鳴者方。
半夏半升(洗),大棗十二枚(擘)[1]。從藥物組成的記載中得知,此處的瀉心湯方劑實際上為甘草瀉心湯,狐惑病及甘草瀉心湯方證在《金匱要略》中均可參見,但并未找到與上述《外臺秘要方》所對應的條文,品讀發現此條并非論述甘草瀉心湯治療狐惑病的相關內容,遂參考《傷寒論》,發現在卷第四,卷第九,卷第十均有此方的論述且相同:“其人下利日數十行……腹中雷鳴,心下痞鞭而滿……甘草瀉心湯主之”[2]。
“下痢不止”與“下利日數十行”“心中愊堅而嘔”與“心下痞鞭而滿”“腸中鳴者”與“腹中雷鳴”等表述及涵義十分接近,不難看出二書中此方的主癥基本相同。
再如《外臺秘要方·第七卷·心下懸急懊痛方四首》中言:仲景《傷寒論》心下懸痛,諸逆大虛者,桂心生姜枳實湯主之方[1]。
上方在《金匱要略方論·卷上·胸痹心痛短氣病脈證治第九》中可見:心中痞,諸逆,心懸痛,桂枝生姜枳實湯主之[3]。可見《外臺秘要方》在描述此方病證表現時未記入“心中痞”,其余內容均與《金匱要略》相同。依據《金匱要略》我們可知桂姜枳實湯多用于治療心下滿悶不舒的心系病證,似乎王燾對此方的認識有失偏頗。但支分節解,我們發現緊接上方,《外臺秘要方》在下文中援引《千金要方》中載:“《千金》心下痞,諸逆懸痛,桂心三物湯主之方。桂心(二兩)膠飴(半斤)生姜(二兩)”[1]。仲景喜愛運用枳實,如橘皮枳實生姜湯,枳術湯等。枳實能破氣化痰散結、消積除痞,是治療氣逆飲停心懸痛的良藥,但此處用膠飴替代枳實,為何如此?筆者以為,實際上這反映出唐代以后的醫家更為注重此方對脾胃功能的調整,漢唐經方在傳承的過程中,根據臨床經驗,將經方驗之臨床,必會存在不斷調整藥味,劑量,煎煮方法的過程。仔細分析發現孫思邈將“九痛丸”“烏頭赤石脂丸”以及我們提到的桂心三物湯都歸于《千金要方·卷十三心臟方·心腹痛第六》的內容之中,《長沙藥解》亦曰:“膠飴補脾精,化胃氣,生津,養血,緩里急,止腹痛”[4]。印證了膠飴的功效,而《金匱要略》中所用飴糖之旨,均以甘溫補脾、建中為目的,除此之外再別無他用。《方機》本方主治曰:“逆滿,吐水,不受水藥者。”有文獻也記載了用該方治療功能性消化不良,收效甚佳[5]。所以王燾引述《千金要方》中重用膠飴而去枳實的桂心三物湯,可見其也意識到心系疾病往往帶有胃脘滿悶,按之柔軟不痛這一癥候表現,故不排除王燾是根據個人臨床經驗或喜好加以修改潤色,這對于我們現今桂姜枳實湯的新用及加減也有一定啟示意義。
1.2 《外臺秘要方》與《傷寒雜病論》方證條文內容有明顯差異者
方劑名稱不同,藥物組成相同;方劑名稱相同,藥物組成不同;主證相同,用方不同三類有明顯差異的條文我們共發現22 條,分別為小柴胡桂姜湯、茵陳湯、干姜黃連人參湯、黃芪建中湯、葛根黃連湯、百合滑石代赭湯、茵陳蒿五苓散、梔子枳實豉大黃湯、二物大烏頭煎、附子白術湯、黃芩湯、大鱉甲煎、桂心生姜枳實湯、通脈四逆湯、半夏加茯苓湯、大黃黃檗皮梔子硝石湯、黃耆芍藥桂酒湯、桂枝湯加黃耆五兩方、雄黃熏法、漬百合水洗身法、小橘皮湯、百合生地黃湯。
王燾排比文獻,章法有序,其直接引用的這22 條仲景文獻與宋本相比,在表述方法、方劑運用和實質方論等方面都有一定差異,比較清晰地反映出王燾所見張仲景著作的此版面貌,應比定型于宋代的《傷寒論》《金匱要略》約早300 余年,雖無法確認其與宋本有直接傳承關系,但借助《外臺秘要方》,可試圖分析和論證仲景方證在漢唐經方傳承的過程中,文字不斷潤色,條文之間的內在聯系更加嚴密的過程。以下舉例說明,可見一斑。
《外臺秘要方·第一卷·論傷寒日數病源并方二十一首》中言:仲景《傷寒論》:‘傷寒四五日,身熱惡風……小柴胡湯主之方。柴胡半斤栝樓根四兩桂心三兩黃芩三兩牡蠣三兩甘草炙,二兩干姜三兩’。上七味,切,以水一斗二升,煮取六升,去滓,更煎取三升,溫服一升,日三服。初服微煩,溫覆汗出者,便愈也[1]。
《傷寒論·卷第三·辨太陽病脈證并治中第六》:“傷寒四五日,身熱惡風……小柴胡湯主之”[2]。
通過比較,我們可以發現:除了《外臺秘要方》所附方劑為柴胡桂枝干姜湯,《傷寒論》卻運用了小柴胡湯這一明顯差別以外,其余論述二書完全相同。究竟此證對應何方劑,孰是孰非我們要從《傷寒論》第96條小柴胡湯方后加減法進行分析,96 條小柴胡湯加減:“若脅下痞鞕,去大棗,加牡蠣四兩;若渴者,去半夏,加人參合前成四兩半、栝樓根四兩;若不渴,外有微熱者,去人參,加桂枝三兩,溫覆微汗愈。”對應到上述癥狀加減變化后為:柴胡半斤,黃芩三兩,桂枝三兩,甘草三兩(炙),生姜三兩(切),牡蠣四兩,栝樓根四兩。這與《外臺秘要方》所記載的“柴胡桂枝干姜湯”除干姜、生姜的區別及個別藥物的劑量不同之外,幾乎如出一轍。漢末《名醫別錄》[6](184—220年)首次將干姜與生姜分別收錄,其中干姜“生犍為川谷及荊州、揚州。”這表明此時干姜與生姜在產地上才有所區分,可見在此之前,仲景時期干姜、生姜兩者功效基本相同。我們分析第99條病機后認為此證為水飲在內蘊結,太陽少陽合病。對于此證治療,應給予柴胡、黃芩以清泄少陽郁熱,栝樓根、牡蠣滌飲散結,桂枝解表兼以溫陽化飲,干姜散寒,與炙甘草同用可健脾行水;炙甘草亦可調和諸藥,諸藥合一既可使太少清解、表里調和,又可使氣機舒暢、水飲溫化[7]。故筆者以為《外臺秘要方》在此方證中記載更為準確。
又《外臺秘要方·第六卷·雜療嘔吐噦方三首》引述仲景《傷寒論》中飲家與支飲后:“又干嘔下痢,黃芩湯主之方。黃芩三兩人參三兩桂心二兩大棗十二枚半夏半升,洗干姜三兩”[1]。上方與《傷寒論》的黃連湯極其相似,《傷寒論·卷第四·辨太陽病脈證并治下第七》:“傷寒胸中有熱……黃連湯主之。黃連三兩甘草三兩,炙干姜三兩桂枝三兩,去皮人參二兩半夏半升,洗 大棗十二枚,擘”[2]。
《金匱要略·方論卷中·嘔吐噦下利病脈證治第十七》可見:“干嘔而利者,黃芩加半夏生姜湯主之。黃芩三兩,甘草二兩,炙芍藥二兩半夏半升生姜三兩大棗二十枚”[3]。
與《外臺秘要方》之黃芩湯相比,《金匱要略》黃芩加半夏生姜湯治干嘔而利者,主治上無差別,方藥組成上差異較大。東洞翁定義本方曰:“心下痞硬,干嘔下利而上沖者。”又曰:“與彼治黃芩湯證而嘔逆者有別也。”然此別欲詳論之,黃芩加半夏生姜湯方證為純陽證,有腹部攣急者,《外臺秘要方》黃芩湯方證為陰陽參半,方中有人參、干姜,故兼陰證也;無芍藥、甘草,故腹部攣急輕;有人參,故有心下痞硬;含桂枝,故有上沖之候。仔細觀察王燾記載的黃芩湯組成,我們可以發現其與《傷寒論》中的黃連湯略同,以黃芩易黃連而去甘草,蓋即瀉心湯之變化。此條后“疑非仲景方”(為叔和按語或為宋臣校勘加注的文字)也值得引起注意,其云“疑者”,則不敢加以臆斷,不禁讓人有此方是否出于一人的疑問。故《外臺秘要方》之黃芩湯未必出自仲景醫方,倘若出自仲景,是由黃連湯加減或半夏瀉心湯之變化,仍無法做出定論。
再如《外臺秘要方·第十六卷·肺虛勞損方三首》載:“又建中湯……補氣方。黃芪芍藥各三兩……飴糖十兩”[1]。
《金匱要略·方論卷上·血痹虛勞病脈證并治第六》載:“虛勞里急……黃芪建中湯主之。宋臣注文……及療肺虛損不足,補氣加半夏三兩”[3]。
宋臣注文“補氣加半夏三兩”引發學界討論,林總各種學說,無乎以下幾點:①半夏化結散痞去腹滿;②以瀉為補,半夏除肺中濕邪;③非原著所出,為后人增入[8]。反觀《外臺秘要方》這一方證,藥物組成即為黃芪建中湯加半夏五兩,用于治療虛證,可補氣。我們有理由相信宋臣注文時參考了此條方證,認為加一味半夏可治療氣短,隨即作出補充。《金匱要略》中類似此種加減用藥頻繁使用,如水飲病苓甘五味加姜辛半夏杏仁湯;少陽病中小柴胡湯加減等等,所以該處也體現了仲景寫作的常規方式,不排除仲景本人所述的可能性,但具體研究仍需其他古籍佐證。
2 《外臺秘要方》中仲景方證佚文考
在《外臺秘要方》直接引用的74 條仲景方證中,有一小部分不見于宋本《傷寒論》和《金匱要略》。這一小部分賴《外臺秘要方》得以保存,并流傳下來,共有4 條,分別為五苓散治黃疸、黃汗吳藍湯、療瘧辨瘧、橘皮枳實湯之主治。
《外臺秘要方·第四卷·黃疸方一十三首》載:“又五苓散,利小便,治黃疸方。豬苓三分,去皮……多飲暖水,以助藥勢,汗出便愈。忌大酢、生蔥、桃李、雀肉等”[1]。《外臺秘要方·第四卷·黃汗方三首》言:“療黃疸身腫……黃汗吳藍湯方。吳藍六分芍藥麥門冬去心……以水二升,煎取八合,去滓。空腹,分二服,未效再合服”[1]。《外臺秘要方·第五卷·療瘧方二十一首》載:“又辨瘧,歲歲發……皮上必粟起”[1]。《外臺秘要方·第十二卷·胸痹噎塞方二首》:“胸痹之病,胸中愊愊如滿……橘皮枳實湯主之方。橘皮(半斤)枳實(四枚,炙)生姜(半斤)上三味,切,以水五升,煮取二升,分再服”[1]。
五苓散方療黃疸以“又”引起,雖然沒有冠以稱謂,但因前一條已冠“仲景《傷寒論》”稱謂,且為前一條的變證變方,因此可視為直接引用仲景文獻。且《千金要方·傷寒發黃第十四》中也發現了五苓散療黃疸的引述:“治黃膽利小便方。豬苓茯苓澤瀉白術桂心(各三十銖)上五味,搗篩為散,渴時水服方寸匕,極飲水即利小便,及汗出愈。”學界也普遍認為此處引自仲景方。而《傷寒論》中有關五苓散證的條文有8 條,《金匱要略》中有3條提及五苓散,均未提到治療黃疸一病。故我們能夠通過《外臺秘要方》的記載窺見唐以前此類方劑的應用和主治概況,使之更加完整化。黃汗吳藍湯存在是仲景佚文的可能性,原因一是根據王燾固定的體例來看,若非脫失掉文字,那么此條必遵從前條的稱謂,即“仲景《傷寒論》師曰”;二是條文后注文“此方未詳所出”。療瘧辨瘧同,毋庸置疑王燾著書體例統一,基本上是根據病名分篇,引述一本典籍中的幾條方癥,接著更換文獻,繼續收錄。故療瘧辨瘧上文的兩段與《金匱要略》相同,下文一段也在《金匱要略》中完整體現,那么此段必是傷寒佚文無疑。橘皮枳實湯之主治在獨有佚文中較為典型,《金匱要略》論述橘皮枳實湯:“胸痹,胸中氣塞,短氣,茯苓杏仁甘草湯主之,橘枳姜湯亦主之[3]。”但從《外臺秘要方》我們可得到此證對應的方劑只有茯苓杏仁甘草湯,而橘皮枳實湯主治并非如此。五苓散與橘皮枳實湯在宋本《傷寒論》《金匱要略》為何虧失掉部分主治及癥狀,究其原因筆者以為在發明造紙術以前,古書多著于竹帛,《傷寒雜病論》傳寫既久之后,遭錯簡脫簡衍訛之命運便在所難免。
就張仲景《傷寒雜病論》傷寒部分而言,目前可見較為完整的傳本除通行宋本外,還有王叔和的《脈經·卷七》本,孫思邈《千金翼方》卷九卷十本,《太平圣惠方·卷八》本等。通過比較各個傳本,我們發現不同傳本記載的方證均存在一些差異。故筆者認為推崇盲信“宋本”必然會產生問題,為了揭示仲景方證最真實的內涵,我們不應局限于“宋本”,而應沿襲前人之論,博采眾家之方,以漢唐醫籍補之缺佚,義難明者,疑之可也。做到若欲求源,首當求全。這樣也有利于我們對仲景臨床思維有更深度的發掘,更好地指導和啟迪中醫臨床實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