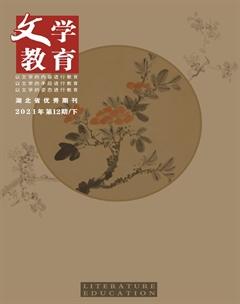《靈感女孩》中華人男性氣質危機的形成原因
董曉燁 付欣雅
內容摘要:譚恩美是20世紀著名的美籍華裔女作家,創作了一系列深受讀者喜愛的暢銷作品,其中她的第三部長篇小說《靈感女孩》以同父異母的李鄺和奧利維亞之間的姐妹之情為線索,刻畫了具有沉默、無能、魯莽及冷漠等刻板化形象,呈現邊緣性男性氣質的華人男性。以瑞文·康奈爾的男性氣質理論為依據,從女性主義、東方主義以及作者對中國文化的誤讀三個方面分析小說中華人男性氣質危機的形成原因,旨在揭示出華人男性的邊緣性男性氣質所引起的危機與困境以及華人男性氣質的可建構性。
關鍵詞:《靈感女孩》 男性氣質理論 華人男性氣質危機 女性主義 東方主義
20世紀七八十年代是美國華裔文學興起與繁盛的時期,作為這一時期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譚恩美為美國華裔文學的發展做出了巨大的貢獻。《靈感女孩》是譚恩美于1995年出版的一部暢銷小說并入圍了1996年的柑橘文學獎。譚恩美在對奧利維亞和她同父異母的姐姐李鄺之間的姐妹關系進行敘述時,一如既往地刻畫了具有沉默、無能、粗魯等刻板化形象的華人男性。本文將結合瑞文·康奈爾的男性氣質理論,探究小說中華人男性呈現出的邊緣性男性氣質以及他們所面臨的嚴重的男性氣質危機。
一.女性主義的沖擊
“在歷史上,女性主義運動是性別政治中最重要的運動。”女性主義思潮不僅為華裔美國文學注入了新的生機與活力,為華裔作家的寫作創造了文化背景,而且極大推動了男性氣質研究的興起和后續的發展。譚恩美通過描寫華人女性的內心活動和個人經驗,解構傳統女性氣質,將女性作為敘述主體,挑戰華人男性的權威,導致他們的日漸“去勢”和男性氣質危機。
女性主義對華人男性氣質危機造成的影響首先體現在女性氣質的威脅。女性不再固守傳統的性別規范,不再滿足男性的需求和期望,試圖打破生產關系和權力關系中賴以維系的父權制和勞動分工。在《靈感女孩》中,作者跨越了傳統理想女性氣質的藩籬,重構了一種具有反叛精神、獨立意識的現代女性氣質。在小說中,鄺的父親盜用了杰克·伊的姓名和身份后,毫無迷戀地擺脫了他的過去,去美國開始了新的生活,并娶了一個白人妻子組建起新的家庭。然而在他面臨死亡時,他妻子的亡魂出現在床腳并警告說:“召回你的女兒,否則死后就要受到報應。”在妻子女性氣質的威脅下,鄺的父親立即按照她的要求將鄺接到美國。鄺的母親的出現對丈夫的男性氣質構成了威脅,削弱其男性力量,造成他的焦慮和恐懼。此外,鄺對其丈夫喬治的男性氣質也構成了沖擊。在喬治對鄺的話語進行回應時,他并沒有發揮傳統男性在家庭領域的主導作用,駁斥妻子的意見,而是“點著頭”、“嘟囔著”、“不滿地嘟囔著”。鄺作為中國女性雖然在美國受到種族主義的歧視,但沒有讓性別主義對她進行打壓,而是“找了個好對象,給我帶來了運氣。”鄺打破了傳統的性別角色規范,選擇外出工作,而這也被認為是對華人男性的“家長地位和男性氣質的威脅。”
女性主義對華人男性氣質危機的沖擊還體現在敘事方式的壓制上。譚恩美的多數作品都是將女性作為敘事主體,審視男性的表現及心理活動,華人男性在作品中被剝奪了話語權,成為了沉默的旁觀者。雙重敘事聲音和第一人稱敘事視角可以說是譚恩美文本結構中的一大特點,《靈感女孩》也不例外。鄺的回顧性敘述與奧利維亞現實生活的融合不僅實現了過去與現在之間的相互轉化,而且還構成華人男性氣質危機的主要敘事方式之一。主敘述者奧利維亞對次敘述者鄺進行觀察和言說,體現出譚恩美所秉持的西方文化立場,從而貶低華人男性形象,迎合了西方對東方的集體想象。在這兩種不平衡的敘事聲音中,華人男性在失去權力與地位的同時,也失去了英雄氣概,被刻畫為具有無能、沉默、冷漠等負面特質的男性。第二種敘事方式為第一人稱視角。在鄺和奧利維亞兩種敘述聲音轉變的過程中,作者均采用了第一人稱敘事視角。這種敘事視角雖主觀性較強,但也恰恰使男性形象更鮮明地呈現在讀者面前。申丹教授在《西方敘事學:經典與后經典》中認為敘事視角有兩種:內視角與外視角,并提出第一人稱敘述中的體驗視角和回顧性視角。在小說的后半部分,主敘述者奧利維亞所采用的體驗性內視角與鄺的回顧性外視角相結合,使敘述在陰陽兩界、前世與今生、過去與現在之間相互轉換,以更真切的方式呈現出了華人男性的刻板形象和邊緣化地位,讓我們看到他們的父權權威正在消失,突顯出他們的男性氣質危機。
譚恩美在作品中塑造了像鄺等具有反抗精神的女性,賦予她們積極向上、具有生機活力的現代女性氣質,并打破了以往的寫作傳統,將女性作為敘述主體,顛覆了西方社會對華人女性的刻板印象。然而,譚恩美僅改變了女性的地位和形象,而沒有對華人男性的生存狀況給予更多關注。正如隋紅升所說:“人們認為只有女性才是有性別的群體,女性的問題才值得被審視和研究,而男性的性別身份則被其表面的普遍性所遮蔽。”
二.東方主義的質詢
康奈爾的男性氣質理論告訴我們并不是所有的男性都是壓迫者,他們也可能是被支配、被邊緣化的客體,比如族裔男性。這些處于弱勢群體的男性面臨著巨大的困境,在他們建立男性氣質身份時不僅遭受到女性的制約,也受到來自美國主流社會以及霸權性男性氣質的阻礙。
薩義德在其著作《東方主義》中將“東方主義”簡要概括為“西方控制、重建和君臨東方的方式。”西方國家對東方及東方人的壓制不僅僅采取侵略等暴力行徑,還訴諸于文本,以語言的形式展開攻擊。美國社會利用東方主義話語模式,對華人男性的形象進行貶低,從而突顯自身的種族優勢,占據著主導地位。在《靈感女孩》中,來到美國生活的華人男性就受到了歧視與排擠:“他沒有戴眼鏡,稀疏的頭發看上去就像是給反靜電吸附產品作的一則廣告。他剛被提升為東灣地區的一家食品店的經理”;“利比—阿,喬治不能去,還沒有積下足夠多的假期。”這些話語均表明了華人男性在美國的現實生活。此外,在鄺、奧利維亞和西蒙一起前往中國,乘坐司機洛基的車時,鄺想起了她的表哥:“原來是個化學工程師,后來去了美國,可他現在只能在餐館里洗碗,因為他實在吃不消講英語,有些人甚至以為他是個白癡。”華人男性無法融入美國的社會,只能在餐館或洗衣店從事一些女性做的職業,造成了華人男子氣概的流失。到美生活的華人男性不僅在工作領域被排斥,而且語言的障礙更是加深了美國社會對他們的侮辱,認為他們只是適合做女性工作的“白癡”,使華人男性產生自卑、自棄的文化心理。
康奈爾在《男性氣質》中將支配性男性氣質定義為“性別實踐的形構,這種形構就是目前被廣為接受的男權制合法化的具體表現。”在小說中,白人男性被賦予支配性特征,擁有統治其他男性和女性的權力。而華人男性不可避免地受到美國社會、政治和經濟政策的影響,被不斷排擠在主流社會以外,成為邊緣性男性,而“邊緣性男性氣質總是與統治集團的支配性男性氣質的權威性相聯系著。”支配性男性氣質由于被賦予強大的社會地位和經濟力量,物化其他族裔男性以維護自己的霸權權威。支配性男性氣質對華人男性的壓迫首先體現在身體的優勢上。小說中主要的白人男性凱普將軍和西蒙就擁有著更健壯、更陽剛的體貌特征:“他個子很高,短須,大絡腮胡子,一頭波浪形的黑發垂落在肩膀上”;“西蒙看上去沒有任何特定的種族特征,他是完美而均衡的混合體……”相較于華人男性,美國男性的外表更具有男性魅力、更為吸引華人女性的注意。此外,美國男性往往能夠給予華人女性更多的慰藉與喜悅之情:“與西蒙在一起,我笑得更厲害,思考得更深刻,對于遠在我自己那舒適的小窩之外的生活也感到更富有激情。”
美國支配性男性氣質除了在身體上更具吸引力外,還依靠種族優勢所帶來的權力對華人男性氣質進行打壓與脅迫。在鄺前一世的記憶中,一半就受到了父親約翰遜的利用。約翰遜是凱普的朋友,他拋棄了懷孕的妻子,使其成為“外國魔鬼遺棄的太太。”妻子去世時兩腿間夾的嬰兒脖子上有著神秘的灼痕,而這成為約翰遜賺錢的工具。當一半不再具有利用價值后,他又毫不留情地將其押給凱普抵債。約翰遜自私自利的行為導致一半一生都沒有感受到真正的父愛與母愛,還要為一個“沒有忠誠、沒有祖國、沒有家庭”的凱普將軍做事。除了一半遭受到白人男性的傷害以外,小說中另一個具有代表性的華人男性老魯也受到來自白人男性凱普的殘忍對待。當凱普將軍帶領清兵沖進鬼商大屋時,老魯憤怒地喊道:“你這忘恩負義的走狗!隨即是一片刀光閃爍,沒等我們反應過來,老魯的人頭已經向我滾來。”由此可見,作為少數族裔的華人男性通常會遭受占據統治地位的白人男性的歧視、暴力甚至是殺戮。
在東方主義集體認同的影響下,譚恩美對華人男性的塑造體現出她的西方文化立場,迎合了主流社會關于東方的想象。白人男性憑借自身較高的社會地位和種族優勢輕而易舉地獲得財富和權力的同時,對華人男性進行壓迫,將其描述為被邊緣化的“他者”。而美國主流話語在對華人男性進行貶低的背后,隱藏著真正的目的:“實為控制、主宰東方,而達其稱霸世界的意圖。”
三.作者對中國文化的誤讀
作為華裔的第二代移民,譚恩美自幼生活在美國,從小便受到美國主流文化的熏陶。雖然從母親身上傳承下來的中國文化對譚恩美也造成了深刻影響,但譚恩美還是經常以西方人的視角進行思考和創作,作品中無不透露著“東方主義”情結。在對西方價值觀的認同和對中國文化不充分了解的影響下,譚恩美在作品中往往以“他者”的眼光審視中國和中國人,誤讀中國文化,迎合了西方讀者的期待視野。
譚恩美在寫作中會從中國傳統文化中選取一些元素來塑造中國和中國人的形象。在《靈感女孩》中,譚恩美在采取靈異敘事以獲得西方讀者認可的同時,引用了中國著名的歷史片段——太平天國運動,顛覆了中國對這場運動的真實論述。作者將太平天國運動所尊崇的拜上帝教描述為與基督教相似的一門宗教。班納小姐的情人凱普是一名美國高級將領,自稱也是拜上帝教的一員,會幫助客家人過上更為富裕的生活。凱普將軍在譚恩美的筆下被刻畫為具有支配性男性氣質的白人男性,與生活在舊中國的華人男性相比,不僅具有性別角色規范所規定的男性特征,而且還擁有高貴的身份和極大的權威。最后為了一己私利,凱普將軍又加入了滿清軍隊。鬼商大屋的傳教士們未來得及逃脫,就被其帶領的清兵殘忍殺害。然而,據歷史記載,中國的拜上帝教雖來源于基督教,但其宗教儀式與教義均別具一格。拜上帝教沒有教會,也沒有傳教士等神職人員。“洪秀全等人始終奉自己的宗教為正統,一直拒絕承認基督教的權威,從未以正統基督徒的身份自居”,因此小說塑造的白人男性凱普將軍與太平天國運動的聯系也就無從考證。在譚恩美書寫的太平天國運動中,華人男性遭到西方男性的迫害和殺戮,更加固化了他們無能無助的形象。
另外,當奧利維亞想更改自己姓氏的時候,母親向她灌輸了一種錯誤的思想:“中國的傳統是讓女孩保持她們母親的姓氏。”由此體現出中國男性在家中、甚至在社會和文化中無能、無權的形象。正因為對文化的誤讀,父親在孩子們的記憶中逐漸消失:“鮑伯是我所了解的唯一的父親,我一點也不記得我們真正的父親了。”而且當奧利維亞向弟弟凱文征求新名字的意見時,凱文明確表示到美國正在把亞洲取而代之,擁有中國人的姓氏并不會帶來任何好處,勸她還是使用繼父的姓。甚至連鄺也不知道父親真正的姓名:“如果我能夠知道他的真實姓名,我就會告訴他。然后他就能去陰間,向我的母親道歉。”
譚恩美在小說中大量描寫關于鬼魂、轉世和靈魂互換等靈異故事,增強了中國的神秘色彩,支持了中國人喜歡迷信的論調,滿足了西方國家對中國的集體想象。譚恩美刻畫的“虛幻中國”不僅不利于中國文化的弘揚與傳播,而且加深了華人男性所面臨的困境,使其更難以擺脫種族主義的束縛。無論他們在社會上如何拼搏,都難以逃離美國主流社會的歧視和白人男性霸權性男性氣質的打壓,在工作和生活中不斷被排斥和邊緣化,成為男性氣質危機的受害者。
在《靈感女孩》中,譚恩美在提升女性主體地位方面進行了積極探索,塑造了像李鄺一樣敢于挑戰華人男性權威的女性,華人男性逐漸喪失傳統文化賦予他們的權力。此外,與康奈爾四重性別結構中的象征關系相對應,本文發現女性作為敘事主體對華人男性氣質建構也產生了負面影響,剝奪了華人男性的話語權并消解了父權。譚恩美自稱為一名美國作家,她站在美國人的立場上將中國描寫為一個充滿神秘和迷信的國度,迎合了西方人的獵奇心理。在東方主義的影響下,白人男性的霸權性男性氣質嚴重壓迫著華人男性,他們將華人男性排斥在主流社會以外,使他們處于邊緣化地位而具有邊緣化男性氣質。最后,譚恩美對中國文化的誤讀也是造成華人男性氣質危機的一個主要原因。作者筆下充滿異國情調的中國形象迎合了西方讀者的期待,使華人男性的男性氣質飽受詬病。
參考文獻
[1]R.W.Connell. Gender: In World Perspective[M].Cambridge: Polity Press,2009.
[2]譚恩美.靈感女孩[M].孔小烔,等, 譯.杭州:浙江文藝出版社,1999.
[3]隋紅升.男性氣質[M].北京: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2020.
[4]Edward W.Said.Orientalism[M].New York: Vintage Books,1979.
[5]申丹,王亞麗.西方敘事學:經典與后經典[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
[6]R.W.Connell. Masculinities[M].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1.
[7]陳愛敏.“東方主義”與美國華裔文學中的男性形象建構[J].外國文學研究, 2005(02):78-83.
[8]夏春濤.太平天國宗教面面觀[J].文史知識,2000(02):31-36.
基金資助:黑龍江省哲學社會科學研究規劃項目“美國非裔女性文學敘事時間研究”(19WWE293)
(作者單位:東北林業大學外國語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