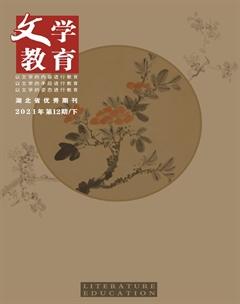論《喜福會》中“他者化”的華裔女性形象
嚴蔚霞
內容摘要:他者是自我意識的投射。譚恩美自幼長于美國,接受美國文化的教育,對中國文化不可避免會產生誤解,但華裔的身份使她在美國主流文化中受到排擠,這種尷尬的境地為她的創作提供了素材。《喜福會》就圍繞移居美國的四位女性:吳蘇圓、龔琳達、盈盈、許安美和她們出生于美國的女兒:吳精美、薇弗萊、麗娜、露絲展開敘述,勾勒出了“他者化”的華裔女性形象。
關鍵詞:《喜福》 女性主義 華裔 他者化 自我結構
譚恩美的小說《喜福會》通過塑造四對極具代表性的移民母女,呈現出在美國文化背景下的“他者化”的華裔女性從壓迫到覺醒,并對女性身份做出解構。
一.男權文化的壓迫
伍爾夫有一個“房間”理論,意思是女性要有屬于自己的“房間”以及“每年五百磅入款”,強調女性要擁有一定的經濟自主權來擺脫男權意識的監控。而舊社會的中國是父權家長制,有著“在家從夫,出嫁從夫,夫死從子”的說法。男性把握著家庭的絕對主導權,還有傳承幾千年的一系列封建陋習在壓迫著女性,不難知道女性的生存地位之低。所以,西方人眼中傳統的中國女性形象,大多只是依附別人的菟絲花,柔弱無能,沒有話語權,沒有獨立人格特征。
“這部小說成功的原因更得益于關于中國的種種異國情調的展示。①”譚恩美的生活經歷避免不了“他者化”對中國形象的誤讀和批判,“異域情調”在四位母親的回憶中很大程度上呈現出的是中國愚昧落后的丑陋形象。《喜福會》小說背景為中國戰爭時期,炮火紛飛,百姓到處逃難、流離失所,母親們的中國經歷也是多折多難。龔琳達還沒長大就被相中做洪家的童養媳,長大后就馬上嫁給小丈夫,要求生兒育女、做牛做馬,但是丈夫連性能力都沒有,顯得可笑。不僅窮苦人家女性難,富貴人家女性也難。大家閨秀盈盈受包辦婚姻嫁給花花公子,丈夫暴虐自私,到處沾花惹草,婚姻痛苦,用殺死自己的孩子來泄恨;許安美的母親被迫做了四姨太后承受侮辱無奈自殺。男性掌握著主導權,女性的能力太過于微弱無能,沒有出頭之日,無法擺脫掉社會的桎梏,這就是遭受中國男權文化壓迫的痛苦。
四位母親的女兒在美國長大,經濟獨立,有著獨立的思考能力,竭盡全力想成為真正的美國人,但是華裔的身份使得美國人不會完全認可她們,仍然處于被壓迫的地位,被美國人視為“他者”。露絲一直覺得自己是美國人,要嫁給美國人丈夫,但是她的婆婆是瞧不上這個黃皮膚的中國女人的,說她是越南人。露絲從小受母親的教導,溫柔善良,導致在婚姻中沒有主見,不敢反駁,婚姻不快樂,丈夫卻漸漸覺得她變了,不可愛了,最后提出離婚。還有麗娜與丈夫的婚姻也是,在婚后雙方實行AA制,沒有融為一個整體,在中國可以說是不可思議,母親得知后直接提出抗議,女兒后續婚姻破裂也是可以預見到的。女兒們雖說不理解、不接受中國傳統文化,成長過程中父母會潛移默化地影響到她們,思想根基中還是會存在中國文化的因子,這會被主流文化排除在圈子外。
二.他者化的母女形象
吳蘇圓在小說開頭講過一段關于天鵝的故事,她說,“在美國我會有個像我的女兒,在那兒,她無需仰仗丈夫鼻息度日;沒人會看低她,因為她將說得一口流利的英文;我要她成為一只比期望中還要好上一百倍的天鵝。②”這是母親對女兒寄予的厚望,希望他們能早日有所作為。這其實就是中國家長思想縮影,子女要聽從長輩教導,守禮節、知情重,父母權威不可撼動,子女要做的就是聽從,期待他們能早日成龍成鳳。而西方崇尚個人主義,每個人是獨立的個體,有獨立的思想,父母沒有權利也沒有責任去干涉過多孩子的生活,并且鼓勵孩子有自己獨特的思維。中西方不同的文化教育決定著不同的思想觀念,母女之間的沖突、碰撞必然是存在的。
中國母親樂于奉獻自己去培養子女,把她們的榮譽看的至高無上,他們的愛如空氣般細致入微、無所不在。在母親眼里,子女長大后也是自己的寶貝,希望她們能幸福,所以會把自己的經驗去傳授給她們,希望能有所幫助,但不同代際的溝通和從小到大積攢的矛盾讓女兒難以接收。母親認為,“在我家里只允許聽話的女兒住進來③”,女兒卻想著“我再也不要受她擺布了”,這樣母女只會一步步走向疏遠。
龔琳達的女兒在棋藝上有天賦,她就為孩子創造條件去下棋,盡管不懂下棋在女兒練習時也在旁邊默默觀看。薇弗萊就討厭母親愛炫耀的性格,所以在母親向路人夸耀自己時大膽反抗,提出不再下棋來挽回自己的面子,希望能有自己的話語權。但是母親以中國思維考慮,更注重自己在家庭中的地位,不把女兒的威脅當回事。這和美國溝通式的教育是截然不同的,也造成了薇弗萊始終渴望得到母親的認可和鼓勵,這些回憶始終會像一根刺時不時隱隱作痛。吳蘇圓希望女兒能踏入美國上流階級,努力訓練女兒做智力測試,當清潔工賺錢,并且免費給鋼琴老師做清潔來換取資源給女兒練習鋼琴。這些都不祈求回報,只是中國母親的一片真心,盡管會批評和責怪,都是出于母愛。但是女兒的思維里并沒有接收中國的母慈子孝,母親的話并不是要一味順從,她們不喜歡被干涉,生氣于被管教,接收不了自由失控的感覺,中美文化的差異讓兩代人的隔閡越來越大。
三.女性身份解構
薩義德認為“自我身份的建構牽涉到與自己相反的‘他者’身份的建構,而且總是牽涉到對與‘我們’不同的特質的不斷闡釋和再闡釋。④”中國舊社會的女性都以自己的力量做出反抗,解構社會的偏見。吳精美的母親被富商搶占后,選擇小年夜自殺,因為民間傳聞人死后三天魂魄會回人間。而且在大年初一的時候必須還清欠債,祈求來年安康。這樣吳慶就好好對待她的孩子,也是為了孩子能平安長大。琳達擺脫想這場婚姻雖不敢光明正大提出離婚,但機智利用洪家迷信的心理,用鬼魂附身的方法蒙混,機智脫身,逃離這個大宅院,去往美國開啟新生活。
《喜福會》的母女雙方視對方為他者,母親理解不了女兒的考慮,女兒不愿了解中國的文化。但是沒有母親會不愛自己的孩子,母親干涉女兒生活都是為了她們過上好日子,不走自己的老路。女兒雖說會逆反,會委屈,但心里面始終會明白這些管教都是出于無私偉大的愛。所以母親代表的中國文化和女兒代表的美國文化之間溝通、融合是趨勢。
孩子長大后都有自己的想法,婚姻開始時,女兒們都不愿意被母親干涉,美國人沒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一說,所以后來即使是有問題也不會選擇找親近的家人溝通,寧愿像美國人那樣找心理醫生。但俗話說,“姜還是老得辣”,母親的生活閱歷和見識遠比女兒高得多,在婚姻困境里也能一針見血。在麗娜與丈夫的婚姻中,麗娜選擇默默忍受委屈,可丈夫連自己不吃冰淇淋都不知道,缺乏愛護的婚姻是沒有希望的,母親用自己經歷開導,揭開傷疤,讓女兒有勇氣維護自己權益,直面矛盾。還有露絲在婚姻中不被尊重,媽媽及時告訴她,“女孩子要像一棵樹一樣挺起身子⑤”,母女關系也開始和解。
同時,母親也在逐漸適應美國文化,融入與孩子的溝通與生活中。開始琳達在女兒交了美國男朋友時,嘴里滿是挑剔,女兒也不樂意介紹。后來女兒帶男友上門,她還是滿懷熱情地招待,準備一大桌子好菜,不想給女兒丟面子。琳達也多次在男友面前強調要夸獎媽媽做的是最好吃的中國菜。雙方的愛是相互的,這讓理解成為可能,所以在瑞奇拜訪中家庭保持著和美的狀態。琳達開始介紹自己拿手菜時表現出中國人傳統的謙虛,瑞奇不懂彎彎繞繞,信以為真,琳達也沒表現出生氣。在中國講究長輩先動筷,吃飯要沉穩。吃飯時瑞奇的美式吃法無疑是尷尬,喜歡吃的直接往自己碗里弄了好幾筷子;琳達客氣地說會不會太咸,還傻傻地往里面加料。看似笨拙的行為因為都被理解了。家人們仍然熱情地教他使用筷子,吃中餐,最后告別時直呼大名也沒計較,琳達的愛讓她尊重文化的差異。為了女兒,琳達走進理發店去做頭發,雖然嘴里還是嘮嘮叨叨,但也是一個轉變。女兒借此說出多年來的芥蒂,兩人像美國家長一樣平等溝通,理解彼此,在兩人哈哈大笑中我們能明白文化的隔膜被打破。吳精美在母親去世后,她帶著母親的期望,回到中國去找尋自己的雙胞胎姐姐,當姐妹倆在機場里相擁。就是母女冰釋前嫌的象征。
譚佳美以其獨特的身份將《喜福會》中華裔女性解構,將“他者化”的偏見逐漸擊破。在當今多元化的世界中,即使中美之間有著隔閡,愛能讓一切變得和諧。
參考文獻
[1]譚恩美著,李軍,章力譯.《喜福會》[M].北京: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2016.
[2]米麗娜.他者的想象--美國華裔作家譚恩美《喜福會》中的中國形象[J].北方文學,2015(07):85.
[3]愛德華.W.薩義德.東方學[M].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9.1.426.
注 釋
①米麗娜.他者的想象--美國華裔作家譚恩美《喜福會》中的中國形象[J].北方文學,2015(07):85.
②譚恩美著,李軍,章力譯.《喜福會》[M].北京: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2016.
③譚恩美著,李軍,章力譯.《喜福會》[M].北京: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2016.
④愛德華.W.薩義德.東方學[M].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9.1.426.
⑤譚恩美著,李軍,章力譯.《喜福會》[M].北京: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2016.
(作者單位:中國計量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