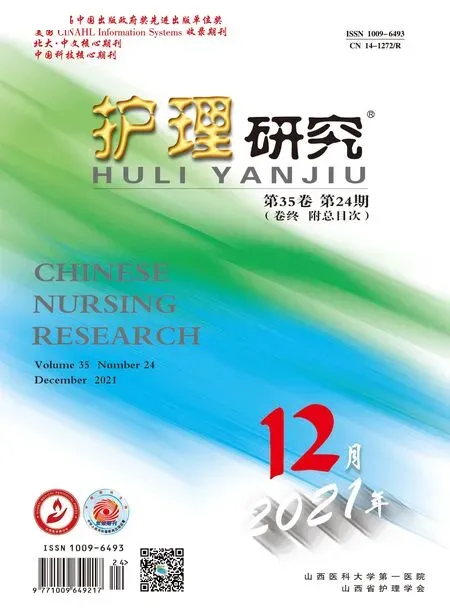超聲在ICU獲得性肌無力量化評估中應用的研究進展
劉 楊,羅 健*,劉 苗,周興婷,丁韞晗,胡夢陽
1.華中科技大學同濟醫學院附屬協和醫院,湖北 430022;2.長江大學醫學部;3.武漢輕工大學;4.華中科技大學同濟醫學院
ICU 獲得性肌無力(intensive care unit acquired weakness,ICUAW)是ICU 幸存者表現出的主要問題之一,可在病人疾病康復后持續存在。根據病理生理改變分為重癥肌病(critical illness myopathy,CIM)、危重癥神經病(critical illness polyneuropathy,CIP)或兩者并存[1]。作為影響重癥病人疾病預后的嚴重并發癥,早期評估和預防是降低其發生率的有效途徑。隨著影像技術的發展,超聲在重癥醫學領域覆蓋范圍越來越大,其顯影定量、可連續性測量、容易操作的特點及較強的抗干擾能力使其越來越受到醫務工作者的歡迎。這些特點與重癥監護的要求有著明顯的一致性[2],已被用于觀察肌肉質量與功能、評估機械通氣撤機、鑒別休克類型、評估營養不良、監測胃殘余量、篩查靜脈血栓、引導穿刺等方面[3-6]。肌肉消耗是ICU 醫生關注的重點之一,它不僅能反映疾病的嚴重程度、進展速度,還可以預測病人預后。現有研究對超聲評估ICUAW 的可靠性的認知尚不統一。本研究的目的就是分析ICUAW 早期評估的困境及超聲在肌肉測量方面的應用,綜述超聲評估ICUAW 的價值。
1 ICUAW 的主要評估方法及局限性
徒手肌力測試——醫學研究委員會評分(Medical Research Council,MRC)是ICUAW 最常用的評估工具,可評估四肢共12 組肌肉的力量,共60 分,總分低于48 分則可認為存在ICUAW[7]。其局限性在于僅能反映病人存在肌力下降,但無法指出原因[8];其次,MRC的評估也會受到病人意識的影響,往往會因肌松、鎮靜藥物的使用、ICU 譫妄的發生等延遲評估時間。研究表明,MRC 測量時間通常是在病人病情穩定可喚醒后,這段時間大概是在7~10 d[9-10],但ICUAW 在入監護室24 h 內即可發生。延遲評估可低估ICUAW 的臨床發病率。此外,MRC 評估較為主觀,觀察者之間存在差異[11]。
電生理檢查(electrophysiological,EP)通常包括神經傳導、直接肌肉刺激、針刺肌電圖等檢測[12]。相比于MRC,EP 可區分CIM 和CIP。CIM 主要特征是復合肌肉動作電位(compound muscle action potentials,CMAPs)波幅異常降低,持續時間延長,感覺神經動作電位(sensory nerve action potentials,SNAPs)正常,直接肌肉刺激時肌肉興奮性降低,針狀肌電圖上顯示肌病運動單位電位;CIP 表現為CMAPs 正常或輕度降低,SNAPs 振幅降低,伴有正常或輕度神經傳導速度降低[13]。EP 可在病人清醒且具有合作性前進行檢測,具有早期識別ICUAW 的優勢。但完整的電生理學檢查需要45~90 min 才能完成,耗時長[14]。盡管簡化的電生理測試也能準確識別CIM/CIP,但依舊無法解決組織水腫對檢查結果的影響,同時檢查結果受ICU 環境中及病人自身放電設備(起搏器等)的電干擾。且該項檢查需要專業技師實施才能確保結果的可靠性。
組織學檢查是評估ICUAW 和鑒別分型的金標準,CIP 表型的組織學改變為急性肌肉去神經支配伴1型和2 型纖維萎縮,CIM 病人活檢最常見的現象為選擇性的粗肌絲(肌球蛋白)丟失和不同程度的壞死[13]。相比于電生理改變,組織學改變出現更晚。盡管神經傳導研究結果異常,但CIP 病人感覺神經軸突變性僅在病程后期才明顯[15]。組織學檢查因其有創性、痛苦性、成本高且需要病理專家對結果進行解釋等限制了其在臨床應用。
2 肌肉超聲在ICU 中的應用
超聲技術具有測量肌肉數量和質量的巨大潛力,超聲無創檢測肌纖維壞死與組織學檢測結果一致。超聲可通過測量橫截面積和肌肉厚度得到近似肌肉質量,也可以通過肌肉回聲的灰度分析得到近似肌肉質量[16]。骨骼肌超聲早在幾十年前便已應用到ICU 環境中,用于評估危重病人營養狀況、預測臨床結局、診斷肌肉疾病等[17]。重癥病人在疾病早期即可出現肌肉消耗,股四頭肌橫截面積與肌肉消耗程度呈反比,與股四頭肌中心腱厚度呈正比。且股四頭肌最大等長自主收縮(quadriceps maximal isometric voluntary contraction,QMVC)與急慢性生理評分之間的密切關系表明,QMVC 可能隨著疾病的嚴重程度而下降[18-19]。研究表明,呼吸衰竭病人第1 周就可觀察到股四頭肌快速丟失,橫截面積減少約10%。在膿毒癥病人中,肌肉超聲能夠檢測出93%病人的神經病變[20]。早期肌肉超聲主要用于床旁超聲測量骨骼肌質量以觀察病人營養狀況和預測不良結局。大多數的研究表明,肌肉的退化可能與不良的預后有關,導致機械通氣和住院時間延長,增加醫院死亡率。由此可見,超聲技術不僅顯示肌肉的結構變化,還可以提供更多的生理見解。但肌肉結構和數量的改變與發生ICUAW 之間缺乏必然聯系,即肌肉結構和數量的改變不等同于ICUAW 的發生。而最近已有研究開始討論骨骼肌厚度變化與肌力之間的相關性。用骨骼肌厚度變化評估ICUAW 的靈敏度和特異度也很可觀。
膈肌超聲已經在ICU 病人中常規使用,用于評估和監測膈肌功能,幫助預測機械通氣病人拔管時間和撤機成功率。胸部X 線、X 線、CT 也可用于觀察膈肌結構,但無法顯示膈肌的運動狀態,且具有一定的輻射性,無法重復使用。MRI 可對膈肌的移動進行定量評估,但對技術人員的依賴性強,必須在特定空間內完成檢查,且費用高,不便在短期內重復檢查[21-22]。超聲檢查膈肌的優勢在于便攜、無輻射、重復性好、操作簡便、可連續動態觀察。研究表明,超聲測量的膈肌厚度與尸檢直接測量的膈肌厚度一致,超聲測量膈肌移動度與X 線、MRI 測量結果也是一致的,說明用超聲評估膈肌的結構和活動是可靠的[22-23]。
另外,標準化超聲圖像的獲取與操作者水平密切相關,是準確評估的基礎。大量文獻報道,使用超聲評估肌肉時,研究者內和研究者間的一致性高。且研究表明,無論操作者專業技術水平如何,都具有出色的觀察者間和觀察者內可靠性[24-25]。北京協和醫院重癥醫學科對ICU 護士進行了16 h 的超聲培訓,培訓后護士超聲評估正確率為92.53%,提示床旁超聲上手快,經過規范化培訓的人員均可以正確實施床旁超聲且研究者內部一致性高[26]。
3 超聲測量肌肉變化對評估ICUAW 的價值
3.1 四肢肌肉變化對ICU 獲得性肌無力的評估價值 肌肉質量減少是ICUAW 發生的直接原因之一。超聲對ICUAW 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股四頭肌上,通常測量點選取的解剖位置為髂前上棘與髕骨上緣連線的中下1/3,但也有研究報道在兩者連線3/5 或1/2 處[6]。Cartwright 等[27]在一組呼吸衰竭病人中進行灰度測量,評估回聲紋理,發現脛前肌的灰度平均值增加,肌肉回聲增強。脛前肌和股直肌的灰度標準差顯著降低,表明肌肉衰竭增加。但肌肉微觀結構的變化并不一定能引起宏觀改變,不能代表ICU 獲得性肌無力的發生。2015年Parry 等[10]發現股中間肌回聲強度與MRC 得分呈負相關,回聲強度越高,病人MRC 得分越低。但他未進一步計算回聲強度診斷ICUAW 的臨界值,這可能是因為研究樣本量不足。一項系統評價結果顯示超聲評估ICUAW 的可靠性尚未完全建立[28]。之后Witteveen 等[9]為了探究神經肌肉超聲評估ICUAW 的準確性,以MRC 作為評估“金標準”,按照流行病學診斷試驗方法,通過床旁超聲觀察肱二頭肌、橈側腕屈肌、股直肌、脛前肌、正中神經、腓神經,對床旁超聲評估ICUAW 的真實性、可靠性進行評價,發現神經肌肉超聲評估ICUAW 的準確性較差。肌肉超聲顯示,即使ICUAW 病人肱二頭肌和橈側腕屈肌的厚度顯著降低,橈側腕屈肌的回聲強度更高,但三者對有無ICUAW病人的區分度低(AUC 分別為0.680,0.645,0.608),而其他肌肉間在兩組病人中差異無統計學意義。同樣,神經超聲顯示,在ICUAW 病人中正中神經橫截面積較小,但其區分度依舊較低(AUC 為0.667)。另一個與其類似的研究發現,床旁超聲測量橈側腕屈肌厚度<1.17 cm 時,AUC=0.742,敏感度為73.75%,特異度為73.1%;測量股四頭肌厚度<1.98 cm 時,AUC=0.787,敏感度為86.7%,特異度為73.1%;測量脛前屈肌的厚度<2.04 cm 時,AUC=0.817,敏感度為86.7%,特異度為69.2%;三者對機械通氣病人并發ICUAW 具有診斷價值,而肱二頭肌厚度對ICUAW 無診斷價值[29],這與Witteveen 等[9]的結論不一致。這兩組實驗僅測量了一個時間段的肌肉結構,這種結果的差異可能是檢查時間段不同而導致的。Formenti 等[30]認為以入院超聲結果為基線,若在ICU 期間肌肉厚度減少20%,橫截面積減少10%,羽狀角減少5%,回聲強度增加至少8% 或可成為評估ICUAW 的合理指標。2019年王茂生等[31]發現超聲下股直肌橫截面積下降9.24%可作為評估ICUAW 的新工具。2020年李若祎[32]連續1 周使用超聲觀察重癥病人股四頭肌的變化發現:當ICU 病人住院3 d 股直肌橫截面積減少6.0%,或住院5 d 股直肌厚度減少14.5%,或住院7 d 股中間肌厚度減少19.9%,可以較好地鑒別ICUAW 病人(AUC>0.75)。該項研究的優點在于作者不僅討論了單個肌肉參數與ICUAW 的關系,還觀察了肌肉參數隨時間變化的連續過程。
3.2 膈肌變化對ICU 獲得性肌無力的評估價值 除四肢外,膈肌也是ICUAW 累及的肌肉之一,病人可表現為困難拔管、機械通氣時間延長、呼吸衰竭,膈肌力量同樣是影響ICU 死亡率的主要決定因素[33]。反之,長期機械通氣也是ICUAW 的已知危險因素之一,不當的通氣模式可導致膈肌功能紊亂,氧化應激和蛋白水解可導致膈肌萎縮[34-35],神經肌肉阻滯劑的肌松作用和神經毒性也會影響膈肌的功能。膈肌萎縮從機械通氣1 d 后就可發生,最大的厚度下降發生在機械通氣72 h 內。一項研究顯示,膈肌厚度在機械通氣1 d 后下降了9%,2 d 和3 d 后分別下降了21%和26%,且ICU重癥病人膈肌的消耗速度比四肢肌肉更快,膈肌功能障礙的發病率是ICUAW 的兩倍,尤其是在膿毒血癥病人中[36-38]。超聲可以充分展現膈肌的特殊性,不僅可以測量動態和靜態的膈肌厚度,還可測量膈肌收縮速度和幅度[38]。一般認為最佳的隔膜超聲檢查是在病人存在自主呼吸或非機械通氣期間。也有研究在機械通氣過程中尋找合適的膈肌超聲參數,盡可能消除機械通氣對膈肌的影響。
超聲下膈肌無力(diaphragmatic weakness,DW)被定義為膈肌移動<11 mm,或膈肌運動矛盾。但研究表明DW 與ICUAW 的相關性并不高,也就是說DW≠ICUAW。想通過膈肌超聲評估ICUAW,還需進一步研究。楊莉[22]發現,在機械通氣病人膈肌超聲相關指標中,呼氣末膈肌厚度(thickness at end expiration,TEE)和膈肌收縮度(diaphragmatic thickness fraction,DTF)是最敏感的指標,能夠很好地反映膈肌功能,可作為早期評估ICUAW 的工具:DTF=16.3%作為臨界值時,AUC=0.84,評估ICUAW 的靈敏度為0.86,特異度為0.80;TEE=0.17 cm 作為臨界值時,AUC=0.80,評估ICUAW 的靈敏度為0.71,特異度為0.74。盡管上述研究具有較好的靈敏度和特異度,但相關研究數量少,膈肌超聲評估ICUAW 的價值還需更多的研究支持。
4 小結
超聲憑借無創、便攜、精確的優勢,成為危重病治療中有吸引力的工具,其對ICUAW 的評估價值也得到了一定的肯定。骨骼肌力量喪失是危重病人的典型癥狀,也是ICUAW 的臨床表現之一。超聲評估四肢肌肉和膈肌不僅可以早期評估ICUAW,還可以預測危重病人的不良結局。但超聲最佳觀察指標和診斷臨界值尚不統一,如何突破肥胖和水腫帶來的成像問題,如何正確利用超聲參數,都需要進一步研究。即便有些參數在現有研究中被認為是沒有意義的,但其動態變化,或與其他參數之前的函數關系,可能會在評估ICUAW 上有一定價值。超聲可能會成為及早識別ICUAW 的有用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