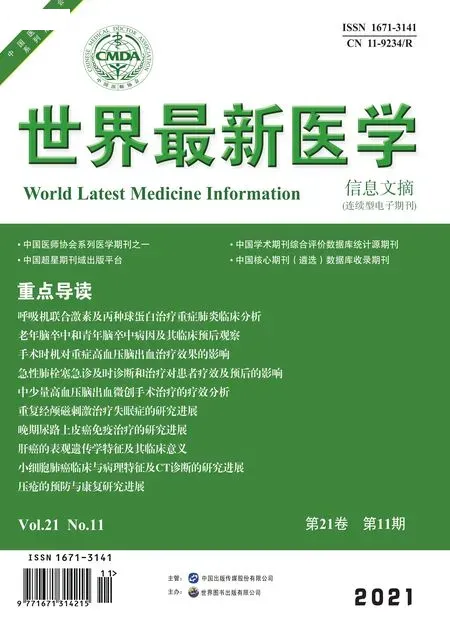肝癌的表觀遺傳學特征及其臨床意義
史海燕
(延安大學醫學院,陜西 延安 716000)
0 引言
肝癌是一種惡性腫瘤疾病,具有發病率高和死亡率等提點,是一種危害極大的惡性腫瘤疾病。一般來說,肝癌可分為原發性肝癌和繼發性肝癌兩大類,前者是指起源于肝臟的上皮或間葉組織的惡性腫瘤,后者則是起源于其他器官的惡性腫瘤,因轉移或繼發至肝臟所致的惡性腫瘤疾病。在臨床上,繼發性肝癌多由結腸癌、直腸癌、胃癌、膽道癌、子宮癌、乳腺癌和肺癌等轉移所致。目前,肝癌的病因和確切分子機制尚不明確,但一般認為環境因素和遺傳因素是導致肝癌出現的主要原因。張曉梅等學者在《MicroRNAs的表觀遺傳學調控機制及其在肝癌中的表達特征》一文中的研究結果表明[1]:肝癌發生過程中只有少數癌基因或抑癌基因發生突變,表觀遺傳學改變能夠使導致肝癌發生率的主要原因之一。從這一研究結果中可以看出,肝癌發生過程中表觀遺傳學改變的重要作用。表觀遺傳學改變是研究基因表達的學科,其中包含組蛋白修飾、DNA的甲基化和非編碼RNA等。程蘭芳學者在《miR-483-5p表達水平與肝癌患者相關病理學參數的關聯性分析》一文中的研究也指出[2]:肝癌的發生同其他類型腫瘤疾病抑制,都是表觀遺傳學異常和基因改變共同引發并促進演變而成的。這一研究研究進一步證明了表觀遺傳學異常同肝癌產生方面密切的聯系。目前,在肝癌表觀遺傳學特征研究方面,DNA甲基化的研究最為深入。為此,本文以肝癌DNA甲基化為切入點,對肝癌的表觀遺傳學特征及臨床意義進行了深入研究,希望通過本文的闡述能夠為肝癌的深入研究提供些許幫助,現綜述如下。
1 肝癌
肝癌的病因。我國是世界肝癌大國,據統計全球每年新發肝癌患者約有85.4萬左右,而我國每年新發肝癌人口則在46.6萬左右,可以說我國肝癌患者占全世界總數的50%左右。通過深入分析發現,導致這一現象出現的原因同過量飲酒、肝炎病毒流行和黃曲霉毒素有著直接的關系。眾所周知,肝炎--肝硬化--肝癌,被稱為肝癌三部曲,由肝炎和肝硬化發展而來的肝癌是首要病因。而飲酒更是導致肝硬化的重要危險因素,我國作為一個人情社會,酒局是成年人人際交往過程中無法繞開的一個環節,也是社會生活中不可避免的過程。并且,近幾年隨著我國經濟的發展,人民工作壓力也在不斷提升,酒局更是成為交際應酬過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環節。這一現象的出現便導致我國肝癌發生率的急劇提升。并且,肝炎也是導致肝癌發生的主要原因之一。據統計,我國乙肝病毒攜帶者高達9000萬人,其中約有2800萬人屬于慢性乙肝。肝炎作為導致肝癌出現的重要危險因素,在我國龐大肝炎患者基數下,便導致肝癌成為我國常見的惡性腫瘤疾病。肝炎病毒主要通過血液、母嬰和性接觸等途徑進行傳播,我國因醫療衛生行業發展較晚,人們早期往往缺乏充足的肝炎病毒預防意識,這便導致肝炎病毒出現了全國流行,導致我國出現肝炎人口基數十分龐大。而黃曲霉毒素則是由黃曲霉和寄生曲霉等菌株所產生的雙呋喃環類毒素,其中存在約20種衍生物,不同的衍生物毒素也不近相同,但普遍存在一定的致癌性。臨床研究發現,動物食用黃曲霉毒素污染的飼料后,肌肉、奶、蛋和內臟中便可檢出微量的毒素,人類一旦食用該類牲畜,便會導致毒素的累計,從而增強人類患癌概率。有統計發現,糧食收黃芪霉毒素污染嚴重的地區,肝癌發生率顯著高于其他地區。也有學者表明,約有4.6%~28.2%的患者發生肝癌的原因同黃芪霉毒素有著直接的關系。我國南方地區常以玉米為主糧,玉米常受到黃曲霉毒素感染,這便導致廣東、附件、廣西和江蘇等地區為我國肝癌高發區,上述地區居民使用糧食中均存在不同程度的黃曲霉毒素污染。近幾年,隨著我國經濟的發展,人們逐漸注意食品衛生問題,但私家車數量的增多和飲食習慣的改變也成為影響肝癌出現的危險因素。有學者研究發現,汽車尾氣及油炸食品中的三四苯丙芘和丙烯酰胺等成為會對肝臟造成嚴重損害,增加人體患肝癌的概率[3]。從上述研究結果中可以看出,外界患者時影響人類是否出現肝癌的主要原因之一。有研究發現,美國出生并長大的華裔肝癌發生率要比中國出生長大的黃種人低三倍。這一研究結果進一步證明了環境因素在誘發肝癌出現方面的作用。有研究表明,我國肝癌發生率和死亡率均較高,近幾年隨著醫學技術的不斷進步其他危重癥疾病患者死亡率已明顯降低,但因我們對肝癌發病機制認知的不足,肝癌患者生存率并未出現顯著提升。從這一研究結果中我們能夠發現,加深對于肝癌發病機制的認知,明確肝癌表觀遺傳學特征,對于肝癌患者的治療和生存率的提升均有著重要的意義。
2 肝癌的表觀遺傳學特征
2.1 肝癌與DNA甲基化。在機體腫瘤發生過程中,RB(Retinoblastoma)通路中的INK4a-ARF編碼兩種細胞周期調控蛋白p16INK4a和p14ARF最為經典。其中,p16INK4a的表達缺失主要因啟動子區異常的甲基化所致。一般來說,p16INK4a的啟動子區CPG到甲基化率為55%~73%,而肝硬化的異常甲基化率則約為29%,慢性肝炎病毒為23%。TMS1/ASG則是另一種凋亡相關基因,屬于細胞核NF-KB的負性調控元件,主要用于NF-KB表達的調控。在肝癌細胞株中,經甲基化酶抑制劑5-AZA和組蛋白去乙酰基酶TSA誘導后激活TMS1轉錄。TFPI2則是一種Kunitz類型的絲氨酸蛋白酶抑制劑,能夠在多種腫瘤細胞入侵過程中起到抑制作用,在甲基化導致表達缺失的肝癌細胞株中,通過甲基化酶抑制劑5aza-cytidine和組蛋白去乙酰化酶抑制劑ESA聯合處理能夠恢復TFPI2mRNA的表達。在肝癌中,組織金屬蛋白酶的甲基化頻率則為13%~19%,目前尚未在正常肝組織中發現甲基化。6-甲基鳥嘌呤DNA甲基轉移酶則是另一種重要的DNA修復基因,在肝臟具有高度活性,肝癌中6-甲基鳥嘌呤DNA甲基轉移酶啟動子區域甲基化頻率約為22%-39%,且肝癌和相應非癌肝組織中均發生甲基化,并多發于肝癌早期[4]。
2.1.1 高甲基化與肝癌:臨床研究發現,高甲基化與多種腫瘤的形成有著密切的聯系,基因啟動子區的CPG島正常狀態下一般處于非甲基化狀態,但當其發生甲基化后,便有可能導致記憶轉錄沉默,從而造成DNA修復基因和抑癌基因等重要基因功能的喪失,致使正常細胞的生長分化調控能力和DNA損傷修復能力減弱,提升機體出現腫瘤的概率。在人體肝臟器官中,氨基甲酰磷酸合成酶屬于特有的線粒體內尿素循環限速酶,該抗體常用于臨床術后病理研究過程中。有研究將肝癌細胞中轉錄起始點附近的氨基甲酰磷酸合成酶二核苷酸和第一個內含子內氨基甲酰磷酸合成酶二核苷酸富含區域高甲基化后,發現細胞內的氨基甲酰磷酸合成酶1基因出現沉默或表達水平下調情況,當肝癌細胞經甲基化抑制劑5-氮雜胞苷處理后發現,細胞內的氨基甲酰磷酸合成酶1基因恢復正常。這一研究結果不僅進一步證明了高甲基化與肝癌間的密切聯系,還表明氨基甲酰磷酸合成酶1基因氨基甲酰磷酸合成酶二核苷酸高甲基化將成為肝癌潛在的生化標記[5]。
2.1.2 肝癌診斷、預后與DNA甲基化間的關系:DNA甲基化常發生于肝癌早期,當腫瘤組織壞死脫落后,分解的DNA會進入血液循環或唾液、痰液等體液中。因此,體液中是否能夠檢出腫瘤相關基因甲基化狀態便成為肝癌臨床診斷的重要依據。
2.2 microRNAs和肝癌。小片段非編碼RNA又被稱為microRNAs,屬于新的調控分子家族,他們能夠結合mRNAs的3′端、5′端,端未翻譯區并加以識別,從而對不同細胞的增殖、分化和凋亡進行調控,全程參與腫瘤的發生和發展。有研究發現,miRNAs表達分析有助于對其功能的了解,是表明其與疾病間關系的有力證據。另有研究發現,在肝癌樣本中,miRNAs表達要高于正常樣本。這一研究結果表明,肝癌診斷過程中miRNAs可能成為新的診斷工具。
2.3 肝癌與組蛋白修飾。表觀遺傳學中組蛋白修飾是重要的組成部分,DNA通過其染色質結構被包裹在真核細胞核中,而染色質的基本單位是核小體,由146對堿基纏繞著兩個拷貝的組蛋白H2A、H2B、H3和H4所形成的十面體結構而構成。組蛋白的出現不僅使染色質的核小體N末端突出區域易與其他蛋白間發生相互作用,還提供了固體結構,使多種類氨基酸殘基經翻譯后修飾發生在組蛋白末端,其中包含精氨酸的乙酰化、泛素化、甲基化和腺苷二磷酸核糖基化。并且,組蛋白翻譯后修飾具有動力功能和可逆轉特性,能夠通過兩套具有拮抗作用的酶復合體在特定位點介導相應化學基團的去除或增加。目前,賴氨酸殘基的乙酰化是研究最透徹的組蛋白修飾,改修飾功能有組蛋白乙酰化酶執行,在該過程中,可被組蛋白去乙酰化酶逆轉。通過研究其他組蛋白修飾發現,賴氨酸殘基會發生單甲基化、雙甲基化和三甲基化,其功能取決于所修飾的位點。最新研究發現,組蛋白去乙酰化酶抑制劑saha結合甲基化抑制劑5-aza在肝癌生長過程中存在明顯的抑制作用。
3 討論
近幾年,隨著醫學技術的不斷發展,肝癌中表觀遺傳學的應用價值已受到學者們的廣泛重視。但是,因研究時間尚短,在肝癌甲基化抑制方面的治療不甚成熟,相關藥物種類、給藥途徑、劑量和使用時間等方面的問題尚未徹底解決,這需要人們加強對于肝癌表觀遺傳學的研究,以達到優質肝癌早期診斷,改善治療方式和優化患者預后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