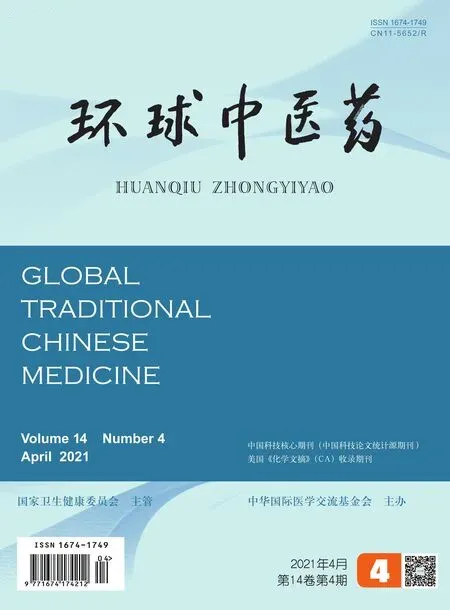從木郁達之談反流性食管炎伴廣泛性焦慮障礙的治療
陳前 劉冬梅 鄒陽 劉百惠
反流性食管炎(reflux esophagitis,RE)是臨床常見高發性疾病,患病率高達12.5%,嚴重影響患者身心健康[1]。西醫常使用質子泵抑制劑、胃腸促動力藥、胃黏膜保護劑等藥物治療[2],外科或內鏡下治療等[3]。仍有部分患者治療效果不理想,RE反復發作,致使其心理負擔過重出現廣泛性焦慮障礙(generalized anxiety disorder,GAD)。“木郁”在其中扮演關鍵角色,“木郁達之”最早見于《素問·六元正紀大論篇》對五氣之郁的論述“郁之甚者,治之奈何”“木郁達之,火郁發之,土郁奪之,金郁泄之,水郁折之”[4]。根據天人相應的觀點,五郁與人體疾病的病癥密切相關。歷代諸多醫家不斷豐富其內涵,木郁作為五郁之首,多將其引申為肝郁。郁而不發,致使木受制約,失其條達之性,五行相因,木壅土郁,情志不暢發為抑郁。現試從“木郁達之”探討RE伴GAD的中醫診療思路。
1 RE伴GAD的中醫病機認識
1.1 RE易伴發GAD
胃食管反流病是指胃(或十二指腸)內容物反流入食管或食管以外(口腔、咽喉、肺部)引起的不適癥狀的一種疾病,RE歸屬于胃食管反流病中的一種常見類型,內鏡下表現為食管黏膜破損,即食管糜爛和(或)食管潰瘍[3,5-6]。中醫學多將RE歸屬為“吐酸病”“食管癉”,病機虛實夾雜,多為肝氣橫逆犯胃、胃失和降、胃氣上逆所致[7]。RE中大部分患者有輕重不一的心理障礙,故肝郁是病機關鍵所在[8]。RE在臨床上常表現為反酸,燒心,噯氣,急躁易怒,脘腹脹滿,咽喉不適,口干口苦等[9]。
臨床上RE常伴見GAD,有研究報道GAD的狀態與疾病的嚴重程度呈正相關[10]。GAD指的是患者在生活中對某事件或某想法的擔憂和焦慮,并且可能會出現害怕、緊張及擔心等不良情緒,具有廣泛性、持續性和難自控性[11],在疾病出現過程中伴隨發生,呈現出對疾病的慢性擔憂狀態[12]。GAD屬于臨床最常見的一種焦慮障礙[13],GAD在中醫學中常辨證劃分為“郁證”,“郁”的概念源于《內經》。明代虞摶在《醫學正傳·卷之二·郁證》中,正式提出將“郁證”作為獨立病名[14],臨床多表現為煩躁不安、善驚易恐、坐臥不寧、失眠健忘等[12]。
1.2 因病致郁
《景岳全書·吞酸》中述:“腹滿少食,吐涎嘔惡,吞酸噯氣,譫語多思者,病在脾胃。”[15]RE病位雖在上為食管,與中焦肝脾胃密切相干[16]。《難經集注》記載“咽在后,下連食道,直貫胃腑”,故稱之為“胃之系”[17]。若中焦氣機失調,則樞機不利,肝木失其達,郁而為滯,胃之通降不暢,脾之升清受阻。初病在實,久病多虛,隨著病機的演變,濕、痰、食、熱、氣、瘀六種病理因素互相搏結,由實致虛,邪盛正衰,濁氣不降反升則氣機逆亂,易招致情志疾病發作[7]。《景岳全書·郁證》中指出:“凡氣血一有不調而致病者,皆得謂之郁證,亦無非五氣之化耳。”[15]汪昂在《醫方集解》中指出“郁證多在中焦……四臟一有不平,則中氣不得和,而先郁矣”[18],均說明中焦肝脾胃生理功能正常則氣機疏利調和,氣血循行周流全身,五臟得以濡養,化生五志,情緒平和。若中焦受損,樞機不利,氣血失和,化生乏源,更易誘發情志疾病。
人體攝入的飲食,通過胃氣的受納腐熟、脾氣的輸布運化作用,化生為水谷精微以濡養臟腑,故《素問·靈蘭秘典論篇》云:“脾胃者,倉廩之官,五味出焉。”[4]五臟化生五志,即肝藏血以舍魂,脾藏營以舍意,心藏脈以舍神,肺藏氣以舍魄,腎藏精以舍志。《靈樞·本神》中提到“五臟藏精氣而不瀉”[19],精氣充盈,則情志平和。若五臟精氣匱乏,藏瀉失常,無法正常化生五志,情志病隨之失常而發生病變。反流性食管炎病程遷延日久,致使中焦疏利、健運功能受損,運化失調,氣血化生乏源,常伴憂思惱怒,情志不暢。故臨床上針對RE伴GAD的患者,可加用健脾和胃之藥,對于改善情志失常確有療效。
1.3 郁而為病
郁證多是由于情志怫郁不暢,氣結日久,臟腑功能失常所致。陳無擇在《三因極一病證方論》中著重強調七情致郁學說,同時提出情志失調是導致郁證發作的重要病因[20]。巢元方在《諸病源候論》中云:“結氣病者,憂思所生,心有所存,神有所止,氣留而不行,固結于內。”[21]郁久則出現諸多病理變化,如憂思惱怒,氣機郁而不暢,首先導致氣郁,氣郁日久則化火,火邪內遏,發為火郁;火郁灼傷津液而發濕郁,濕邪聚而為痰化生痰郁,痰氣互結,濕濁不化,水谷無以化生精微物質而成食郁,氣血同源,痰濕食郁又會阻礙氣血運行,導致血郁。氣、痰、濕、食郁日久,化火灼傷津液,阻礙津液輸布,日久而成熱郁,最終六郁錯雜互見,互為因果,相因為病,可見氣郁為諸病之基礎,諸郁為致病之源,木郁始于氣郁,故《醫碥》提出:“百病皆生于郁,……郁而不舒則皆肝木之病矣。”[22]朱震亨在六郁學說提出“人身諸病,多生于郁”“諸郁證者,郁結而不散也。人之氣血沖和,百病不生;一有郁結,諸病皆生”。
中焦為情志病變之本,是人體氣機升降的關鍵所在,當情志不暢時,中焦首先受到侵害,郁滯結聚于中焦。唐容川在《血證論》提出:“木之性主于疏泄,食氣入胃,全賴肝木之氣以疏泄之,而水谷乃化。”[23]肝主疏,脾主升,胃主降,中焦氣機暢達,人體則能通過脾胃的正常納運功能,促進水谷在體內的消化,脾氣散精,將其轉化為水谷精微,輸布全身,維持人體正常生理功能。若情志不暢,木氣不舒,肝木失疏泄,木郁制酸,克犯脾土,升降失常,終日犯及脾胃,影響脾胃運化,滯而不暢,遂胃酸隨胃氣而逆升,臨床上伴廣泛性焦慮障礙的反流性食管炎患者,其病情常遷延日久,纏綿難愈,正如《衛生寶鑒》所云:“心思郁結,憂慮不已,以致飲食無味,精神日減,肌膚漸至瘦弱。”[24]憂思者易傷脾,脾氣不得上升,橫郁中焦,飲食乏味、脘腹脹滿、吐酸。
1.4 RE與GAD的病機關聯
RE因中焦功能受損,脾胃失調,無以化生氣血,常易誘發情志不舒,出現GAD;反之,GAD易阻礙中焦氣機正常運行,滯而不發,加重RE的病情。GAD不僅是RE的重要病因之一,也是其病程過程中出現的異常心理狀態,二者相因為病,類似《景岳全書·郁證》“因郁致病”與“因病致郁”觀點[15]。二者相互影響,相互轉化,致使RE病情日久難愈,由此可見,治病求本,欲解郁、除反流,須調達木郁方可恢復肝臟的疏泄功能及脾胃的運化功能。
2 基于“木郁達之”論治——以達解郁
2.1 疏肝理氣,和胃降逆為達
情志不暢是導致RE伴GAD最常見的原因,臨床上多因憂思惱怒發為本病,《壽世保元·吞酸》曰“夫酸者肝木之味也,由火盛制金,不能平木,則肝木自甚,故為酸也”[25],說明吐酸與肝氣密切相關,肝臟體陰用陽,肝胃升降相因,肝郁氣滯,易傷及脾胃,中焦氣機升降失常,則見反酸、燒心、噯氣等;肝郁氣滯,疏泄失常,故可見善太息、胸膈滿悶不舒。
肝失調達,郁而不伸,故治療著重以暢利樞機、平降胃氣為主。主方選用柴胡疏肝散合烏貝散加減,基礎藥用:柴胡、佛手、炒枳殼、醋香附、陳皮、川芎、炒白芍、海螵蛸、烏賊骨、炙甘草。方中柴胡性味辛、苦,升清氣、解郁滯,炒枳殼苦降,有理氣寬中、下氣除滿之效,柴胡、枳殼升降相宜,配伍以調達肝氣、助脾胃運化,共為君藥;醋香附、佛手、陳皮疏利木氣、降逆平胃,川芎活血行氣止痛,考慮肝為體陰用陽之臟,為防劫肝陰,致使肝臟疏泄功能太過,配伍白芍、炙甘草養血柔肝。研究表明烏貝散可顯著提升胃泌素-17、胃蛋白酶原Ⅰ、胃蛋白酶原Ⅱ的水平,從而促進黏膜修復,達到制酸止痛的目的[26]。
2.2 清肝瀉火,益胃生津為達
葉天士提出“肝為起病之源,胃為傳病之所”,木疏則土達,木郁即肝郁,RE伴GAD病情遷延日久,纏綿難愈,肝氣郁久則化熱生躁怒,正如丹溪所云“氣有余便是火”。由于肝為陽臟,體陰用陽,亦屬風木之臟,更易衍生火熱之邪;胃為陽腑,喜潤惡燥,以降為和。肝氣犯胃,夾火熱之邪逆而上沖,故《臨證指南醫案》中提及“因郁則氣滯,氣滯久則必化熱,熱郁則津液耗損而不流,升降之機失度”[27]。若“木壅土郁”,肝火灼傷胃中津液,故出現反酸、胸骨后灼熱感、脘腹痞滿、消谷善饑、噯氣、口苦口干等不適。
肝郁化火,灼傷津液,治療以清肝瀉火,益胃生津為達,方用化肝煎合左金丸加減,基礎藥用:白芍、牡丹皮、梔子、陳皮、青皮、澤瀉、黃連、吳茱萸。方中用青皮、陳皮等量為份,二者味辛苦氣溫,味辛則入肺,氣溫稟天春和之氣則入肝,辛能散,溫能行,積者破而結者散[28]。青皮性較陳皮烈,取其行肝膽氣之功,以寬胸脅三焦之郁而為方藥之主,陳皮有苦降之性,《本草綱目》以其“療嘔噦反胃嘈雜,時吐清水”[29],二者共疏肝氣。怒傷肝,氣機結聚不得發越,閉而為郁,肝木郁結失疏,久則化熱,故張景岳稱其為“氣逆動火”,以梔子清宣郁熱,丹皮清熱涼血降火,同時通氣中血滯,滯消則可祛郁熱,二者共清肝火。肝體陰用陽,為防劫肝陰,以白芍護肝陰,養陰柔肝。澤瀉甘、淡、寒,善利水滲濕以瀉熱,以其利小便以瀉肝中伏火;黃連性味苦寒,善清泄肝胃郁熱;吳茱萸歸肝、脾、胃經,李時珍稱吳茱萸為“開郁化滯,治吞酸”之品,故以辛熱之吳茱萸反佐黃連,寒熱并調,辛開苦降,合為左金丸。現代藥理研究發現左金丸主要是通過抑制炎癥因子對胃黏膜起保護作用,可有效減少胃熱證對胃黏膜損傷[30]。有臨床研究報道左金丸可通過調節胃腸道自主神經功能,改善患者反酸、燒心等不適癥狀[31]。
2.3 柔肝活血,健脾益氣為達
RE伴GAD病程日久,傷正氣于內,氣虛生化無權,機體失于濡養,故“久病多虛”;氣虛日久,血行乏力,血滯脈中不暢,影響氣血運行,氣滯而血瘀,故有“久病多瘀”。肝主藏血,主疏泄,久病則肝失濡養,津液枯竭,虛火上炎,灼傷胃中津液,致使胃受納腐熟水谷之功能失常,上逆之火攜未腐熟的水谷,故可見吐酸、燒心、噯氣、口苦等癥狀。宋代醫家楊士瀛在《仁齋直指方·血榮氣衛論》最早提出:“氣者血之帥也,氣行則血行,氣止則血止,氣溫則血滑,氣寒則血凝。”[32]臨床常見上腹部或胸骨后刺痛,伴兩脅肋下不適。
肝失濡養,傷及正氣,以養血柔肝、益氣活血為達。方用補氣運脾湯合通幽湯加減,基礎方用:黨參、炒白術、橘紅、茯苓、甘草、炙黃芪、砂仁、桃仁、紅花、生地黃、熟地黃、當歸、升麻。方中黨參、炙黃芪健脾益氣;白術、茯苓、砂仁燥濕運脾;橘紅燥濕化痰、理氣寬中,防止脾氣失健、痰濁內生,共同顧護中焦。當歸合二地滋陰養血,以增液行舟,專攻幽門閉塞,氣機上逆;升麻升清降濁,與當歸升降相宜;桃仁、紅花活血潤燥。有文獻報道反流性食管炎在病理上有局限性水腫、炎癥、糜爛等表現,這與現代病理上的“瘀血”概念不謀而合,臨床研究證明健脾祛瘀法對RE有攻補兼施的療效[33]。
2.4 心理學療法——移情易性以達之
RE伴GAD,二者相互影響,患者既有肝脾不和、脾胃功能失調的臨床表現,又有較為明顯的焦慮障礙。GAD不僅作為RE的重要病因之一,也是疾病過程中出現的異常心理狀態,葉天士提出“郁證全在病者能移情易性”。“木郁達之”一法,旨在通達中焦氣機。通過氣機升降的特點及氣化規律進行變通,順應木性,斡旋中氣,全在于達,對于臟腑病證的辨治以及臨床有關疾病的診療提供了指導原則。
隨著生物-心理-社會醫學模式的不斷發展,一方面,患者對于自身心理健康越來越重視,另一方面,其較難接受自身患有精神類疾病,部分患者在就診過程中可能存在刻意隱瞞自己心理問題的情況[34]。王慶其[35]認為除藥物治療外,此時醫生需要對患者進行心理疏導,主要包括三大原則:傾聽原則、幫助原則、肯定原則。巴建全等[36]提出防治不良心理問題的重要措施,需要醫患雙方的共同努力:患者應擺正心態,以樂觀積極的心態正視自身問題,主動配合醫生治療;醫生應對病人進行人文關懷、提高診療疾病的專業水平,做到身心同治。可酌情增加放松療法、短期正念冥想訓練等專業治療。結合現代心理學療法,包含支持性心理療法、認知行為療法、心理動力性心理療法,其中應用最為普遍的當屬認知行為療法[37],最大程度地減輕不良因素對疾病的影響,減少患者對疾病本身的恐懼,提高就診依從性,從而達到治愈疾病目的。
3 結語
RE伴GAD病程遷延日久,纏綿難愈,其病因病機多為情志不暢,中焦運化失常而致氣機失調。氣機失調始于木郁,木郁則肝氣失疏,橫逆犯胃;病久則郁而化火,灼傷胃之津液;或久郁成瘀、成虛。木郁致病,病機多變,需調其性,即為達道,故治療上也應靈活應用疏肝氣、清肝火、柔肝血、健脾胃之法,佐以醫務工作者對患者的心理疏通,以暢達木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