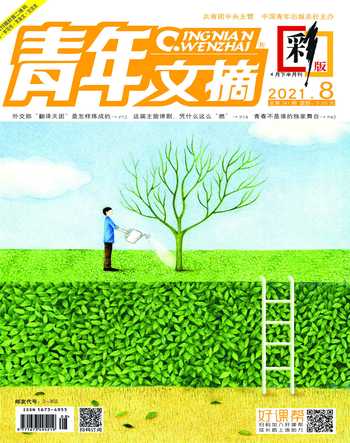媽媽,我們都將是彼此驕傲的存在
曉可

人人都羨慕季軒有個好媽媽。上幼兒園時,每次過兒童節,媽媽都會做好吃的蛋糕分給每個小朋友,女孩的是粉嘟嘟的草莓慕斯,男孩的是酷酷的巧克力虎皮卷。穿著白色連衣裙的媽媽,真像一朵盛開的夏花。
那時的季軒,也是媽媽眼里最完美的孩子:兩歲就能背誦幾十首古詩,三歲能念完整首英文兒歌,逢人便禮貌地打招呼……每天放學后,是母子倆怎么也親昵不夠的游戲時光。
最令季軒自豪的是,媽媽是個出色的服裝設計師。從小他就喜歡向客人指著家里一排亮晶晶的獎杯說:“你看,我媽媽多厲害!”不過他不太愿意提起爸爸。身為公司高管的爸爸,向來來無影去無蹤,偶爾父子相見,也永遠只是嚴肅的一句話:“別貪玩,要聽話!”
日子就這么帶著小歡喜,又伴著些小遺憾,靜靜地滑過。直到有一天,幼兒園大班班主任的家訪打破了平靜。老師悄悄把媽媽拉到一角,說:“季軒這段時間很奇怪,上課經常注意力不集中,有時還一個人跑到教室外面上躥下跳。”為了治一治兒子的“調皮”,媽媽推掉了項目,多抽時間陪伴兒子。可情況并沒好轉:經常吃著飯,季軒就扔掉筷子跑出門去;最喜歡的繪本看個兩分鐘,就開始在書桌上東摸西翻……媽媽焦急起來,難道是孩子上小學前的叛逆期?奶奶寬慰說:“小男孩哪個不頑皮?”媽媽也不得不自我安慰:或許上了小學,一切就會好起來。
轉眼間,小學時光如期而至。為了能開個好頭,媽媽拒絕了所有加班,每天晚上坐在他身邊陪讀。但季軒的情況根本沒有好轉,隨時邊做作業邊開啟“神游”模式;只要媽媽一離開,他就嗖一下竄出書房,在外面“哐哐當當”起來,急得媽媽連衛生間都不敢去。如此艱難地熬過了兩年,季軒的成績還是排名倒數。
到了三年級,情況越來越嚴重,一切都有垮掉的趨勢。已共處兩年的同學,都在背地里叫季軒“季瘋子”,沒人愿意做他的同桌。新來的班主任沒辦法,只能將他安排到第一排的特殊座位。沒想到,在老師眼皮底下的季軒,非但沒有收斂,反而更加變本加厲。他經常會在考試中途把試卷狠狠地揉成一團,大吼大叫地沖出門去。數學考試時最容易“反常”,按照數學老師的說法,季軒的邏輯推理能力“比其他同學差了一大截”。語文老師也非常失望,說季軒“沒有閱讀能力,讀篇小短文都會漏字漏行”,寫作更是一塌糊涂,“不會組織語言”。各科老師也都耐心教育過,想引導季軒把自己不懂的地方說出來,但他總是東拉西扯,連起碼的問題都表述不清楚。久而久之,老師們也都紛紛放棄了。
媽媽崩潰了,成績單上的分數像一把錐子扎進心里。她毅然辭去工作,全力以赴地照顧孩子。出差回來,不明就里的爸爸見狀,忍不住責打季軒,事后又對媽媽怒吼:“你看你養出個什么樣的兒子!”
期末的家長會上,媽媽默默坐在角落里,看著其他家長喜氣洋洋的笑臉,忍不住淚眼婆娑。班主任走過來拍拍媽媽的肩膀,說:“我知道你很難過,但或許季軒不是毫無希望。我觀察一個學期了,他其實很聰明,也不是品行不好,或許他只是得了一種病癥,比如說,多動癥。可以帶他去醫院看看。”
幾天后,媽媽帶著季軒來到了醫院。一進診室,季軒就竄到醫生后面,瘋狂地轉動轉椅,還沒等醫生從突然的眩暈中回過神來,他就一把扯過桌子上的鼠標,對著電腦一陣亂點。一旁的媽媽又尷尬又痛心,急得什么話都說不出來,只是流淚。醫生趕緊安慰道:“你別哭,會有辦法的。”經過一系列檢查,季軒被診斷為多動癥。因為已滿九歲,所以需要藥物治療。
服藥一個月后,情況有了令人驚喜的改變。班主任反饋,聽課時季軒明顯坐得住了,注意力也越來越集中,能安靜地聽完一整堂課。媽媽陪讀的次數也越來越少,他慢慢能堅持自己完成作業,而且正確率越來越高。三年級第二學期的期末考試,季軒的成績躍到了班級的中游。醫生說,癥狀緩解后,還需要服藥一年以上,以鞏固療效。對此,季軒全家欣然接受,連不茍言笑的爸爸都長舒了一口氣,表示“一切都聽醫生的”。
最近季軒陪媽媽逛街,看著櫥窗里的模特身著最新款的連衣裙,媽媽眼睛亮晶晶的,說:“這款連衣裙,當年我設計過,還拿了獎。”旁邊的季軒眼睛一陣發酸,他清了清嗓子,堅定地對媽媽說:“媽媽,你回去工作吧!我努力學習,你努力工作,看咱們誰更厲害!”
“好,一言為定!”媽媽笑了,又哭了,這應該是春天里最開心的眼淚。
(本刊原創稿,感謝成都市婦女兒童中心醫院神經科趙力立副主任醫師對本文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