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能源轉型困頓
文 | 李曉平
作者供職于能研智庫
德國一直以來被公認為全球能源轉型的模范,但從事實看來,德國不但無法實現2020年的大部分能源轉型目標,而且在轉型過程中新問題“頻出”,德國能源轉型已然陷入“困頓”之中。
德國是能源轉型的先驅。2000年,該國頒布《可再生能源法》。在高額上網電價補貼政策的支持下,可再生能源裝機發展突飛猛進。2009~2018年,德 國風能 和 太陽能裝機規模的復合增長率分別達到9.7%和17.7%。此外,該項法律也催生了一個巨大的綠色產業:德國的公司發展相關尖端技術、為數十萬員工創造就業機會。基于這一令人驚嘆的成就,德國為進一步加快能源轉型設定了雄心勃勃的目標。根據聯邦政府的規劃,到2020年,德國應該在向低碳密集型、安全且低價的能源供應轉型上取得重大進展。
今年是規劃目標實現的一年,但大家可以很明顯的看到德國無法完成制訂的大部分目標。與此同時,“能源不可能三角”(能源安全、能源公平以及環境可持續性)的三個“角”均出現了問題。能源轉型的列車貌似已經“脫軌”。
能源供應形勢嚴峻
德國長期以來一直擁有高度安全的電力供應,但這種形勢隨著能源轉型的深入逐漸發生惡化。彭博社的數據顯示,2014年德國電力市場的過剩電量相當于需求峰值的17%。德國電力基準合同價格自2010年底以來下跌了超過36%。但隨后形勢出現了“逆轉”。

一方面,由于可再生能源發展過快,備用電量日趨緊張。2019年6月,德國電網屢次面臨嚴峻形勢:連續三天發現可用電量嚴重不足。需求峰值時,供需缺口達到600萬千瓦。為了穩定電網,需要從周邊國家緊急安排電力進口。此外,平衡能源的價格曾一度升至2017年均值的600倍。
未來的供應形勢或將更加嚴峻。德國提出2022年底逐步淘汰核電,以及2038年逐步淘汰煤電,國內電力供應缺口或將繼續擴大。如果不建設新的發電設施,備用容量或將大幅下降。尤其是,未來一段時間內,德國西部和南部區現有電力裝機大量關閉后,區域內的工業區將受到嚴重的打擊。此外,在電力需求高、但可再生能源供應較低的情況下,從可調度的能源向間歇性的可再生能源的轉型也會導致新的問題。
另一方面,德國或將從電力凈出口國轉為電力凈進口國。2019年6月,德國電力出現近5年以來的首次凈調出,而且5~8月連續4個月出現凈調出。此外,德國周邊的一些國家還在關閉電廠。例如,荷蘭正在逐步退出煤電,比利時有關停止使用核能的討論也可能導致該國核電站的關閉。從中期來看,整個歐洲電網或將出現電力供應缺口,德國也很難“獨善其身”。
此外,德國風電行業發展出現了明顯惡化。德國沿海(北海)的5個州(梅克倫堡—前波莫瑞州、不來梅、漢堡、石勒蘇益格—荷爾斯泰因州和下薩克森州)的州長聯名給總理默克爾寫了一封公開信,在信中他們疾呼:德國風電行業已經到了最危險的時刻。2014~2018年間,德國陸上風電年均新增裝機2.7GW,而2019年這個數字只有507MW;部分風電企業或破產,或裁員,整個行業已減少了40000個工作崗位。
環境可持續性堪憂
從環境可持續性上看,德國能源轉型遠遠落后于2020年的目標。根據Agora EnergieWende測算,2019年德國二氧化碳排放量約為8.11億噸二氧化碳當量(CO2e),同比下降約5.1%,但仍比之前制訂的2020年7.5億噸的目標高出6100萬噸。而且近兩年的改善只是短暫的,二氧化碳排放的下降主要由于可再生能源發電量創紀錄、二氧化碳價格上漲以及氣候溫和等因素造成的,并不可持續,更重要的是并未出現長期改變的趨勢。到目前為止,德國幾乎所有的二氧化碳減排均來自電力行業的努力,而電力行業的減排主要是由于可再生能源裝機和發電量的提升、舊的煤電和核電的關停以及歐洲排放交易體系對二氧化碳的額外增收所產生的。然而,電力行業的成就尚未在交通、建筑或工業領域得到復制。在交通領域,自2012年以來,二氧化碳排放量增長了近6%。乘用車的增加(增加5%)抵消了每公里排放量的減少(減少3%),導致總體上呈負平衡。在工業領域,二氧化碳排放量從1.8億噸增至1.96億噸(增長9%)。最后,建筑行業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有所下降,但僅從1.3億噸降至1.17億噸,降幅僅為10%。
1.電力成本居高不下
電價其實是能源轉型中最明顯的問題。德國的電費世界第一。目前,家庭用電價格仍比歐洲平均水平高出約45%。
居民用電價格居高不下的主要原因是稅費,盡管采購和銷售成本下降了16%,但自2012年以來,稅費上漲了17%。《可再生能源法》的征稅從3.6歐分/千瓦時提高至6.4歐分/千瓦時,這對德國來說是一個不小的挑戰。在德國稅費占家庭電價的54%,遠高于歐洲37%的平均水平。電網擴建以及電網干預成本也導致了德國的電價增加;電網使用費已達到7.4歐元/千瓦時,自2012年以來上漲了20%。
2.聯邦政府頒布氣候行動提案
在德國,由于在應對氣候變化方面缺乏進展,普通民眾的沮喪情緒在漸增。“未來星期五”學校罷工以及綠黨在歐洲選舉中取得良好成績,都表明公眾對氣候保護有著強烈的意識。聯邦政府的壓力正在增加。很明顯,小的調整還不足以使能源轉型回到正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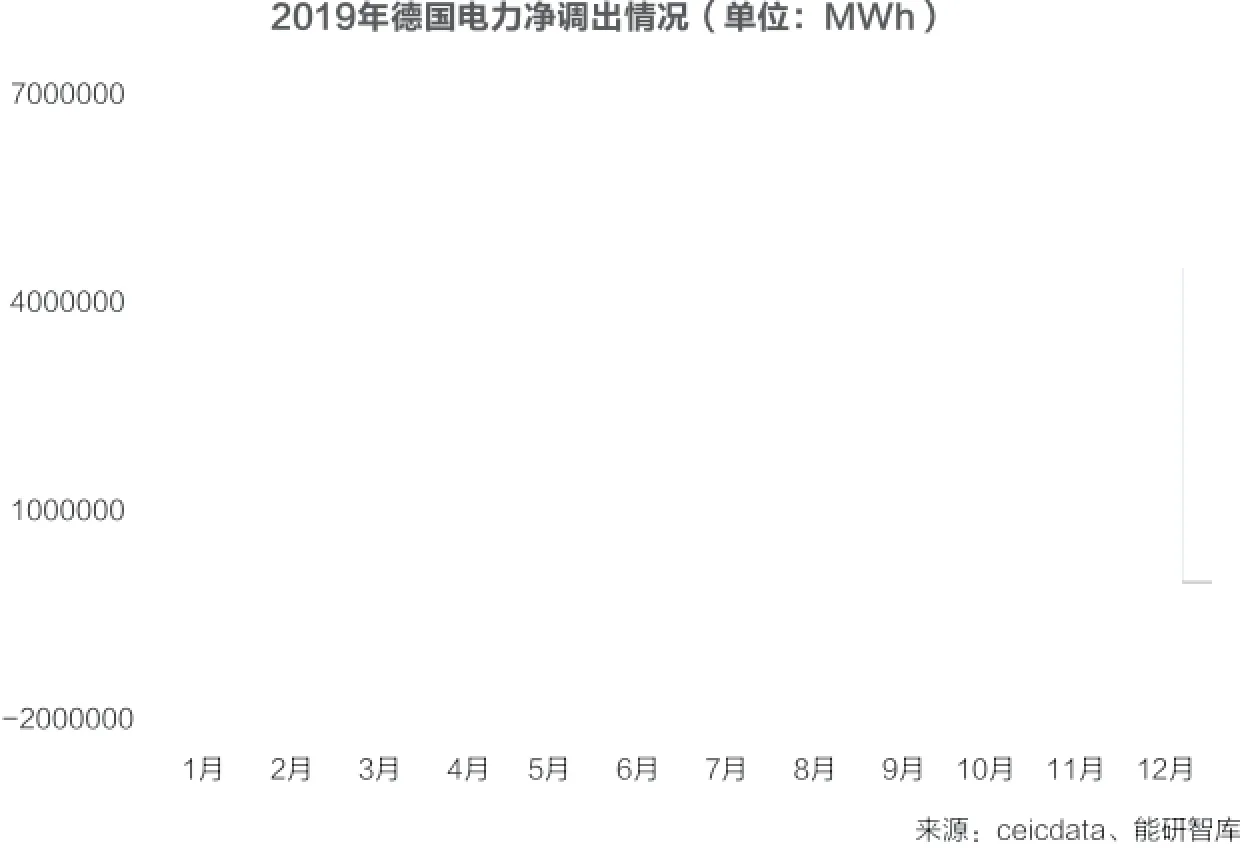
因此,在2019年9月,德國政府就一個理念達成一致,即在2030年前實現溫室氣體排放量減少55%的目標,并制定每個部門的年度減排目標。一些政府部門已經就這一“氣候套餐”的提案進行了數月的工作,為了確保遵守,減排工作將受到外部專家委員會的客觀監測。目前計劃采取50多項措施,幫助加快減排步伐,控制成本:從2021年開始,將對建筑和運輸部門的排放實施碳定價,完善現有的歐洲排放交易體系。此外,政府還將通過降低電價、增加對通勤者的補貼、提高住房補貼以及減少公共交通工具的稅收等措施來補償市民的經濟利益。
盡管人們普遍認為,這一氣候行動提案是朝著正軌邁出的一步,但大多數研究人員認為,提案中的措施不夠有效,無法在2030年前達到重新制定的減排目標—55%。最大的不足是:二氧化碳價格水平不足以導致客戶行為和投資的充分轉變。例如,在部門合作方面,雖然這一提案界定了移動出行部門的具體目標(2030之前完成700~1000萬輛電動汽車),但其他部門的目標仍然模糊不清,例如在建筑和供暖方面。
關于能源效率,批評人士抱怨稱,對能源效率措施的作用缺乏全面的看法,因此政府已宣布在年底前制定2050年能源效率戰略。制定這一戰略的一個挑戰是,雖然對能源效率措施的財政支持增加,但尚不清楚這些措施將在多大程度上有助于減少能源消費。由于電氣化的進一步發展,盡管采取了提高效率的舉措,但至少可以預期用電量仍將進一步增加。
客觀地說,這些措施也不能充分解決德國的供應安全問題,因為德國依賴歐洲電力系統的容量富裕。然而,隨著歐洲各國可調度能力的下降,可以肯定的是,更進一步行動需要采取,以確保德國中長期的能源供應,并防止潛在瓶頸帶來的高宏觀經濟成本。特別是,聯邦政府還應考慮采取四種額外的行動:第一,需要加快電網擴建,以便將更多的可再生能源并網。其次,應擴大峰值負載的能力,以彌補將缺失的電力安全能力,或者增強電力儲備能力。第三,為了在短期內確保供應,德國可以與外國電廠簽訂合同協議,在國內電力供應出現短缺時提供電力。然而,由于其他國家也規劃減少備用容量,這種協議只能作為有限范圍的臨時解決辦法。第四,應增強需求管理,進一步緩解供應短缺;隨著核電和煤電的逐步淘汰,這一辦法將在未來幾年將變得更加重要。
從煤電到可再生能源的必要轉型對世界各國都構成了重大挑戰。德國是最早為其能源轉型制定雄心勃勃目標的國家之一。如今,可以說德國沒有達成2020年的大部分能源轉型目標。然而,能源轉型仍然是一個過程。為了回到正軌,德國聯邦政府需要以有效且及時的方式將最近頒布的氣候提案付諸實際行動,并且需要考慮更進一步的措施。德國仍有機會繼續成為氣候保護的先鋒。此外,德國取得成功還有一個外部“動機”:根據目前歐盟的規定,如果歐盟的指標不斷被違反,該國或將有義務支付賠償金。在2020~2022年的聯邦預算中,已經預留了3億歐元補償對其他歐盟國家的二氧化碳污染。根據Agora EnergieWende估算,未來10年,罰款總額可能高達300~600億歐元。如果不采取對策,納稅人將不得不支付這筆“開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