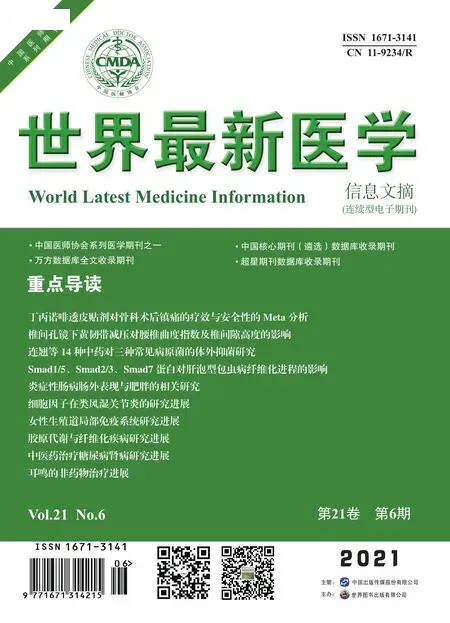孤獨癥譜系障礙兒童父母病恥感情況調查及影響因素研究
溫李滔,潘勝茂,唐省三,來慧麗,胡亞妮
(廣東食品藥品職業學院,廣東 廣州 510000)
0 引言
兒童孤獨癥譜系障礙(autism spectrum disorder ASD)是一組從行為學定義的全面性精神發育性疾病,其核心癥狀為社交交流障礙、行為刻板重復和溝通交流障礙三聯征。美國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CDC)發布歐洲、亞洲、北美洲地區ASD兒童平均患病率在1%-2%之間,美國8歲兒童ASD患病率為1.69%[1]。我國學者對兒童ASD的患病率進行meta分析發現:0-6歲兒童ASD患病率在3.51‰[2]。照顧ASD患兒,父母不但承受精神折磨,還經歷求醫治療挑戰,大量研究表明ASD患兒父母都承受著不同程度病恥感困擾[3]。隨著新醫學模式的發展,ASD患兒父母病恥感嚴重影響一個健康家庭功能正常運轉和健康社區維護,引起國家公共衛生體系關注,成為我國亟待研究的重要問題。因此,本文對ASD患者父母病恥感影響因素、測評工具以及干預措施3方面進行綜述,旨為探討符合我國文化背景下ASD兒童父母病恥感的干預研究提供參考依據。
1 ASD兒童父母病恥感的相關概念
病恥感(stigma)又稱“污名”,指個體因患某種疾病被貼上標簽,遭受歧視,從而產生的一種恥辱體驗。Link指出,病恥感由被貼標簽、社會刻板印象、地位喪失、歧視5個因素構成[4]。ASD兒童父母病恥感是指ASD父母因其子女發育障礙性所致的羞辱感和社會公眾對他們所采取的歧視和排斥態度。病恥感可分為感知的病恥感(perceived stigma)和實際的病恥感(enacted stigma)。前者是指妨礙ASD兒童父母談論親身經歷、尋求幫助的羞恥感和對歧視的預期感受;后者是ASD兒童父母遭受他人歧視及不公平對待的經歷[5]。ASD兒童家長易內化社會互動中對ASD的刻板印象、偏見和歧視,從而體驗到病恥感。
2 ASD兒童父母病恥感的影響因素
國外學者研究證實,影響ASD兒童父母病恥感的因素有家庭因素、臨床因素、社會心理因素等。
2.1 家庭因素:應對策略不足
父母體驗病恥感與其患兒疾病嚴重程度呈正相關[6]。Sarkar[7]等人發現母親比父親更易受到病恥感影響她們與親朋好友間互動,原因在于母親會承受更多外源性的歧視、社會輿論以及社區內異樣眼光。國外學者研究發現[8]家境貧窮、學歷低下的父母與教育水平高、生活水準高的父母獲得更高的病恥感,可能受教育程度高的家屬更理性看待大眾異樣眼光或輿論紛紛,從容不迫應對疾病連帶病恥感。研究證明[9]母親更易因ASD兒童的言行舉止異常而受到歧視,可能是母親感知病恥感比父親要強,還有ASD兒童日常生活更多由母親照料及陪伴,父親更多精力在于賺錢來支撐家庭經濟運轉。
國內學者也研究發現社會文化因素也是病恥感產生主要因素,不同國度其文化背景涵義也不盡相同。而Dunn等研究提示,自我效能與感受到的價值貶低和歧視間存在負相關[10]。Kamei A[6]等學者通過對比美國與日本ASD兒童父母感受到病恥感發現,因文化背景迥然不同,日本父母比美國父母體驗更多疾病連帶病恥感,更強烈感受到被社會孤立。
2.3 衛生服務因素:保健人員不理解
8.4%的城市社區初級衛生保健人員和74.7%的鄉鎮的初級衛生保健人員都把ASD主要發病原因歸因于“教育不當”或“親情缺失”[11]。國外研究表示有[12]45.1%的初級衛生保健人員把ASD形成是因為父母照料不足或冷漠所導致的。美國初級衛生保健人員比專科醫生更顯著的將ASD的病因歸咎于父母的教育因素,很少認為ASD是一種全面性精神發育性疾病[13]。研究結果顯示[14],有14例參與研究的ASD兒童父母在陪患兒進行康復治療是就感受到初級衛生保健人員的歧視,被初級衛生保健人員認為“小孩目前這種狀況,是父母讓小孩缺乏家庭關愛和教育不足造成”的經歷。超過一半以上的社會培訓機構工作者認為ASD疾病發生主要原因是由于家長們的“教育不當”。疾病錯誤歸因是一個不良社會因素,也會導致社會人群將兒童行為異常問題歸咎于家長“親情缺失”。因此,保健人員及培訓機構工作者應加強ASD相關知識的學習,多站立在患兒父母視角上,憂其所憂,分擔患兒父母情感上焦慮,從而減少保健人員及機構工作者的歧視而產生連帶病恥感。
以上針對患兒父母連帶病恥感的相關研究,盡管在對象選擇、研究方法以及對病恥感理解的文化敏感性有差異,研究結局不盡相同,但都表明了ASD患兒家長們具有較深病恥感同時受到多種因素的制約,病恥感對ASD患兒父母就業、心理功能、社交功能以及生活品質等方面有嚴重影響,務必采取有效措施降低其病恥感。
3 ASD病恥感的相關測評工具
①病恥感水平[15]:采用Link等人2002年修訂的病恥感系列量表的中文版,2007年由徐暉漢化,具有良好的信度和效度。該量表包含三個分量表:貶低-歧視感知量表,病恥感應對量表和病恥感情感體驗量表,共有8個維度,46個條目,采用4級評分法,包含貶低-歧視感知、保密、退縮、教育、挑戰、分離、誤解、不同/羞恥8個維度,其Cronbach’s alpha系數分別為0.76、0.79、0.61、0.75、0.68、0.64、0.71、0.73,各維度分值越高表明患者的病恥感水平越高。
②連帶病恥感量表(Affiliate Stigma Scale):該量表是由Make等人開發最初用于評估精神疾病或智力障礙照顧者病恥感,量表內部一致性系數Cronbach’sα范圍為0.85~0.94。臺灣的Chang等學者[16]將連帶病恥感量表用于癡呆照顧者中進行檢驗,量表有3個維度22個項目:情緒維度包括7個條目,行為維度包括8個條目,認知維度包括7個條目。量表采用4級評分法,1~4分分別表示非常不同意、不同意、同意、非常同意,總分值越高表示病恥感水平越高。量表總的Cronbach’s α系數為0.929,三個維度的Cronbach’s α范圍為0.822~0.855,證明該量表良好的穩定性。
4 降低ASD患者父母病恥感的相關措施
各國積極采取措施降低ASD患者父母病恥感:包括社會支持、心理支持、認知支持等從而保護ASD父母利益。
4.1 社會支持
社會支持是人遇到外部復雜事件時,從社會內外部資源中獲得物質及精神的緩助,即包括客觀支持和主觀支持,而客觀支持是人獲得外部資源比如物質、人際關系網等參與,主觀支持即個體所感受到被人肯定、尊重的情感體驗。國內學者[17]的實驗證明,從個體和社會兩個層面共同展開殘疾群體病恥感效應干預,可以顯著減輕病患家屬的病恥感。Mak等[18]研究證實,一方面通過網絡、雜志文章、社交媒介等傳播途徑普及公眾ASD疾病的常識,另一方面協助ASD患兒父母提高自我控制意識和尋找社會支持資源,可以降低父母疾病連帶病恥感內化。研究發現獲得社會支持越多家庭更采取積極措施應對困難,使家庭功能得以正常運轉,從而減少父母病恥感內化[0]。因此,我國應以科普自由行模式開展ASD知識宣傳提高公眾對孤獨癥常識認知,自發性為ASD兒童父母建立支持小組;其次國家層面制定相關扶持政策及宣傳反病恥感運動;最后完善ASD患兒就診療程及有效監管康復機構,為ASD家庭提供整個生命周期的養育教育指導、保險服務和職業發展規劃咨詢[19]。
4.2 心理支持
因親人不支持、社會不理解、康復技能缺乏以及治療干預巨額花費,所以ASD兒童父母不但背負沉重的經濟負擔,還承受著巨大的心理壓力。近年來有研究發現[20]:ASD兒童父母存在焦慮、抑郁、絕望等負性情緒的心理問題,約有超過三分之一ASD兒童父母抑郁量表評分高于常模水平。自我同情心理調節功能突顯了病患家屬自身強大心理素質,有助于降低個體疾病連帶病恥感,提高個體的自我效能感和教育訓練技能[21]。個體心理干預和健康教育有助于提升ASD兒童父母疾病認知,改善負性情緒,減輕自我病恥感。提升疾病認知,增加疾病理解,掌握疾病管理技能,增強內心自信,能夠有效減輕病患家屬的各方壓力,從而促進ASD病患家屬病恥感的干預療效[22]。教育技能訓練能夠提升ASD患兒家長們社會適應能力和改善心理健康水平,從而積極應對疾病帶來的病恥感[23]。有學者研究發現病恥感與抑郁焦慮呈正相關,而正念療法能夠有效降低ASD兒童父母病恥感與抑郁焦慮的關聯性,同時能夠使父母正視病恥感帶來的負面影響[24]。
4.3 認知支持
認知療法是根據人的認知過程,影響情感和行為的理論假設,強調人的情緒來自人對所遭遇事情的信念、想法、觀念,而非來自事情本身,認知療法常采用認知重建、心理應付、問題解決等技術進行心理輔導,發展適應性行為,促進個體身心健康發展[25]。有學者研究表明舉辦ASD科普知識培訓有助于提高公眾對ASD的認知及理解[26]。通過學習ASD病因等相關醫學通識,父母可在養育及康復路上為小孩和自身爭取一種身份認同感,照顧者有足夠底氣維護小孩獨特性,從而減少病恥感[27]。因此,利用多方資源加強宣傳,促進公眾認知,獲取大眾理解,減輕公眾對ASD的誤解與歧視;建議大眾傳媒對ASD患兒及家庭給予正面報道,充分喚醒社會群體的大愛,并內化為實際行動關愛和支援ASD患兒及父母,提供他們生活信心,降低疾病帶來病恥感。
5 ASD患者父母病恥感研究展望及存在相關研究問題
ASD病患家屬病恥感研在國外已開展大量系統探索研究,尤其是歐美國家,但國內相關研究甚少,而針對不同區域間比較研究目前尚未進行。目前國外對該領域研究量表種類繁多,但針對適應我國文化背景下信效度高的病恥感量表相對較少,給科研人員帶來研究技術上的困境或難以開展深層次的研究。ASD患者父母病恥感水平,公眾對ASD患者父母歧視的嚴重程度,產生病恥感的主要原因及其作用機制,以及如何破除社會公眾對ASD的刻板印象、打破醫療服務行業的局限、形成家庭生命周期支持,幫助ASD兒童父母樹立正確的疾病觀念,提高ASD患者父母自尊和自我認同感,降低病恥感,促進其生理、心理、社會層面的全面康復、提升其生存質量,是當前亟待研究的重要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