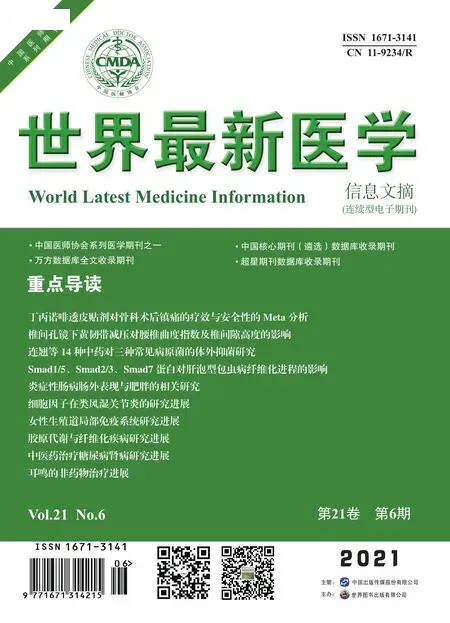中醫藥治療糖尿病腎病研究進展
范文靜,章彩鳳,許筠
(1.甘肅中醫藥大學,甘肅 蘭州 730000;2.蘭州市第一人民醫院,甘肅 蘭州 730050)
0 引言
近年來隨著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運動鍛煉的缺乏,糖尿病發病率不斷增加。全球成年人糖尿病和糖耐量受損的患病率逐年上升,2017年全球糖尿病患者有4.25億,患病率約為8.4%,到2045年,全球糖尿病患病人數預計將增至6.29億人,約為9.9%[1]。而糖尿病腎病是糖尿病常見的微血管并發癥之一,目前已經成為我國終末期腎臟病的首要原因。有研究顯示,當出現大量蛋白尿時,糖尿病腎病的進展速度幾乎是其他慢性腎臟疾病的14倍[2]。可見,早期診斷和及時干預對改善腎臟病結局有重要意義。西醫治療措施主要為控制血糖、血壓,降低尿蛋白,糾正脂代謝紊亂、透析及腎臟替代治療。中醫藥在糖尿病腎病的診治中可保護腎臟功能,減少蛋白尿,延緩疾病進展,均顯示出其積極作用。本文就近5年來中醫中藥在防治糖尿病腎病中取得的進展綜述如下。
1 病機研究是其基
中醫文獻中無“消渴病腎病”的病名記載,根據其臨床癥狀,可歸屬于“消渴”、“水腫”、“腎衰”等范疇。其發生多與素體虛弱,飲食失度,情志失調或房勞失節所傷,致陰津損耗,燥熱偏盛。現代醫家對本病病因病機都有其獨特的認識,仝小林教授[3]認為糖尿病腎病的基本病機為虛、濁、瘀,早期以瘀滯為主,中期虛損漸重,后期則脾腎陽虛、濁毒內生。呂仁和教授[4]認為本病是消渴病失治誤治,加以痰瘀、熱郁積聚于腎絡,耗傷氣血陰陽,致腎元衰敗。楊辰華教授[5]從“腎絡-玄府”論治,認為痰瘀阻于腎絡,致腎絡不通;阻于玄府,則玄府開闔失司,固攝無權,精微下泄,形成濁尿,臨床上重視“開玄通絡”理論的運用。崔陳敏教授[6]認為血瘀是消渴病的重要病機,是產生多種并發癥的根源,其病理產物痰、瘀、毒、絡貫穿于病程始未。巴元明教授[7]從糖尿病和腎病二者的病機出發,認為糖尿病腎病虛實夾雜,概括其病機為氣陰兩虛,久病入絡,毒損腎絡。陳洪宇教授[8]認為消渴腎病演變遵循“腎陰虛-腎氣陰兩虛-腎陰陽兩虛”,腎虛證為最常見證候,實證則為痰瘀、風濕、肝風等。
2 辨證論治護其根
薛伯壽教授[9]從三焦辨證指導糖尿病腎病的治療,其認為糖尿病腎病早期可參照三焦辨證的上焦辨證,病位在肺,治則為宣肺解表、祛風除濕,常用越婢加術湯、麻杏苡甘湯等;中期參照中焦辯證,病位在脾胃,此期主要表現為脾胃氣虛、胃熱熾盛、濕熱蘊結,代表方劑有防己黃芪湯、參苓白術散等;晚期可參照下焦辨證,病位在腎,認為此期病情較為復雜,正虛邪盛,在扶正基礎上兼顧祛“濁毒”,故確立了滋腎健脾,泄濁解毒的治則。國醫大師張大寧[10]從糖尿病腎病的病程、發病機制、癥狀特點出發,認為在中醫辨證上,糖尿病腎病是一個從脾腎氣虛到脾腎陽虛、肝腎陰虛、陰陽俱虛的過程。
3 分期論治顯其效
陳洪宇教授[11]將早期糖尿病腎病分為風濕證、痰淤證、腎虛證,其中將腎虛證又分為腎陰虛及腎氣陰兩虛證,分別確立了三大治則,即祛風除濕、祛痰化瘀、益氣養陰。王耀獻教授[12]認為“內熱致癥”是糖尿病腎病的核心病機,尤其在中期階段最為顯著,中期內熱位于腎絡血分,痰瘀夾雜,治療以外透內清為主,強調兼顧正氣,方藥以生黃芪、牛蒡子、水蛭、黃蜀葵花為主。朱雪萍[13]從“積”論治Ⅲ~Ⅳ期糖尿病腎病,認為有效除“積”,則水谷精微和血液可逐漸恢復正常運行,蛋白尿、血尿隨之好轉,臨床上喜用牡蠣、卷柏相伍軟堅散結,黃芪、肉蓯蓉補中有消,薏苡根、鬼箭羽祛痰化瘀,加強化積之力。劉春瑩主任[14]認為糖尿病腎病V期的病機為脾腎虧虛、水液代謝失常,臨床常用“益氣健脾、溫腎利水”法治療糖腎晚期患者,取得較好療效。國醫大師鄭新[15]從“腎病三因論”出發,認為早期應益肺補腎,中期補腎健脾,晚期調補陰陽,兼和氣血。王耀獻教授[16]提出熱邪貫穿糖尿病腎病始終,并將其分為早期伏熱、中期郁熱、晚期濁熱,治療上強調清熱、透熱、化熱。
4 臨床研究供依據
4.1 自擬經驗方治療
楊江成[17]用益腎別濁湯治療早期氣虛型2型糖尿病腎病患者,分為中藥組82例、西藥組92例和中西醫組101例,分別給予中藥治療(益腎別濁湯:山藥、茯苓、石偉、枸杞各15 g,黃芪、黨參、車前子各10 g,芡實、五味子各5 g)、西藥治療(坎地沙坦)和中西醫結合治療,療程12周,中藥組及中西醫組患者的倦怠乏力、不欲飲、面白等癥狀較西藥組改善更加明顯(P<0. 05),3組患者的ACR以及Cys-c水平較治療前明顯下降,且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 01),中藥組、中西醫組血清HDL-c上升水平顯著高于西藥組(P<0. 05)。姚芳[18]把80例糖尿病腎病患者隨機分為治療組和對照組,治療組在西醫基礎治療上給予扶正祛濁方(當歸、黃芪、太子參、地骨皮、紅花、桃仁、制大黃等),對照組給予西醫基礎治療。結果:治療組總有效率85%,對照組總有效率57.5%(P<0.05));治療組在降低尿素氮、肌酐、尿蛋白/肌酐比值等方面優于對照組(P<0.05))。李巧[19]將早期糖尿病腎病氣陰兩虛夾瘀證患者分為干預組39例和對照組38例,干預組予以滋腎健脾化瘀片(黃芪、山萸肉、葛根、大黃、三七、山楂、雞血藤等藥物)治療,對照組予以匹配的安慰劑治療。結果:12周后,干預組的總有效率為87.18%(34/39),對照組為42.11%(16/38),干預組中醫證候積分的降低明顯優于對照組(P<0.05),干預組的Ccr、Cys-C、ACR及FBG、HbA1c、TC、TG及LDL-C水平較治療前明顯改善(P<0.05)),而對照組的各項指標均無顯著性改善(P>0.05)。
4.2 藥對治療
高彥彬教授[20]在遣方用藥時,喜用藥對,如黃芪與當歸、金櫻子與芡實、狗脊與牛膝、白花蛇舌草與倒扣草,取其協同作用,以增加療效。其中,黃芪、當歸合用,既能益氣健脾,又可活血化瘀,臨床使用時,根據患者氣虛和瘀血嚴重程度,二藥比例從1:1至5:1均可;金櫻子、芡實多用于糖尿病腎病早中期的患者,二者相合增強益腎固精、降低尿蛋白的作用;白花蛇舌草、倒扣草共奏清熱解毒利濕之功,多用于糖尿病腎病中晚期,此外,也常用于內熱較盛的患者;狗脊、牛膝滋補肝腎、強筋健骨,牛膝還具逐瘀通經之效,適用于肝腎虧虛、瘀血內阻證。周恩超教授[21]在辨證論治的基礎上,根據長期臨床實踐,總結出獨特的中藥對藥治療。黃芪與山藥:黃芪補脾腎之陽,山藥補脾腎之陰,二者伍用,一陰一陽,陰陽相合,共收健脾腎、斂脾精、止漏濁之功;生地、玄參:二藥相須配伍,清中有補,養中促清,使清熱涼血,養陰生津之力倍增;玉米須、絲瓜絡:兩味配合,淡滲利水,溫通經絡,同時可降低血尿酸,周恩超教授常以此藥對用于水腫、血尿酸升高的腎衰竭患者。許筠[22]教授以“本虛濕瘀”論治慢性腎臟病,臨床常用黃芪與當歸、澤蘭與穿山龍、女貞子與墨旱蓮、水蛭與地龍、蟬蛻與僵蠶、杜仲與牛膝等藥對辨證論治,收效頗豐。其中女貞子與墨旱蓮兩藥聯用可加強滋補肝腎之陰,但無滋膩之性;澤蘭、穿山龍配伍活血不傷血,利濕不傷陰,共奏活血通絡、利水祛濕之效;蟬蛻配僵蠶,祛風利咽散結,透邪外出,防止咽喉受累而使蛋白尿反復,達到“未病先防,既病防變”的目的。
4.3 中西醫結合治療
李康玲[23]將早期2型糖尿病腎病患者分為對照組、治療組各35人,對照組給予替米沙坦治療,治療組給予替米沙坦+益氣養陰通絡方治療(黃芪60g,當歸30g,雞血藤30g,玄參20g,生地黃20g,山藥20g,石斛20g,牛膝15g,杜仲15g,丹參20g,紅花10g,桃仁10g,地龍10g,桑枝30g,),3月后治療組患者的總有效率高于對照組(P<0.05),患者TG、TC、LDL-C、FGB、2hPG、HbA1c、Scr、BUN、MAU、24h Upro指標均低于對照組(P<0.05)。云銳[24]以纈沙坦膠囊聯合保腎通絡方治療糖尿病腎病,觀察組和對照組各100例,對照組予纈沙坦膠囊治療,觀察組聯合保腎通絡方治療(黃芪、山藥、豬苓各30 g,當歸20 g,黨參、熟地黃、川芎各15 g,山茱萸、鬼箭羽各10 g,水蛭、生甘草各5 g),療程8周。結果:觀察組總有效率為89.00%(89/100),對照組總有效率為77.00%(77/100)(P<0.05),觀察組TNF-α、IL-1β、CRP均低于對照組(P<0.05),Scr、BUN、UAE、β2 -MG水平均低于對照組(P<0.05)。馮穎[25]則選取60例氣陰兩虛夾瘀型糖尿病腎病患者,隨機分為對照組與聯合組各30例,對照組給予鹽酸貝那普利片,聯合組在此基礎上加用水陸地黃湯(生黃芪30g,金櫻子20g,山藥、茯苓、澤瀉、丹皮、芡實各15g,丹參、熟地、山萸肉各12g),療程12周。結果:聯合組治療總有效率為90.0%,對照組總有效率56.7%,差異有統計 學 意義(P<0.05);聯 合 組FPG、2hPG、HbA1c、 24hU-PQ、eGFR、mALB較治療前均下降(P<0.01)。
5 結語
糖尿病是一種慢性和嚴重的代謝性疾病,糖尿病腎病是腎臟結構和功能變化引起的糖尿病嚴重并發癥,至尿毒癥期則為時已晚。有研究發現,若糖尿病前期血糖控制不佳,則各種微血管并發癥相繼出現,可見早期干預對預后有重要意義。近年來中醫的優勢作用逐漸被發現,尤其在全國抗擊新冠肺炎期間功不可沒。中醫藥在糖尿病腎病的預防、輔助治療及改善預后方面同樣顯示出積極作用。但當前有關研究中,多為臨床報道,缺乏中醫藥對糖尿病腎病的降尿蛋白作用、改善血脂代謝及腎臟遠期保護作用的藥理研究、作用機制及多中心臨床研究,我們期待中醫藥治療手段能有進一步循證醫學證據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