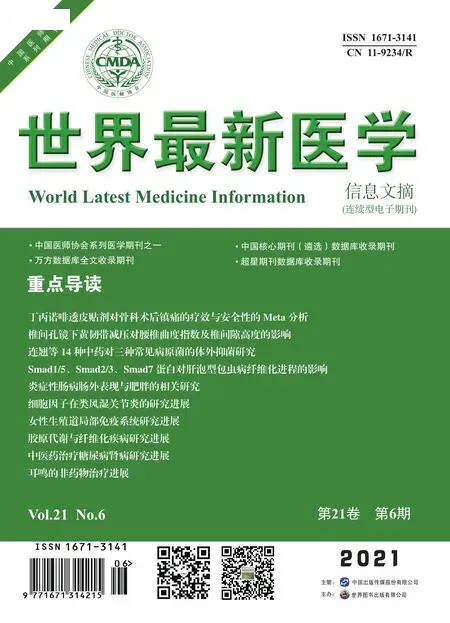妊娠期糖尿病患者孕前體質指數、孕期增重及干預措施的研究進展
萬苗,李紅梅,趙慧文
(延安大學附屬醫院產科,陜西 延安 716000)
0 引言
妊娠期糖尿病(gestational diabetes mellitus, GDM)是指孕前糖代謝正常或潛在糖耐量異常的育齡婦女孕期出現的一種的代謝性疾病[1]。GDM不僅增加了圍產期母嬰不良結局的發生率,而且顯著增加了孕婦及其后代長期肥胖、糖尿病、心血管疾病和惡性腫瘤的風險。根據國際糖尿病聯盟新近發布的糖尿病地圖數據(DIABETES ATLAS),在全球范圍GDM的發病率為14.0%[2]。因此對妊娠期糖尿病這一特殊群體的體重監測及科學管理已是大勢所趨。
1 GDM孕期增重標準
BMI較單純的體重衡量更為準確,因為其考慮到人體的身高因素,能夠有效避免身高產生的誤差,目前,作為反映肥胖程度和健康狀況的一項指標,國際上公認其可靠性更高。根據世界衛生組織(WHO)的BMI分類指南,將孕前BMI分為4組:孕前BMI<18.5kg/m2視為體重偏低,BMI18.5 ~24.9kg/m2為體重正常, BMI25~29.9kg/m2視為超重, BMI≥30.0kg/m2則為肥胖。懷孕期間體重增加的特別推薦標準于1990年制定[3],2009年[4]由美國醫學研究所(IOM)更新。根據世界衛生組織的標準,對婦女孕前體重指數進行了分類。相應的孕期增重指標為:低體重孕婦孕期增重范圍為12.5-18kg,正常體重孕婦為11.5-16kg;超重孕婦體重增加范圍為7-11.5kg,肥胖孕婦為5-9kg[5]。但其針對的是美國人的BMI,與中國人體質有一定的差異,且未綜合考慮年齡及妊娠期并發癥等因素,特別是妊娠期的特殊人群,如妊娠期糖尿病,許多研究已證實與肥胖關系密切, IOM卻未提出孕期增重的指導意見。我國有學者研究涉及此類,但樣本量較少,多為單中心研究,且各地生活狀況、經濟條件及文化底蘊不同,孕前BMI差異明顯。根據2015年發布的“中國肥胖指數”,研究顯示,我國肥胖人群分布由北向南逐漸趨緊,北方肥胖人口較多,南方偏少,特別是東北地區是我國肥胖人群的聚集地。在Mastella等[6]的研究中,只有1/4的人達到了2009年的IOM指南中推薦的體質量增加值,這就意味著GDM孕婦的具體體重范圍應該有所調整。考慮到這些因素,我國妊娠期糖尿病患者尚沒有理想的妊娠期體重增加范圍。
2 GDM與孕前BMI的相關性
1980年至2013年間,成年人超重和肥胖的患病率增加了27.5%,兒童增加了47.1%。目前,在許多中等收入國家,肥胖是一個主要的公共衛生挑戰[7]。無論是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女性的肥胖率都高于男性。這種高肥胖率使肥胖婦女有可能患上與肥胖有關的并發癥,如糖尿病[7]。Torloni等人在他們的薈萃分析中指出,超重女性患GDM的風險幾乎是正常體重女性的兩倍,肥胖女性患GDM的風險是正常體重女性的4倍[8]。同樣有學者證實,超重是2型糖尿病的主要病因,其中腹型肥胖(女性孕前腰圍≥88cm)的胰島素抵抗明顯增加[9]。孕前肥胖、糖尿病家族史和30歲以上是GDM的三個獨立危險因素。孕婦孕前肥胖,優勢比為2.74,是GDM最強的危險因素[10]。但全世界人群的BMI在逐年增長[11]。Najafi等對33項觀察性研究進行薈萃分析發現,妊娠前BMI與GDM有關,BMI每增加1kg/m2,GDM風險增加14%[12]。對已發表研究的薈萃分析表明,懷孕前肥胖母親的孩子超重的風險是懷孕前體重正常母親的3倍[13],并且在一定數值內,出生巨大兒的可能性與孕前BMI成正比。目前尚不清楚這些風險是否因肥胖的嚴重程度而不同,以及這些影響是否僅限于母親BMI的極端程度,還是存在于整個范圍內。然而,巨大兒顯著增加剖宮產、產后出血、軟產道裂傷和不良新生兒結局的風險[14]。國外還有研究認為母親的BMI對胎兒性別為女性有影響(但對男性的影響較小),因為男性和女性從出生起就表現出身體組成的差異,通常女性出生時比男性肥胖,但目前相關研究較少,證據不足,將來還需要多中心,大樣本數據進一步證實。有研究表明,妊娠前BMI、妊娠期體質量增加與臍帶血C肽有直接關系,新生兒出生體重與臍血C肽呈正相關。適當控制母嬰體重,特別是孕前BMI控制,可降低長期代謝綜合征的發生率[15]。此外,在1494名澳大利亞人和3805名荷蘭參與者中,最近的兩項研究觀察到,母親BMI與兒童生長和肥胖風險隨著母親年齡的增長,呈現出的關聯性更強[16-17]。因此,高齡孕產婦BMI對子代結局有相當大的影響,并可作為預防策略的目標,尤其是妊娠前的BMI控制,更是預防工作的重中之重。
3 GDM與孕期增重的相關性
孕期體重增加是衡量胎兒正常發育和孕婦妊娠期適應性變化的重要指標。孕婦體重應控制在適當范圍內,否則會引起各種并發癥。妊娠婦女不同時期體重增加和GDM發生率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1)。GDM的發生率隨著孕期體重的增加而增加[18]。有學者指出,妊娠期體重增加不足和過多與高脂血癥、妊娠期糖耐量異常甚至GDM有關[19]。
3.1 孕期增重過多
研究發現,肥胖孕婦的腹部、臀部、盆腔和陰道中最容易儲存脂肪。脂肪會降低分娩時子宮平滑肌的收縮力度,宮內空間狹窄,產道不得力致產道裂傷,產程延長,陰道助產,新生兒窘迫,剖宮產,感染機率增大,難產等,新生兒患病率和死亡率因此增加[20]。且成年早期的體質量增加過多即使在正常BMI范圍內,也是發生GDM的重要危險因素,因此,從步入青春期到妊娠前控制適當體質量增加范圍似乎是預防GDM發生的主要策略[21]。有學者認為妊娠期前3個月的體質量增加對孕產婦、胎兒及兒童期的不良結局的影響最大,包括新生兒肥胖的增加[22]。妊娠期補充維生素D對GDM婦女的代謝指標有有益影響,可改善糖代謝,尤其是懷孕前三個月[23]。另有一項關于早孕體重增重率與不良妊娠結局關系的研究表明,早孕體重增重是孕前體重正常孕婦發生GDM的危險因素[24],此外,研究發現,在正常體重女性中,妊娠早期增重每超過預期增重的1個標準差,患GDM的風險便增加23%,而中期體重增重與GDM的發生無關[25]。可能是因為孕早期較孕中晚期,早期的增重主要是不成比例的脂肪組織的蓄積,這個時期增重過多可能會導致胰島素抵抗大幅度上升。而到孕中晚期時,雖胎兒所需營養物質的增加,母體儲備脂肪和蛋白質的能力增加,但此時的體重增加易引起孕婦及醫生的關注,積極給予飲食及運動干預有關。然而,一些研究表明,與正常體重增加相比,孕期體重增加過多的孕婦和胎兒的不良后果會增加,而且,懷孕期間體重低、體重增加不足的孕婦分娩小于胎齡兒的概率增加[26]。因此,未來的干預研究應該將重點轉移到先入為主的體重管理上,以育齡婦女為目標,以達到正常體重。
3.2孕期增重不足
此外,有學者發現,增重不足可使胎兒宮內生長發育受限及小于胎齡兒的概率增加,分娩可能導致心腦血管系統疾病、代謝性疾病風險上升。因此,妊娠期間體重增加不足的婦女患GDM的風險增加了2倍以上[27-28]。懷孕前BMI正常的女性應避免體重增加低于美國醫學會(IOM)推薦的推薦值。低于建議的孕期增重可能更適合超重和肥胖婦女。對于GDM患者來說,體質量增幅應小于IOM推薦的體質量增幅,但仍需供給母體代謝及胎兒成長的適當營養。
4 GDM孕前BMI與孕期增重的關系
孕婦孕前肥胖反映了母親的遺傳傾向、營養狀況、脂肪積累和低度炎癥,而孕婦在懷孕期間體重增加也反映了胎兒、胎盤和子宮的液體擴張和生長[29-30]。目前尚不清楚二者間是否有因果關系,以及這些關聯背后的機制。Mastella等[10]認為,高血糖和BMI升高的獨立作用勝過孕期體質量增加,因為他們通過母體的高血脂和相對胰島素不足介導的協同作用,進一步刺激胎兒胰腺分泌胰島素,促進胎兒宮內過度生長。但也有研究證實,懷孕前已經超重或肥胖的婦女中,過多的妊娠期體重增加對兒童超重/肥胖風險的額外影響很小[31]。且與體重正常和妊娠增重充足的婦女的子女相比,超重和肥胖母親的子女超重/肥胖的風險更高,而不管妊娠增重如何。孕期體質量增加過多,尤其是肥胖和超重女性,大于胎齡兒、巨大兒的發生率則越高[32]。表明了妊娠期體重增加的影響可能只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孕婦孕前BMI的影響。也有研究顯示,孕期體重增長過多是GDM孕婦出現分娩巨大兒等多種不良妊娠結局的獨立危險因素[33]。在未來,可進行多中心,大樣本的前瞻性研究,以消除混雜因素對實驗結果造成的影響,明確二者之間的聯系。
5 干預措施
隨著經濟水平的逐漸提高,人們的生活方式和飲食結構發生變化,而在妊娠這一特殊時期,運動量顯著減少,營養攝入又相對過多,GDM患病率增加已經成為一個重要的公共衛生及臨床問題。
5.1飲食及體育鍛煉
有研究表明,適度的個體化的生活方式干預,包括適度體育鍛煉與飲食干預相結合,可使高危孕婦中GDM的發生率降低39%[34],同時還能控制GDM孕期的體重增加,使GDM孕婦相關的不良妊娠結局得到改善。芬蘭的一項GDM預防研究表明,通過攝入富含水果、蔬菜和全麥谷物的飲食以及積極的體育鍛煉,GDM的風險可降低約40%[35]。Mijatovic-Vukas等指出與缺乏體育鍛煉的孕婦相比,孕婦在妊娠前和妊娠早期進行適當的體育鍛煉可使GDM的發生率降低30%和21%,且孕婦在妊娠前每周進行體育活動時間≥90min,可使GDM的發生率下降46%[36]。Nasiri-Amiri等采用病例對照研究對100例GDM孕婦和100例非GDM孕婦進行孕期體育鍛煉問卷調查,發現妊娠早期體育活動總量較低的女性發生GDM的風險高于體育鍛煉水平較高的女性(OR=4.12,95%CI:2.28~2.743,P=0.001)[37]。可以得出,適度的體育鍛煉對降低GDM發生率起到了積極的作用,尤其是孕前和妊娠早期作用更明顯,步行、游泳或水中有氧運動及瑜伽等運動方式均能夠幫助孕婦改善孕期代謝,加速脂肪分解,從而使得妊娠結局得到改善。
5.2 其他干預措施
對于孕前肥胖人群,也有專家建議可以進行藥物治療及減重手術。《2019SOGC妊娠期肥胖管理指南》中指出,在加拿大,藥物治療肥胖可選用奧利司他和利拉魯肽,但這兩種藥物均需在孕前停用。減重手術則是對消化道進行重塑,從而減少人體食物的攝入和吸收,改善代謝功能。在歐美國家已經成為一種安全、有效、常規的減肥方法。最常見的術式包括袖狀胃切除術(SG,45.9%)、Roux-en-Y胃旁路術(RYGB,39.6%)、可調胃束帶術(AGB,7.4%)和膽胰分流術(BD,1.1%)。但減肥手術后受孕間隔時間一直存在爭議,通常建議在進行減肥手術后至少避孕24個月[38]。指南推薦:建立產科團隊有助于對肥胖孕婦進行孕前、孕期、產時以及產后的管理(Ⅲ-3A)。產科團隊的建立,有助于對復雜多變的孕期進行更加全面的風險評估和制定適宜的分娩計劃,尤其對于高危人群益處更多。通過飲食及鍛煉等專業指導,達到科學、均衡、健康的孕前BMI和妊娠體重增加可以減輕妊娠并發癥的負擔,最終降低母嬰發病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