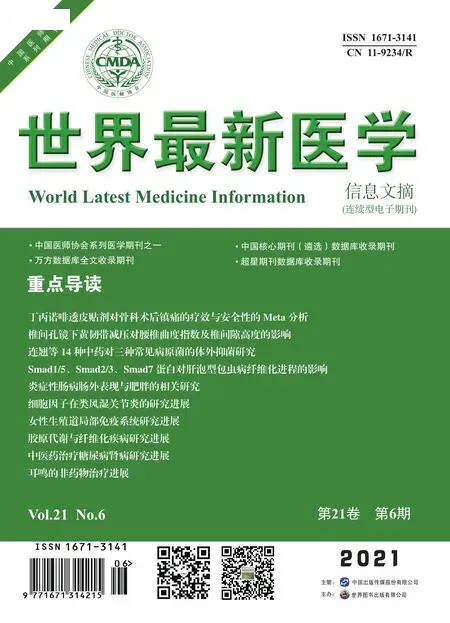女性生殖道局部免疫系統研究進展
胡蕊,俞晶,許金美,李茂余
(昆明醫科大學第三附屬醫院,云南省腫瘤醫院,云南 昆明 650000)
0 引言
女性生殖道(Female reproductive tract,FRT)包括上下兩部分,上FRT包括宮頸內口、子宮、輸卵管、卵巢,其黏膜層多由單層柱狀上皮組成;下FRT包括宮頸外口、陰道,其黏膜層多由鱗狀上皮組成。雖然生殖道位于體內,但與外界環境相通。因此生殖道黏膜作為免疫保護的哨兵成為第一道抵御防線。
女性生殖道免疫的特點,在于易受性激素影響,其包括先天性免疫和適應性免疫。先天性免疫主要由緊密連接的上皮細胞構成,適應性免疫主要由體液免疫和細胞免疫構成。上皮屏障的完整性能夠有效抵抗外界抗原入侵,這些上皮細胞除了維持保護狀態外,還進化出對病原體的反應,部分可通過Toll樣受體(Toll-like receptors,TLR)來增強免疫保護,并在必要時發起免疫反應。除上皮細胞的緊密連接外,生殖道中的粘液層及免疫細胞、免疫因子同樣發揮著重要免疫調節作用,如巨噬細胞、NK細胞、T淋巴細胞(Th1和Th2)、細胞因子、趨化因子等[1]。健康女性陰道免疫微環境處于一種動態平衡中,陰道局部免疫系統穩態的破壞有利于外界病原體的持久定植,最終導致疾病的發生[2]。因此,生殖道疾病的發生與陰道局部免疫狀態的改變有著密不可分的關系。
1 生殖道局部免疫檢測方法
目前,女性生殖道免疫測定方法多種多樣,因地域不同目前尚難達到統一的檢測標準。臨床中大多采用圓錐形宮頸細胞刷、局部黏膜組織活檢、陰道灌洗液等方式獲取標本。免疫檢測方法有酶聯免疫吸附法(enzyme-linked immunosorbent assay,ELISA)、流式細胞術、免疫印跡法、免疫組化單克隆抗體法、放射免疫分析(radioimmunoassay,RIA)、細胞因子微球檢測技術(cytokines beads assay,CBA)等[3]。
其中,ELISA能夠真實反映測定值在體內分泌的情況,在測定IgA、IgG水平上有一定的潛力,其靈敏度高,并可重復用于測量各種生物體液中的免疫球蛋白濃度。而流式細胞術可以更清楚具體細胞分泌的具體因子,而且可以定量,較ELISA測細胞因子水平更深入揭示機制,但需要在體外刺激后測出分泌的細胞因子量,所以此時只能反應細胞產生細胞因子的能力,而不能說明這個值能否代表體內真實情況[4]。RIA、CBA可以一次性檢測很多因子,實際上比ELISA更快、通量更大,但價格相對較高,臨床較少應用。
2 性激素與生殖道局部免疫環境
女性生殖道上皮細胞的獨特之處在于受甾體激素的調控,性激素水平的變化調控著FRT免疫系統變化、月經周期的改變、受精卵的著床、胚胎的發育等。Vitali,D等人發現內源性性激素(雌激素、孕激素)及外源性性激素類藥物能夠改變FRT防御屏障的成分,包括生殖道黏液黏度、生殖道PH值、上皮屏障厚度、免疫細胞和常駐陰道微生物等,繼而影響病原體的感染[5,6]。
研究表明,雌二醇和孕酮通過下層基質細胞直接和間接起作用,進而調節上皮細胞的先天性和適應性免疫功能,以保護免受潛在病原體的侵害,足夠的雌激素水平將有益于預防濾泡輔助性T細胞介導的自身免疫。另外,雌激素水平的降低會導致Th1/Th2平衡向Th1偏移,黏膜內皮細胞遭到一定損傷,進而增加機體局部炎癥反應[7]。一定程度的雌孕激素水平升高能夠作用于生殖道免疫細胞,增強細胞生長因子、IL-8、IL-1的表達,抑制IFN-α、IFN-β的生成,進而改變生殖道局部免疫功能,對于絕經后婦女而言,隨著體內雌激素水平下降,生殖道免疫微環境也發生著顯著變化[8]。
更有研究表明,在月經中期生殖道免疫功能出現抑制現象,在促進精子通過生殖道、受精卵形成的同時,同樣形成了月經周期中所謂的“脆弱窗口”,潛在的病原體更容易通過窗口期入侵機體[9]。女性成功的繁殖取決于性激素和多種生長因子的共同作用,受精、植入、胚胎發育的每個環節都離不開性激素的支持。性激素的免疫增強效果似乎是直觀的,但更應該檢測生殖道免疫反應的強度及過程,進一步了解性激素對免疫功能的影響。
3 陰道炎癥與生殖道局部免疫環境
陰道是女性生殖道的入口,與外界環境相通并且與尿道、肛門相鄰,性交、分娩及宮腔操作也均通過陰道完成,因此生殖道易受外原體入侵和感染。
研究表明,當陰道黏膜受到細菌或病原體入侵時,陰道局部將引發多種細胞因子及趨化因子釋放,如IL-1、IL-6、IL-8、IL-10、IL-12、 IL-17、GM-CSF、IFN-γ和TNF-α等[10]。Carey,AJ等人研究表明CD4+淋巴細胞分泌的IL-17在控制鏈球菌生殖道黏膜定植中起到重要作用[11],而念珠菌能夠主動抑制IL-17的分泌[10]。研究發現,在外陰陰道假絲酵母菌病(vulvovaginal candidiasis,VVC)的發病過程中,發揮保護作用的免疫分子IFN-γ、IgG、IL-17表達是降低的[12];而在細菌性陰道病(bacterial vaginosis,BV)中,加德納菌的定植并不總是導致BV的發生[13],免疫因子IL-1α、IL-1β及IFN-γ誘導蛋白IP-10在BV的發展上具有一定的臨床意義[14],同時Fruitwala,S等人認為人β-防御素2(HBD-2)和人防御素5(HD-5)可能參與防御BV等相關微生物的侵襲,而IL-4、IL-1的缺乏可能對BV的發病機制起作用[15,16]。
可見,當外源性病毒及細菌入侵女性生殖道時,陰道分泌物中存在的免疫物質提供了針對病毒和細菌感染的有效保護機制,此刻對機體而言生殖道黏膜免疫應答尤其重要[12]。
4 宮頸病變與生殖道局部免疫環境
子宮頸陰道部分在結構學和免疫學上與陰道相似。在宮頸感染的早期階段,多涉及巨噬細胞、樹突狀細胞、朗格漢斯細胞、自然殺傷細胞及多種細胞因子參與免疫反應。
4.1 HPV感染與生殖道局部免疫環境
持續高危型HPV感染與宮頸癌前病變及宮頸癌發生相關[17],HPV在宮頸粘膜上皮細胞定植,機體產生的抗體有時不足以對抗病原體的進攻,因此,除了評估全身免疫力外,宮頸局部免疫力的準確測量對于評估對HPV感染和疫苗接種的局部免疫反應也很重要。
近來,研究發現HPV的感染能促進生殖道中多種免疫細胞遷移并分泌IL-10或轉化生長因子β(TGF-β)等多種細胞因子來抵御感染[18]。Nguyen,PV等人表明宮頸上常駐有IgA漿細胞,當宮頸受到外界病原體感染時,上皮細胞將釋放促炎細胞因子IL-8、IL-10及趨化因子[19],以介導炎癥反應的開始及免疫細胞向感染部位的募集,同時也表達β-防御素參與免疫機制反應。
相關研究表明,Th2細胞因子水平增加和Th1細胞因子(例如IFN-γ、IL-12、IL-2、IL-33和TNF-α)水平降低與HPV感染及宮頸病變發展有一定相關性[20]。同樣,生殖道中IL-10、IL-2、IL-23水平變化與宮頸癌前病變發展有關,但阻斷類似IL-10等細胞因子似乎并不簡單,可能是免疫因子在不同濃度和不同環境中具有多種免疫調節作用所致[21,22]。
4.2 宮頸病變與生殖道局部免疫環境
Petrini,CG等人,從HPV感染的宮頸組織中檢測多種細胞因子,結果顯示相對活檢正常組,宮頸癌前病變組織中的IL-2、IL-18、IL-23和IL-1β水平較低,低水平的IL-2、IL-18、IL-23細胞因子可能與病毒持續存在及癌前病變發生有關[23,24]。另有研究顯示,隨著宮頸病變程度的增加,陰道免疫因子IL-2減少,IL-10增加,IL-2 / IL-10減少,而SIgA和IgG增加,IL-2 / IL-10比率的降低以及SIgA和IgG水平的變化都可能影響宮頸病變的發展[25]。同時,Colacurci,N等人[26]在不同級別宮頸細胞中檢測免疫表型,結果顯示CD29、CD38、HLA-I和HLA-II的高表達與CIN程度正相關,這些細胞及標志物的高表達有望作為持續感染患者的檢測指標。
另外,Sahin,E等人對LSIL、HSIL及正常患者分別采取宮頸分泌物,使用ELISA方法檢測各組宮頸粘液中分泌白細胞蛋白酶抑制劑(secretory leukocyte protease inhibitor,SLPI)水平,結果顯示LSIL和HSIL組的宮頸粘液SLPI水平明顯高于正常組,SLPI似乎是宮頸黏膜中提供局部免疫應答的重要免疫調節蛋白[27]。Fahim,NM等人對SIL、LSIL、HSIL及宮頸癌患者的宮頸組織通過PCR方法檢測人類白細胞抗原-G(Human leukocyte antigen-G ,HLA-G)表 達 情 況,結果顯示HLA-G表達從癌前期和癌性宮頸病變逐漸增加,但HPV陽性和HPV陰性宮頸病變之間HLA-G沒有顯著差異,此外該研究通過抑制宿主免疫應答觀察到HLA-G在功能上涉及腫瘤逃逸機制[28]。同時,Chauhan,A等人研究表明Toll樣受體(Toll-like receptor,TLR)參與宮頸癌的發病機制,其中TLR4和TLR9在宮頸病變應答的誘導上起關鍵作用,然而宮頸癌中血清TLR濃度的顯著性尚不清楚,目前仍需進一步研究TLR的預后價值[29,30]。
Th9細胞是T細胞中新發現的一個亞群細胞,近年來,一些研究多集中在IL-9/IL-9R信號傳導通路的調節及IL9細胞在腫瘤細胞中的作用,Chauhan,SR等人研究表明細胞因子IL9能夠抑制HeLa細胞增殖,增強細胞的凋亡并刺激MHCI的表達,并且在宮頸病變組織中存在IL-9R過表達現象[31],Th9似乎增強了抗腫瘤免疫反應,但具體機制仍需要進一步研究。
近年來,研究逐漸證實了生殖道局部免疫功能的削弱是宮頸病變發生發展的重要因素。但宮頸免疫學環境并非單一存在,其受陰道微環境及遺傳因素影響,了解其涉及機制有望為宮頸相關疾病的療法奠定基礎。
5 全身免疫與生殖道局部免疫環境
生殖道局部免疫是女性全身免疫的一部分,生殖道局部感染病原體后,機體抵抗大多是細胞免疫,主要在生殖道局部起作用。目前關于生殖道疾病的全身免疫與局部免疫的關系研究較少。臨床中,全身免疫多通過采集外周血進行檢測,生殖道局部免疫多通過采集陰道灌洗液或活檢病變組織進行檢測。
Xue,J等人,通過對宮頸癌及癌前病人外周血及宮頸組織離心的上清液進行細胞因子IL-17檢測,結果發現在HPV感染的病人中,不論其宮頸病變程度如何,宮頸組織中的IL-17水平均高于外周血,免疫抗體能夠以宮頸上皮細胞滲出的方式與外周血相通[32]。另外,凡是患有免疫系統疾病(例如系統性紅斑狼瘡、HIV)的女性無論是否進行免疫抑制治療,其患宮頸癌前病變和癌癥的風險都高于普通人群[33,34],機體全身免疫的降低將有助于生殖道病原體入侵定植。另外,Chen,Z等人通過ELISA方法檢測宮頸病變患者及正常患者血清IL-10水平,發現宮頸病變組中外周血IL-10水平顯著高于正常組[35]。宮頸癌是涉及到黏膜組織的疾病,而黏膜相關不變性T細胞(Mucosal-associated invariant T cells ,MAITs)對于抵抗傳染性病原體的免疫防御和調節各種炎性疾病具有重要意義,Huang,WC等人通過流式細胞術檢測宮頸癌患者及正常患者外周血CD3細胞中MAITs水平,研究顯示宮頸癌患者外周血中MAITs比例更低,并且越低的MAIT宮頸癌患者PFS越差[36]。
目前HPV疫苗是全球首個把癌癥(宮頸癌)作為適應證列入說明書的疫苗,至今上市的HPV疫苗有2價、4價、9價三種,“價”代表疫苗可預防的病毒種類。HPV疫苗產生的抗體會通過宮頸上皮細胞滲出作用于局部生殖道免疫,但目前還不清楚子宮頸局部免疫是否或如何影響HPV疫苗功效的長期持續時間[37]。不過,相關研究顯示通過支持生殖道局部免疫因子sIgA、溶菌酶及C3補體成分的穩定生長,有望緩解女性生殖道疾病的發展[38]。盡管HPV疫苗產生的特異性抗體在陰道分泌物中的滴度低于血清,但在陰道分泌物中檢測抗體也是可行的,未來陰道黏膜部位的特定疫苗接種有望成為刺激女性生殖道免疫的首選途徑[39]。
疫苗重在預防,而不是治愈。理想的疫苗既需要引起細胞介導的免疫又要激發體液免疫,雖然許多候選疫苗正在動物模型中進行廣泛測試,但仍需更多臨床研究進行考量[40],或許從黏膜免疫系統的分子和細胞方面以及它們對傳染病、炎癥和免疫系統疾病的防御機制入手更易于研發新的疫苗。
6 小結
正常女性生殖道的免疫微環境復雜且穩定,需要先天性免疫及適應性免疫共同維持。機體免疫功能在病毒的清除及疾病的發生發展中起重要作用,生殖道的各個部位免疫應答獨立存在又相輔相成。生殖道黏膜作為天然屏障的重要組成部分,通過免疫調節機制改變生殖道菌落將有望對生殖道感染的治療提供策略,但如何提高生殖道局部免疫,尚有待于進一步的深入研究。近年來,對女性生殖道菌群、生殖道黏膜免疫、黏膜疫苗的研究以成為女性生殖道微生態研究的熱點,相信不久的將來,生殖道免疫狀態會更加清晰的擺在人們面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