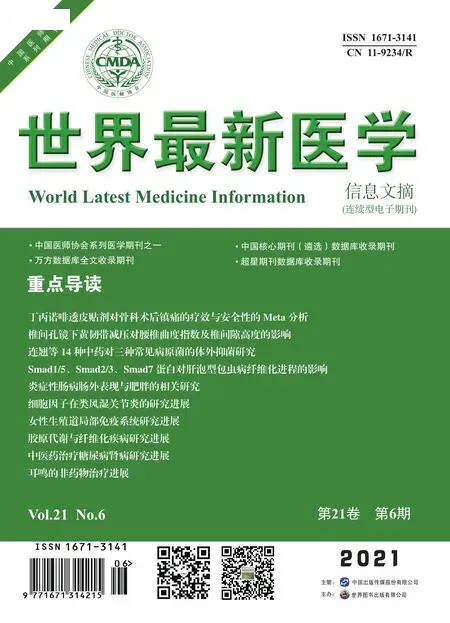王平教授治療失眠合并焦慮癥驗案三則
陳艷華,張旖旎,李非洲,王平*
(1.湖北中醫藥大學中醫臨床學院,湖北 武漢 430061;2.湖北中醫藥大學老年醫學研究所,湖北 武漢 430065)
0 引言
失眠,中醫稱為“不寐”。不寐是一類以經常不能獲得正常睡眠為特征的病證,臨床上表現為睡眠的時間、深度不足,輕者入睡困難,或寐而不酣,時寐時醒,或醒后不能再寐,重者徹夜不能寐,常影響人們白天的生活[1]。焦慮癥是西醫的診斷,根據其臨床癥狀,在中醫上可以歸于“心悸”、“郁證”等范疇,表現為心悸膽怯、善驚易恐、精神恍惚、情緒不寧、坐臥不安、失眠多夢、胸脅脹滿、注意力不集中、食欲不振、腹脹便溏等。
失眠和焦慮既可獨立發生,也可相伴存在,兩者關系錯綜復雜,包括失眠引發的焦慮,焦慮促發的失眠和失眠與焦慮共病,因果難分[2]。研究表明,70%-80%精神障礙患者均報告有失眠癥狀,而50%的失眠患者同時患有1種或1種以上精神障礙[3]。流行病學研究結果顯示,40%~92%的失眠癥狀由精神疾病引發[2]。失眠會增加發生焦慮癥的風險,焦慮亦會增加新發失眠的風險,失眠的嚴重程度與焦慮嚴重程度有關,故在治療時應重視同治[4]。
王平教授是湖北中醫藥大學教授,博士研究生導師,岐黃學者,湖北省首批醫學領軍人才,全國名老中醫學術經驗優秀繼承人及指導老師。王平教授認為飲食不節、情志失調、勞逸過度、病后體虛、環境變化等均可引起失眠,其中以情志失調、環境變化、病后體虛常見。《靈樞·百病始生》說:“喜怒不節則傷臟”。七情傷人直傷五臟,五臟失和則寐不安[5]。在失眠的治療中,情志的調節占有重要地位。
1 病機淺析
1.1 心神失養
為直接病機人的睡眠由心神控制,營衛陰陽的正常循行是心神調節睡眠的基礎。《靈樞·口問》云:“衛氣晝行于陽,夜半行于陰,陰者主臥,夜者主臥。”“陽氣盡,陰氣盛,則目暝;陰氣盡而陽氣盛,則寤矣。”《靈樞·大惑論》云:“衛氣不得入于陰,常留于陽。留于陽則陽氣滿,陽氣滿則陽盛不得入于陰,則陰氣虛,故目不瞑矣”。正常人氣血旺盛,營衛調和,則晝精夜暝。病理狀態下,陰陽失去平衡,導致疾病的產生,一則陰虛不能受納陽氣,二則陽氣過于亢奮,不能入于陰分。心陰血不足,心神失養而導致失眠。王平教授認為,臨床上失眠病人以虛證居多。
1.2 元氣不足
為根本腎氣又稱為元氣,腎精化腎氣,腎氣又分為腎陰和腎陽,腎中陰陽為一身陰陽之根本,因此是臟腑之氣中最重要者。腎精以秉承父母的先天之精為基礎,后天脾胃所化生之精為補充。病理狀態下,各臟腑的氣血陰陽不足,必然會累及到腎臟。元氣虧虛則百病生[6],王平教授臨床上緊緊抓住這個基本點,在治療疾病的過程中不忘固護元氣。
1.3 情志不舒
貫穿始終《素問·舉痛論》云:“怒則氣上,喜則氣緩,悲則氣消,恐則氣下,驚則氣亂,思則氣結”。《三因極一病證方論·七氣敘論》中說:“喜傷心,其氣散;怒傷肝,其氣出;思傷脾,其氣結;悲傷心,其氣散;恐傷腎,其氣怯;驚傷膽,其氣亂”。
情志活動是對外界刺激的應答,各種情緒變化與氣的運動變化密切相關,情志異常會導致氣的升降出入聚散失常,進而產生各種疾病。肝主疏泄,能疏通、暢達全身氣機。若肝氣調暢,則心情開朗、心境平和、情志活動適度,若肝氣郁結或亢逆,疏泄失常,則易導致情志活動異常。《醫貫·郁病論》說:“予以一方治其木郁,而諸郁皆因而愈。一方曰何?逍遙散是也”。臨床上因為情志導致失眠的患者,王平教授常進行睡眠衛生教育、睡眠限制療法、放松療法,配合疏肝解郁方藥,促進失眠的好轉。
2 驗案舉隅
2.1 案1
患者某,男,64歲。2020年8月30日因“睡眠不佳9年余”首診。現病史:患者自訴2011年無明顯誘因出現睡眠不佳,后背燥熱,心跳快,胸口憋悶感,頭昏,血壓升高,診斷為焦慮癥,住院治療后癥狀緩解,服藥治療。今年2月份因家中瑣事焦慮加重,睡眠不佳,入睡困難,睡眠質量差,急躁易怒,服用枸櫞酸坦度螺酮、草酸艾司西酞普蘭、米氮平治療。飲食一般,口干口苦,小便正常,大便稀溏。既往史:膽囊切除術,前列腺手術史。查體:Bp 110/80mmHg。舌脈:舌紅苔黃;脈浮弦稍數。西醫診斷:1.焦慮癥2.失眠。中醫診斷:不寐(肝郁脾虛,肝火擾心證)。治則:疏肝健脾,寧心安神。處方:制香附10g,川芎10g,蒼術10g,梔子10g,焦山楂10g,神曲10g,黃連10g,法夏10g,竹茹10g,厚樸10g,柴胡10g,枳殼10g,干姜10g,丹參15g,草果仁15g,白豆蔻15g,夏枯草10g,淡豆豉15g。7劑,水煎服;一日一劑,分三次溫服。
2020年9月6日,二診。患者訴服上方后睡眠改善,心跳平緩,左側少腹部下午2點感不適,不可描述其性質,下午4點減輕。大便時可成形。舌脈:舌紅苔微黃;脈弦緩。處方:柴胡10g,枳殼10g,白芍15g,赤芍10g,丹參15g,黃芪30g,川芎10g,郁金10g,五味子15g,蒼術10g,川楝子10g,懷牛膝15g,梔子10g,煅龍骨20g,煅牡蠣20g,棗仁30g,合歡皮10g,廣木香10g,沙參15g炙甘草6g。14劑,水煎服;一日一劑,分三次溫服。
2020年9月20日,三診。患者訴現睡眠可,情緒較前放松,仍覺左側脅肋下有搏動感,飲食、二便可。舌脈:舌稍紅苔黃稍膩,脈浮弦。處方:仍宗前方,去丹參、赤芍、黃芪、五味子、廣木香、合歡皮、川楝子,加知母10g,茯神10g,夜交藤30g,太子參15g。14劑,水煎服;一日一劑,分三次溫服。
按:《辯證錄·不寐門》云:“夫憂愁之人,未有不氣郁者也。氣郁既久,則肝氣不舒”。患者肝郁日久,脾失健運,郁而化火,肝火擾心,心神不安。故方可用柴胡疏肝散、梔子豉湯、酸棗仁湯化裁。首診時方用香附、柴胡疏肝解郁,枳殼、川芎行氣寬中,夏枯草清肝瀉火,黃連、梔子、淡豆豉、竹茹、丹參清心除煩,干姜溫通經脈,法夏、厚樸、蒼術、草果仁、白豆蔻、焦楂曲燥濕健脾,助脾胃之運化。二診時患者睡眠改善,大便時可成形,焦慮癥狀減輕,調整用藥,二診時側重于疏肝、行氣、安神,減少健脾胃藥物。方用柴胡、郁金疏肝解郁,川芎、枳殼、木香、川楝子行氣止痛,白芍、赤芍同用,入肝經,養血活血,體現肝臟“體陰用陽”之性,蒼術燥濕健脾,黃芪補氣健脾,沙參養陰益胃,梔子、丹參瀉火除煩,加用酸棗仁、合歡皮、煅龍牡四藥合用加強安神之功,久病及腎,加用懷牛膝、五味子補益肝腎,炙甘草調和諸藥,兼有補脾和胃之效。三診時癥狀明顯改善,故仍守前方,稍作化裁。去丹參、赤芍、五味子、木香、川楝子,改黃芪為太子參,改合歡皮為茯神、夜交藤以養血寧心安神,加知母滋腎陰,腎陰滋養心陰,心血充足則心神得養。
2.2 案2
患者某,男,28歲。2020年8月11日因“睡眠不佳半年余,伴頭痛加重2月”首診。現病史:因工作原因需長期于凌晨12:00-04:00工作,工作壓力大,2019年12月出現睡眠不佳,表現為入睡困難,多夢易醒,可復睡,連續失眠則頭痛,頭部緊束感,甚則心慌心悸,焦慮,脾氣急,易怒,未予以特殊處理。2月前頭痛加重,睡眠同前,腿部肌肉麻木刺痛感,偶有左足趾疼痛,飲食、二便可。既往史:高尿酸血癥,高脂血癥。舌脈:舌質紅苔薄白,舌尖紅;脈細弦。西醫診斷:1.失眠2.高尿酸血癥3.高脂血癥。中醫診斷:不寐(心肝火旺證)。治法:清肝瀉火,養心安神。處方:酸棗仁30g,川芎10g,知母10g,茯神10g,夜交藤20g,梔子10g,淡豆豉20g,合歡皮15g,懷牛膝15g,車前子15g,丹參15g,夏枯草10g,百合15g,炙甘草6,煅龍骨20g,煅牡蠣20g。7劑顆粒劑,水沖服,日一劑,分三次服。
2020年8月28日,二診。患者訴服上方后睡眠較前改善,入睡較快,偶有易醒,醒后可復睡。未訴頭痛,有足趾疼痛,飲食、二便可。輔檢:2020.8.23查尿酸516mmol/L。舌脈:舌邊尖紅苔根部稍膩;脈浮稍弦。處方:仍宗前方加熟附片10g,續斷15g,威靈仙15g,金錢草15g,豬苓10g,改車前子15g,蒼術10g,黃柏10g,去淡豆豉、茯神。7劑顆粒劑;水沖服,日一劑,分三次服。
按:方用酸棗仁湯、梔子豉湯化裁。方中重用酸棗仁、夜交藤、茯神養血寧心安神,煅龍牡重鎮安神,合歡皮解郁安神,百合清心安神,七藥同用,其安神之力強,梔子、淡豆豉、丹參清心瀉火除煩,川芎可行氣活血,《本草匯言》記載川芎善“中開郁結”,夏枯草清肝火,知母清心火、滋腎陰,懷牛膝補肝腎、強筋骨,車前子清熱利尿通淋,炙甘草調和諸藥、緩急止痛。二診時患者頭痛未發,睡眠改善,有腳趾疼痛,尿酸高,考慮濕邪為患,在治療睡眠的同時兼顧關節疼痛,故仍守上方,稍作化裁。去淡豆豉、茯神,加用熟附片散寒除濕止痛,《本草匯言》記載附片為“通關節之猛藥也”,續斷以強筋骨、補肝腎,威靈仙以祛風濕、通經絡止痛,加大車前子用量、加用金錢草、豬苓以利水通淋,金錢草亦可解毒消腫,黃柏清熱燥濕、瀉火解毒,蒼術健脾燥濕、助脾胃運化水濕。
2.3 案3
患者某,女,60歲。2018年8月21日因“睡眠差20余年”首診。現病史:20余年前即出現睡眠不佳,表現為入睡難,易醒,夢多,醒后難以復睡,需服用艾司唑侖(1#,po,qd)維持睡眠,驚恐不能獨自乘車、乘電梯、獨處,常臆想,擔心被人害,大便干,胃脘灼熱感,畏寒,口干,口苦,有反酸,飲食一般,小便正常。既往史:23年前因房屋裝修,發生呼吸困難,經搶救好轉,有恐懼癥、焦慮癥,黛力新1片,3天/次。高脂血癥病史。舌脈:舌紅,苔白略厚,邊齒印,脈細弦。診斷:1.失眠癥;2.焦慮癥。中醫診斷:不寐(心膽氣虛證)。治法:益氣鎮驚,安神定志。處方:生曬參10g,丹參10g,生熟黃15g,熟地黃15g,法半夏10g,陳皮10g,黃芪20g,當歸10g,烏賊骨15g,火麻仁20g,炙甘草6g,白芍10g,棗仁20g,川芎10g,天麻10g,夏枯草10g,梔子10g,煅龍骨20g,煅牡蠣20g,合歡皮10g,玄參15g。14劑,水煎服;日一劑,分三次服。
2018年9月4日,二診。患者訴服上方前7天睡眠明顯好轉,可停服艾司唑侖,但近一周睡眠有所反復,需隔日服艾司唑侖,仍有恐懼感,不能獨自外出,便秘好轉,胃脘灼熱減輕,胃脘嘈雜感明顯、輕度隱痛,輕度口苦,反酸,胃脹明顯,乏力,精神欠佳,頭沉重感。舌脈:舌紅,苔白厚膩;脈細稍弦。處方:仍宗前方去梔子、玄參、火麻仁,改丹參15g,加竹茹10g,燈心草2g,仙靈脾15g,桂枝10g,干姜5g,細辛2g。14劑,水煎服;日一劑,分三次服。
2018年10月9日,三診。患者訴睡眠明顯改善,現服用艾司唑侖,1片,3-4天/次,便秘好轉,現有胃脘部脹滿,打嗝后稍舒,反酸、口苦較前好轉。天氣變化時有心慌、胸悶。舌脈:舌淡暗,苔薄,邊少許齒痕,脈細稍弦。處方:太子參15g,白術15g,茯苓15g,法半夏10g,厚樸10g,生曬參10g,桂枝10g,煅瓦楞15g,合歡皮15g,竹茹10g,靈芝10g,仙靈脾15g,續斷10g,黃芪20g,地 骨皮15g,枳殼10g,石 斛15g,陳皮10g,膽星5g,焦山楂10g,神曲10g,炒麥芽10g,炙甘草6 g。14劑,水煎服;日一劑,分三次服。
按:《素問·舉痛論》說“驚則心無所依,神無所歸,慮無所定,故氣亂矣。”《靈樞·本身》記載到驚恐不解則傷腎精,精傷則骨痠痿厥。患者因暴受驚嚇,導致心虛膽怯,心神失養。心虛則神不內守,膽虛則少陽之氣失于升降,決斷無權,則肝郁脾失健運,痰濁內生。方用生曬參大補元氣、安神益智,黃芪增強補氣之功,生熟地同用滋補腎精,法夏、陳皮健脾燥濕化痰,酸棗仁養心安神,合歡皮解郁安神,煅龍牡重鎮安神,丹參、梔子、玄參瀉火除煩安神,白芍養肝血,當歸補血活血,川芎活血行氣,三藥同用補而不滯,夏枯草清肝瀉火,天麻通絡、平抑肝陽,烏賊骨制酸止痛,火麻仁潤腸通便,炙甘草調和諸藥。二診時患者睡眠改善,艾司唑侖減量,便秘好轉,故仍守上方,加以化裁。去梔子、玄參、火麻仁,增加丹參用量,加用竹茹清熱化痰除煩,燈心草清心火,加仙靈脾補腎陽,與生熟地同用,同補腎中陰陽,干姜、桂枝溫通經脈,細辛祛風止痛。三診時患者睡眠穩定,以脾胃問題為主要矛盾,因患者病程長,故調整診處方以補氣健脾為主,故兼以安神、補益肝腎。
3 小結
失眠特別是慢性失眠更容易發生其它疾病。在臨床上,王平教授認為需要辨別疾病的先后順序,有無因果關系,孰因孰果,在疾病的不同階段,審因辨證,因證立法施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