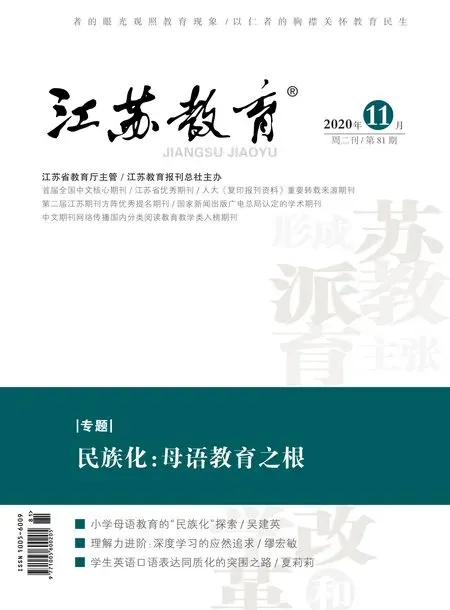“三體對話”:協同學習觀照下數學對話的新路徑*
蔣 虹
協同學習是一種通過對話實現同伴互助、教師輔導的教學策略。日本教育學家佐藤學認為它主要由三個要素組成:組織符合學科本質的學習、建立相互傾聽的對話關系、提出有挑戰性的問題并展開高層次的思考和探究。那么,如何使這三個要素有機融合呢?筆者認為,深入數學對話是一條重要的路徑。教師在教學中可以設法構建一個立體空間,引導學生進行一種精神相遇的深入對話活動。
一、三體對話的內涵
三維世界觀認為:萬物都在一定的空間存在。x、y、z是關鍵性的三個向度,決定著這個空間的大小與走向。學習對話同樣如此,存在著特定的對話空間。三體對話是指教師引導學生分別與現實世界對話、與他人同伴對話、與自我內心對話。在這樣三位一體的對話活動中,引導學生辯證地理解知識,系統地自主構建,從而使每個學生深度卷入學習之中。與現實世界對話、與他人同伴對話、與自我內心對話相當于x、y、z 三個向度,穩定地構成立體的對話空間(如圖1)。它具有三向性,向思維的寬度、廣度和深度延展;它還具有均衡性,延展要平衡、融合、共生。三個向度發展得越和諧,對話空間就越寬廣,認知活動就越深入。三體對話具有平等性、積極性、序列性、立體性,它的空間建構決定著學生學習的深度和品質。
二、三體對話在數學協同學習中的價值
(一)提升深度理解力
數學學習注重客觀事實,數學知識的建構需要去情境、去形式、去個體,也就是在對話中要達到共性的理解。三體對話提供多種路徑,讓學生在討論、交流、爭辯和優化的過程中完成對知識的個性化處理和轉換,從而達成意義建構。這個過程既能讓學生對知識本質達到融會貫通,又能鍛造他們的深度理解力。
(二)提升高階思維力
數學思維力是一種數學化的思維方式。在三體對話中,有需要做出邏輯判斷的問題情境,有能引發獨立思考的學習過程,更有能形成思維矛盾沖突的交流機會,學生充分運用數學化思維去發現問題、提出問題、分析問題和解決問題。這個過程,在讓學生的思維有機融入學習的同時,更能培養學生思維的深刻性、嚴謹性和批判性,使其向高階思維轉化。
(三)提升綜合學習力
史寧中教授提出:數學核心素養是指具有數學基本特征的、適應個人終身發展和社會發展需要的人的思維品質與關鍵能力,也就是讓學生會用數學的眼光觀察世界,會用數學的思維思考世界,會用數學的語言表達世界。在三體對話中,學生積累了豐富的數學學習活動經驗,感受智慧,實踐智慧,從而生成智慧,培養綜合學習力。
三、三體對話讓協同學習真正發生
(一)x 維:與現實世界對話——寬度決定量的積累
1.結構對話導引,讓思維有軌可行。
數學思維是動態的過程。在對話伊始,要給學生提供結構化的對話導引,可以是顯性的學習卡、學習任務、核心問題,也可以是隱性的、不同層級的探究活動。如此,才能讓學生的數學思維有軌可行,能聚焦,能遷移。比如,教學蘇教版五下《和與積的奇偶性》一課,筆者為學生提供了三個探究活動對話單:①號對話單讓學生“研究兩個非0 自然數的和的奇偶性”;②號對話單讓學生“模仿研究多個非0 自然數的和的奇偶性”;③號對話單讓學生“獨立研究若干個非0 自然數的積的奇偶性”。從研究目標和研究方式可以看出,這是三個不同層級的自主探究對話單。三個活動中舉例的設計與結論的表達,從設定格式到半開放再到完全開放,讓學生經歷了探究方法類比遷移的過程,充分體現了“用結構學結構”的理念,學生從“他組織”走向“自組織”,其書面表達更是化無形為有形,真實刻畫出了他們的思維軌跡。
2.個性對話表征,讓思維有跡可循。
思維是人類特有的高級認知活動,具有內隱性、抽象性等特征,小學生的數學思維基本處于具體形象階段或初級抽象階段,發展水平極不均衡,類型、特點也有差異。因此,他們在與現實世界對話的過程中形成了豐富的、個性化的意義表征。教師適時鼓勵學生把這些思維痕跡真實地呈現出來,將會為其接下來與他人同伴對話提供差異性的寶貴資源。比如,教學蘇教版五上“解決問題的策略:列舉”單元例2:南山中心小學舉行小學生足球賽,有4 支球隊參加,分別是紅隊、黃隊、綠隊和藍隊。如果每兩支球隊比賽一場,一共要比賽多少場?學生利用文字、符號、圖(圖形、圖畫、圖表等)、算式等不同的方式進行了思維的可視化表征,但他們的思維水平有一定的差異。大部分學生的思維需要借助較為具體形象的方式來演示,少部分學生的邏輯推理能力較強,能將生活中的實際情境轉化為抽象的數學模型。這些不同的表征方式讓學生與客觀現實的對話思維躍然紙上,形成了充盈的再生資源。
(二)y 維:與他人同伴對話——廣度決定質的變化
1.逐層式路徑推進。
語言是思維的外殼。在初級認知資源板塊化呈現時,學生就要在教師的引領下,通過序列化的言語對話闡述自己的觀點,傾聽他人與同伴的想法,在對比中分享,在分享中質疑,在思辨中糾偏,在互補中完善,促使思維逐層深入。比如,教學蘇教版三下《小數的初步認識》,學生在教師引導下,通過兩個層次的對話建構小數“0.5”的本質意義。
第一層次:具象表示“你的0.5米”
師:怎樣表示0.5米?
生1:畫一條直線表示1 米,將這條直線分成2份,其中很小的一部分就是0.5米。
生2:我覺得這樣不準確,很小的一部分可以是0.5 米,也可以是0.4 米。應該將整個線段平均分成10份,其中的5份才是0.5米。
生3:我也覺得應該平均分,不過我不是畫線段,而是畫一個長方形表示1米……
第二層次:抽象出0.5米的含義
師:雖然大家用不同的方式表示1 米,但都能準確表示0.5米。這些方法有什么相同點?
生4:雖然用不同的方式表示1 米,但都是將它平均分成10份,都是取其中的5份,因而都可以用0.5米來表示。
透過學生、教師以及同伴之間的對話,不難發現,不同的學生呈現出了不同的思維表征水平,教師引導學生把自己的思考表達出來,并不斷在分享、對話、溝通中求同存異,從而逐步走向抽象。可以說,與他人同伴深入對話,可以讓學生的思維從零散走向結構、從膚淺走向深刻。
2.模式化思維融合。
從本質上來說,數學是在抽象、概括、模式化的過程中逐漸發展和豐富的,只有深入到“模型”“建模”的意義上,數學學習才是真正發生了。在三體對話中,正確理解概念或解決問題只是達成了一種短程目標。教師注重挖掘概念或問題的核心內涵,拓展其與外部世界的聯系,建立包容性強的問題模型,將能真正促進學生的數學理解。比如,教學蘇教版五下“列方程解決行程類問題”,學生很容易就能在對話中明晰:當貨車的速度未知,而總路程已知時,可以利用“客車的路程+貨車的路程=總路程”“速度和×時間=總路程”這些等量關系來列方程解決相遇問題。但這樣的理解是淺層次的,數學對話不能就此停止。教師還可以給學生提供一組生活中的實際問題(挖隧道問題、購物問題、面積問題等),引導他們繼續研究和對話。最后通過比較、抽象發現:只要已知兩個部分的總和,求其中一個部分的量,就可以用“一部分量+另一部分量=總數”這個等量關系來列方程解決,而乘法的等量關系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如此,就水到渠成地建構出了方程中加法等量關系的模型。
(三)z維:與自我內心對話——深度決定體的形成
1.與前我對話,完善現我。
與現實世界對話,基于“我”的視域掌握的信息可能是片面的、存在謬誤的。與他人同伴對話,基于“我們”的視域掌握的信息可能是被動的、零碎的。因此,與自我內心對話的首要目標是內化統整,形成“現我”的系統知識網絡。比如,蘇教版四下“三角形、平行四邊形和梯形”單元集中認識三種平面圖形的特征,輸出的信息量巨大,大部分學生概念模糊,甚至混亂不清。因此,在單元練習前,筆者讓學生繪制思維導圖。畫思維導圖是促進學生與自我內心對話的一種重要方式,能讓其思維從混沌走向明朗,從中心朝著各個方向自由發散、自由表達。
2.與現我對話,指向未我。
蘇聯結構主義符號學的代表人物之一巴赫金說,對話是一個無限進行的過程,永遠沒有終點。在與自我內心對話的過程中形成“現我”的系統知識網絡,具有開放性和衍生性。在它逐漸成熟的過程中,又會產生新的學習欲望,從而引發與現實世界對話的新需求。然后,又會引起第二次三體對話活動,這樣立體循環的對話活動會觸發學習向更深處進發。比如,教學蘇教版五上《三角形的面積》一課,探究三角形的面積公式時,學生在教師引導下理解并構建出“把兩個完全一樣的三角形拼成一個平行四邊形,根據平行四邊形的面積公式推導出三角形的面積公式”這一觀念。其實教師往往都容易忽略這一點,受到前一課“平行四邊形轉化成長方形”活動經驗的直接影響,學生更傾向于“直接把三角形剪移,拼成一個長方形或平行四邊形”這種操作性思維。所以,學生往往會產生這樣的疑問:還可以通過什么方法把三角形轉化成我們學過的圖形?這就促使他們繼續與客觀世界對話,深入探索,從而發現更多方法(如圖2)。這樣的學習才是發生了真正的深度覆蓋,培養了學生的立體思維。
佐藤學說,協同學習就像演奏一首交響樂,每一個人就像不同的樂器,發出不同的聲音。當各種聲音和諧地匯聚在一起,就奏出了一首動聽的樂曲。三體對話就創造了這樣一個對話空間,從此,深度協同學習就在這兒發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