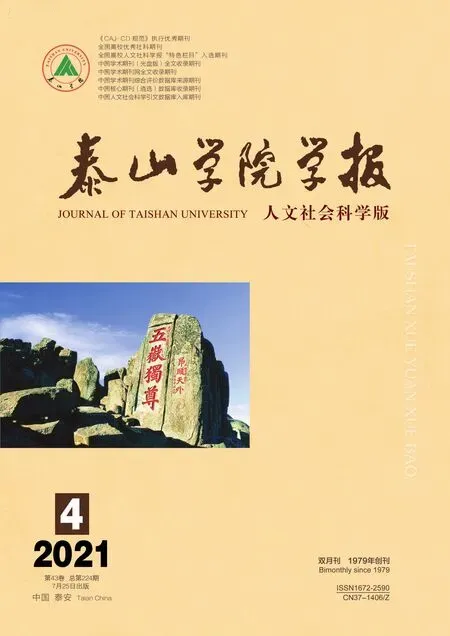以書寫抵抗遺忘
——陳河小說的戰(zhàn)爭敘事探析
盧文婧
(吉林大學(xué) 文學(xué)院,吉林 長春130012)
在文學(xué)視野中,“戰(zhàn)爭”是一種獨特而又沉重的存在,它作為文本指涉性話語和被描述的對象,往往承載著國族敘事、革命敘事、倫理敘事等宏大的敘事功能。戰(zhàn)爭敘事在海外華文文學(xué)的創(chuàng)作中占據(jù)著重要地位,由于創(chuàng)作主體生活閱歷、知識經(jīng)驗、文化視野、歷史體悟的不同,戰(zhàn)爭敘事也呈現(xiàn)出多元的文學(xué)狀貌,如嚴歌苓、張翎、虹影、陳河等作家作品中的“戰(zhàn)爭敘事”就既有同一性又有異質(zhì)性。陳河小說的戰(zhàn)爭敘事在海外華文文學(xué)以及當(dāng)代文學(xué)視域中是突破性的代表,他旅居海外的經(jīng)歷、傳奇豐富的人生、國際性的歷史文化視野、先鋒與傳統(tǒng)并置的筆法使得其作品的戰(zhàn)爭敘事呈現(xiàn)出深闊的格局,為當(dāng)代戰(zhàn)爭文學(xué)開拓出新的天地。
一、多維度的文本空間
戰(zhàn)爭敘事是歷史書寫的一部分,具有記憶歷史、警醒現(xiàn)世的文本功能,它獨具的歷史性使得創(chuàng)作主體在書寫的過程中就要具有一定的歷史意識、當(dāng)下意識和未來意識。“‘歷史科學(xué)’是歷史‘事實’的見證,而藝術(shù)作品則是歷史‘生活’的見證。科學(xué)家看到的是鐵板釘釘?shù)摹聦崱凰囆g(shù)家眼里則是活生生的‘人’和‘事’。他們的眼光雖然各有不同,但‘看到’的都是‘歷史’,而不是‘非歷史’。”①葉秀山.葉秀山文集(美學(xué)卷)[M].重慶:重慶出版社,2000:556-557.文學(xué)作品描寫的戰(zhàn)爭大多有一定的歷史依據(jù),關(guān)于歷史的戰(zhàn)爭經(jīng)過創(chuàng)作主體的再加工再創(chuàng)造以文本的方式體現(xiàn),即使會受到創(chuàng)作者的個體經(jīng)驗、文化視野和歷史體悟差異的影響,但是都具備著“見證”歷史的作用。
在海外華文文學(xué)作品中,戰(zhàn)爭敘事的文本空間是比較廣闊的,如嚴歌苓的《金陵十三釵》《第九個寡婦》,張翎的《勞燕》、虹影的《上海之死》等作品涉及到抗日戰(zhàn)爭、解放戰(zhàn)爭的敘事,有的作品把筆觸延伸至“二戰(zhàn)”的大背景之中。文本空間的廣闊和敘述視野的延伸使得作家的戰(zhàn)爭敘事有歷史整體意識,而且對戰(zhàn)爭的審視反思意識也更加強烈,從而拓寬了文本的歷史空間、政治空間和文化空間。陳河在書寫戰(zhàn)爭的過程中架構(gòu)了多維度的文本空間,有力地突破傳統(tǒng)戰(zhàn)爭敘事的格局和范式。從時間上看,陳河小說的戰(zhàn)爭敘事不僅涉及20世紀上半期的“一戰(zhàn)”“二戰(zhàn)”時期,還有20世紀下半期的冷戰(zhàn)、抗美援越戰(zhàn)等時期。長篇小說《甲骨時光》部分故事發(fā)生在“一戰(zhàn)”和抗日戰(zhàn)爭時期,描寫出戰(zhàn)爭背景下尋找甲骨的人的真實心態(tài),日本考古者在保護文物的幌子之下卻深藏著掠奪寶物的丑陋嘴臉,從文化的角度進行歷史的寓言化。《沙撈越戰(zhàn)事》的故事發(fā)生在“二戰(zhàn)”時期,講述了加拿大華裔青年士兵周天化被空投到沙撈越叢林的抗戰(zhàn)傳奇。《米羅山營地》書寫“二戰(zhàn)”中馬來亞戰(zhàn)場華人抗戰(zhàn)的歷史,《外蘇河之戰(zhàn)》描寫20世紀60年代抗美援越的歷史。短篇小說《怡保之夜》則講述了日軍占領(lǐng)馬來亞時期發(fā)生在怡保的大屠殺事件,另一部短篇小說《被綁架者說》則展現(xiàn)了20世紀90年代阿爾巴尼亞內(nèi)亂時的社會狀況,這“可能是當(dāng)代首部記錄海外戰(zhàn)亂中國政府保護僑民組織撤僑的紀實文學(xué)”①羅玉華.論陳河的戰(zhàn)爭小說[J].小說評論,2019(3):164.。從陳河小說戰(zhàn)爭敘事的地點,能夠看出其地理空間的架構(gòu)非常廣闊。從中國、加拿大、新加坡、英國、美國、日本到馬來西亞、越南等國家,從歐洲、北美洲再到亞洲,戰(zhàn)爭背景下不同地域的具體境遇都存在著差異性,而正是這樣的差異性在地理空間的互動中向整體性靠近,表現(xiàn)出人道主義的“人類命運共同體”意識。
《沙撈越戰(zhàn)事》《米羅山營地》描寫的是“二戰(zhàn)”期間的馬來亞戰(zhàn)場,也是華人域外抗戰(zhàn)的英雄歷史。《外蘇河之戰(zhàn)》作為中國當(dāng)代抗戰(zhàn)文學(xué)鮮少提及的中國軍人抗美援越戰(zhàn)爭歷史的一部作品,既有抗戰(zhàn)文學(xué)地理空間的開拓性,又有歷史關(guān)注視角的深入性和宏觀性。陳河作品中的戰(zhàn)爭敘事突破了以往的地理空間,延伸至東南亞戰(zhàn)場并進行了一場場與歷史的對話。尤其把華人群體在東南亞戰(zhàn)場的英勇無畏、機智聰慧、堅毅正直的崇高品質(zhì)展現(xiàn)得淋漓盡致,塑造出具有國家意識和世界意識的“英雄”。正如陳河自己在訪談中說道:“我沒有評判一場戰(zhàn)爭的能力,但我在書寫中,對于那些為國參戰(zhàn)的軍人或平民,都給予發(fā)自內(nèi)心的崇敬。”②魯大智.陳河:講好中國人的故事是我的責(zé)任和使命[N].中華讀書報,2018-12-12.戰(zhàn)爭敘事中地理空間的差異性并不影響創(chuàng)作者表達對無數(shù)英勇將士的崇高敬意,同樣給予深刻的人文關(guān)懷。由于地理空間放置在東南亞,所以相應(yīng)的自然空間也呈現(xiàn)出熱帶雨林氣候的特質(zhì),高溫多雨的天氣,茂密繁盛的原始叢林,復(fù)雜崎嶇的地勢,縱貫橫穿的河流,展現(xiàn)出當(dāng)代戰(zhàn)爭文學(xué)鮮少描繪的異域風(fēng)情。熱帶叢林的環(huán)境為戰(zhàn)爭書寫布下險惡艱難的自然之幕,也為情節(jié)發(fā)展和人物行動提供純?nèi)惶斐傻淖匀痪坝^,渲染出異域的奇特浪漫。
陳河在具體的戰(zhàn)爭敘事中,又表現(xiàn)出戰(zhàn)爭類型和戰(zhàn)爭主體的多樣性。《米羅山營地》有英國與日本、中國與日本、馬來亞游擊隊與日本的對戰(zhàn),還有馬共游擊隊和英殖民地的斗爭;《沙撈越戰(zhàn)事》有馬來亞本地土著、原始部落依班人、紅色游擊隊、英加部隊與日本軍隊的對戰(zhàn),也有紅色游擊隊的內(nèi)部肅殺;《外蘇河之戰(zhàn)》有身在越南的中國軍人與美國軍隊的對戰(zhàn),也有越南政府內(nèi)部政權(quán)的爭斗等。最吸引人的一點是戰(zhàn)爭主體的多樣性,也就是戰(zhàn)爭敘事過程中塑造的豐富人物群像,有土著人、華僑、商人、醫(yī)生、士兵、土匪、農(nóng)民等。他們的國籍、身份、職業(yè)、階級都不同,但是作為戰(zhàn)爭的裹脅者,他們都是普通存在的個體,在戰(zhàn)爭的混沌洪流中堅守屬于國家民族層次上的意義,去追尋個體生命層次的終極價值。陳河的小說本身就是一個多維度的空間,除了戰(zhàn)爭敘事,也展現(xiàn)出海外華人生存的掙扎與奮斗,如《紅白黑》《去斯可比之路》;海外留學(xué)群體的精心一瞥與用心書寫,如《女孩和三文魚》《我是一只小小鳥》;回望故國的批判反思,如《布偶》《夜巡》;還有個人生活經(jīng)驗的投射和反思,進而上升到作為群體性的審視與書寫,如《被綁架者說》《西尼羅癥》《猹》等作品。陳河的創(chuàng)作內(nèi)容豐富廣闊,戰(zhàn)爭敘事作為其文學(xué)作品的宏大敘事部分,也潛藏著多元的要素表達和精細的思想內(nèi)核。
二、書寫人物主體的生命意識
文學(xué)作品中的戰(zhàn)爭敘事往往表現(xiàn)出殘酷的殺戮、侵略的非正義、兇殘的人性、不幸的命運等悲劇性的體驗,同時也承載著關(guān)于國家、民族、革命等宏大的敘述主題,這是文學(xué)書寫戰(zhàn)爭和表現(xiàn)戰(zhàn)爭的常態(tài)。“思考戰(zhàn)爭也就是思考人,寫好戰(zhàn)爭也就是寫好戰(zhàn)爭與人、戰(zhàn)爭與人性的關(guān)系。”①黃修己.對“戰(zhàn)爭文學(xué)”的反思[J].河北學(xué)刊,2005(5):171.如何超越普遍的書寫模式,深入挖掘戰(zhàn)爭中顫抖靈動的人性,展現(xiàn)人作為主體的真實生存狀態(tài)和心靈境遇,從個體記憶、集體記憶、民族記憶上升到人類整體的記憶,去豐沛文學(xué)作品中戰(zhàn)爭敘事的思想意蘊,這是作家應(yīng)該思考和解決的問題。陳河為小說的戰(zhàn)爭敘事架構(gòu)多維度的空間,同時也融入自己作為作家的多元要素表達,如人性、人的存在、個體價值、民族認同、種族歧視、階級沖突、文化習(xí)俗、哲學(xué)宗教以及歷史遺留的問題等,突破傳統(tǒng)戰(zhàn)爭敘事的局限性,有力地體現(xiàn)宏大敘事和個體敘事的雙向交融。
在海外華文文學(xué)的戰(zhàn)爭敘事中,男女愛情的描寫既是文本的結(jié)構(gòu)策略,也是表現(xiàn)人性和命運的敘述話語。張翎的《勞燕》通過伊恩、比利、劉兆虎與姚歸燕“三男一女”的多角戀描寫,展示出戰(zhàn)爭背景下人性的裂變和人的命運的起伏不定。虹影的《綠袖子》和《上海魔術(shù)師》表現(xiàn)出人物帶有命運感的生存狀態(tài)和悲歡離合。陳河的系列戰(zhàn)爭作品也有愛情的書寫,有別于傳統(tǒng)文學(xué)中的“革命加戀愛”模式,人物的主體意識和生命自由意識鮮明強烈。《米羅山營地》中卡迪卡素夫婦的善良以及面對酷刑拷打的堅韌與他們忠貞不渝的愛情合為一體。《沙撈越戰(zhàn)事》中的藤原香子是周天化的精神支撐,依班姑娘猜蘭是他生命的拯救者。《外蘇河之戰(zhàn)》中趙淮海和庫小媛的生死愛情既有悲劇感又有壯麗感,一位將生命獻身于戰(zhàn)場,一位為堅守理想信念而開槍自殺。江雪霖在濟南火車站對丈夫甄聞達的等候既有人性的溫情又有戰(zhàn)爭帶來的苦澀感。戰(zhàn)爭的殘酷往往與人性的美好對照描寫,去展現(xiàn)生命微光的靈動。《米羅山營地》中的卡迪卡素夫人如圣母一樣,無私救助受傷的群眾和士兵,面對嚴刑拷打依然堅韌無比,這是陳河戰(zhàn)爭小說中崇高人物的代表。英國士兵查普曼雖然給叢林深處的人帶來災(zāi)難,但是華人老百姓與沙蓋人還是會幫助他,這種人性的善意超越種族和階級的差異,上升為強烈的心靈力量。
陳河在戰(zhàn)爭敘事的過程中所塑造的人物大多具有崇高的品質(zhì),從國家民族的角度來看具有崇尚正義、堅持真理的高度,從個體角度來看具有追求理想價值和生命自由的深度,達到宏大話語和個體追求的有力結(jié)合。陳河在《外蘇河之戰(zhàn)》中寫道:“如果說,攝影師朱復(fù)興到越南南方是在執(zhí)行一個國家的任務(wù),而我舅舅所執(zhí)行的則是他個人生命和理想的一次重要使命。”②陳 河.外蘇河之戰(zhàn)[M].北京:人民文學(xué)出版社,2018:120,139.趙淮海從北京長途跋涉到越南,在槍林雨彈中不畏生死,最后犧牲在戰(zhàn)場上,真正實現(xiàn)了自己的革命理想和生命價值。士兵袁邦奎為打撈越南老人的豬苗獻出年輕的生命,馬今朝療傷休養(yǎng)之后又義無反顧地歸隊……這些為理想而獻身的人物承載著國家民族、生命價值的意義,同時也表現(xiàn)出作者對生命的深刻思考。作品中,趙淮海在面對戰(zhàn)友的犧牲以及戰(zhàn)爭的困惑迷茫時,保爾這句關(guān)于人生的話“人最寶貴的東西是生命,生命對于每個人只有一次……”會浮現(xiàn)在他的腦海中,這是趙淮海作為個體的生命思考,也是包括作者在內(nèi)的全人類視角去探討生與死的永恒論題。陳河的戰(zhàn)爭小說有對生命的終極思考,也有關(guān)于個體存在與民族認同的探討。以《沙撈越戰(zhàn)事》的周天化為例,他作為加拿大華裔兵被空投到沙撈越叢林作戰(zhàn),他參加抗戰(zhàn)的過程就是一個民族身份認同的過程,“我要去哪里?我為什么要去?”③陳 河.外蘇河之戰(zhàn)[M].北京:人民文學(xué)出版社,2018:120,139.體現(xiàn)出以周天化為代表的少數(shù)族裔在身份認同和民族認同的含混性。陳河小說的整體性視野使他能夠表達出被其他民族認同的張力,如作品中寫到在加拿大生活的日本居民,面對加拿大公民權(quán)利和作為日本人對戰(zhàn)日本的選擇中,深刻體現(xiàn)出不同民族群體中出現(xiàn)的身份認同的含混性和尷尬性。
陳河小說的戰(zhàn)爭敘事還涉及種族歧視、階級沖突、文化習(xí)俗等問題的探討。《沙撈越戰(zhàn)事》中的二戰(zhàn)華裔老兵憶述華人受到嚴重歧視,沒有選舉權(quán),不能從事白領(lǐng)職業(yè);游擊隊的戰(zhàn)略與英軍戰(zhàn)術(shù)的沖突表面是戰(zhàn)爭策略的沖突,實質(zhì)是階級思想的沖突;依班部落奇異的風(fēng)俗習(xí)慣,獵取人頭、長屋樣式、“阿娃孫谷”庇護所、驅(qū)邪儀式、凈火節(jié)等帶有原始部落性質(zhì)的敘述為戰(zhàn)爭書寫增添了傳奇浪漫的色彩。《米羅山營地》中的林謀盛之所以走上諜戰(zhàn)之路是因為日本人對中國乃至對馬來亞的侵略,他的民族精神和無畏勇氣超越現(xiàn)時的階級沖突而成為正義的昭示;馬共游擊隊與英殖民地以及當(dāng)局政府的斗爭沖突,既是民族主義的沖突,又是階級立場和政治理念的沖突。《外蘇河之戰(zhàn)》中關(guān)于階級身份的沖突具有鮮明的現(xiàn)實性和深刻性,庫小媛不斷進取努力是為了改變自己資本家出身的身份。政工組長甄聞達對她說:“你的家庭原來是資本家出身,毫無疑問,這是階級的烙印。”①陳 河.外蘇河之戰(zhàn)[M].北京:人民文學(xué)出版社,2018:149,222,251,69,259、139.由于妻子的資產(chǎn)階級家庭出身影響了他的政治前途,他對庫小媛產(chǎn)生了畸形的報復(fù)心理,召開了斗私批修抓典型現(xiàn)場會。囿于階級意識和革命理想的束縛,庫小媛在絕望的心境中結(jié)束了自己的生命。
三、對話歷史與直面戰(zhàn)爭創(chuàng)傷
陳河作為文本的敘述者,他通過搜集文獻資料、實地考察訪問等方式來展開對戰(zhàn)爭的全景書寫,這種駕馭大量歷史材料的能力以及深入歷史場域的實踐為他的小說增加了敘述的可靠性與歷史的厚度。陳河在敘述過程中是一種“親歷者”的身份,“親歷者”既是文本話語的建構(gòu)者,又是歷史語境的向?qū)В瑫r也是喚醒人們關(guān)注邊緣記憶的召喚者,更是拒絕和抵抗遺忘歷史的警醒者,最終是精神意義上的體悟者和啟迪者。“如果講故事者本人就在故事里,作者便被戲劇化了;他的陳述便贏得了分量,因為那些陳述由于畫面場景中有敘述者在場而得到支持。”②[英]盧伯克.小說美學(xué)經(jīng)典三種[M].方土人,羅婉華,譯.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90:180.陳河作為文本親歷者的身份具有多重的文本意義,元敘事策略的使用是文本親歷者的一種體現(xiàn),“我”的在場不僅方便靈活運用各種文獻史籍、書信日記等材料,也能夠跳出來直接和讀者對話交流,帶領(lǐng)讀者一起追尋歷史、見證歷史和書寫歷史,從而在具體的戰(zhàn)爭敘事中設(shè)置一個與歷史和戰(zhàn)爭直接對話的場景,這就是文本的臨境感。
在《西尼羅癥》《怡保之夜》《猹》《沉浮》《被綁架者說》等作品中,陳河都采用第一人稱的敘述視角。第一人稱視角具有敘述的自如性和靈動性,以一種“可靠的敘述”去表現(xiàn)自己的生活體驗和人生思考。陳河小說中“我”的個體境遇和心路歷程由于書寫空間的異域性和廣闊性,往往具有以一觀類的作用,通過個體經(jīng)驗的書寫上升到關(guān)注人類共同體命運的高度。《沙撈越戰(zhàn)事》《外蘇河之戰(zhàn)》以及《怡保之夜》中,元敘事中的“我”承擔(dān)著文本敘述者、實地訪問者、創(chuàng)作者的多重身份,“我”的介入性敘事增添了鮮活的生命體驗和現(xiàn)實感。“以敘述者身份進入讀者視野的陳河就被貼上了思想者的標簽:冷靜而深刻,有著對生活的獨特經(jīng)歷與思考。”③默 崎.文化的傳承與歷史的想象——論陳河的長篇小說《甲骨時光》[J].華文文學(xué),2018(1):97.同時,在“我”之內(nèi)還有陳河作為創(chuàng)作主體的自我言說、自我思考。《外蘇河之戰(zhàn)》中的“我”替母親尋找舅舅在越南的陵墓為引,展開中國軍人抗美援越戰(zhàn)的敘述。“在我前往越南之前,我已經(jīng)接觸到了很多口述的故事,我被不斷發(fā)現(xiàn)的人物和細節(jié)所吸引,開始主動介入。”④陳 河.外蘇河之戰(zhàn)[M].北京:人民文學(xué)出版社,2018:149,222,251,69,259、139.“寫到這里,作為寫作者的我忍不住跳出來說說這件事。”⑤陳 河.外蘇河之戰(zhàn)[M].北京:人民文學(xué)出版社,2018:149,222,251,69,259、139.“但是我不希望甄聞達的遺孀江雪霖看到這一段文字。為了做到這一點,我已經(jīng)把甄聞達、江雪霖的名字和他們生活的城市名字都進行了虛構(gòu)。”⑥陳 河.外蘇河之戰(zhàn)[M].北京:人民文學(xué)出版社,2018:149,222,251,69,259、139.《米羅山營地》作為非虛構(gòu)故事,陳河查找相關(guān)檔案文獻、博客網(wǎng)頁、書信日記,同時還實地訪問馬來西亞,一些事件和人物都是真實存在的,尤其是他多次跳出來對話,如“在這本書里我盡量避免學(xué)術(shù)式的討論,但適當(dāng)?shù)貛ёx者研究一下歷史檔案還是必要的”⑦陳 河.米羅山營地[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13:75,249.“事實上,在寫作這本書的過程中我的睡眠質(zhì)量大大下降,而且脾氣變得非常暴躁。”⑧陳 河.米羅山營地[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13:75,249.,為非虛構(gòu)文本增添了更多真實性和可讀性。“當(dāng)‘非虛構(gòu)寫作’不斷重返歷史記憶時,不僅僅是為了揭示歷史真相,更重要的是,它還試圖通過揭示真相被遮蔽的過程,展示這種重返歷史現(xiàn)場的艱難與必要。”⑨洪治綱.論非虛構(gòu)寫作[J].文學(xué)評論,2016(3):66.《沙撈越戰(zhàn)事》中“讀者對于這個小說里突然插入這樣一個題外的故事和人物可能會覺得不適。然而必要的閱讀耐心還是需要的。”①陳 河.沙撈越戰(zhàn)事[M].北京:作家出版社,2010:240,154,5,249.陳河通過大量元敘事的筆法,交代創(chuàng)作緣由、創(chuàng)作過程、創(chuàng)作方式以及創(chuàng)作心態(tài),推進文本、作者、敘述者與讀者和世界的互動。《沙撈越戰(zhàn)事》以第三人稱的敘述視角進行全面客觀地敘事,全景式地展現(xiàn)“二戰(zhàn)”時期馬來亞戰(zhàn)場的狀況,尤其是沙撈越叢林的作戰(zhàn)場景。在這里,周天化其實是作為一個“他者”的眼光去審視“二戰(zhàn)”,以“他者”的身份來進行不確定的民族認同。作品中,陳河還設(shè)置了很多敘事圈套同時在戰(zhàn)爭敘事的過程中,人物的夢境、意象的隱喻、歷史寓言化、神幻色彩與原始叢林、風(fēng)云諜戰(zhàn)、異域風(fēng)情、奇特習(xí)俗、浪漫愛戀等結(jié)合,也為文本增加了神秘感和浪漫主義色彩。
陳河小說戰(zhàn)爭敘事最可貴的一點是能夠直面戰(zhàn)爭對當(dāng)事人的創(chuàng)傷,這種創(chuàng)傷既是身體上的又是精神性的,而且這種雙重創(chuàng)傷會延續(xù)在戰(zhàn)爭結(jié)束之后。“一種經(jīng)驗如果在一個很短暫的時期內(nèi),使心靈受一種最高度的刺激,以致不能用正常的方法謀求適應(yīng),從而使心靈的有效能力的分配受到永久的擾亂,我們便稱這種經(jīng)驗為創(chuàng)傷的。”②[奧]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引論[M].高覺敷,譯.北京:商務(wù)印書館,1986:216.戰(zhàn)爭雖然發(fā)生在彼時,但它給人們帶來的創(chuàng)傷性體驗超越時空,又成為現(xiàn)時的創(chuàng)傷,這樣的創(chuàng)傷描寫比描寫戰(zhàn)爭的生死搏斗、暴虐殘殺更加直擊人心,刺痛每一個經(jīng)歷戰(zhàn)爭和閱讀文本的人的內(nèi)心。在《米羅山營地》中,卡迪卡素夫人遭受日軍的酷刑拷打,木棒的重擊造成半身癱瘓,下頜骨斷裂之后形成敗血癥,最終去世,去世時沒有家人陪伴。卡迪卡素夫人肉體的苦難與精神的孤獨是戰(zhàn)爭帶來的雙重性創(chuàng)傷。英國軍人查普曼1971年開槍自殺,“原因是無法忍受的背痛、胃痛、頭痛,像噩夢一樣一直折磨著他,這些傷痛和疾病都是他在馬來亞叢林時期留下的。”③陳 河.米羅山營地[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13:249,248,205.戰(zhàn)爭帶給查普曼的嚴重的身體創(chuàng)傷,同時成為一種精神上的折磨,最終選擇自殺來擺脫痛苦。還有吳在新等被日本人抓捕的軍人,在之后的回憶資料里往往突出被捕前的經(jīng)歷,而對于被捕之后遭受的苦難一筆帶過,“這個現(xiàn)象的一種解釋就是日本人所采用的酷刑在他們的精神中留下了永久的創(chuàng)傷,以致他們不愿去面對記憶里那種極端的恐怖和厭惡。”④陳 河.米羅山營地[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13:249,248,205.當(dāng)代作家胡發(fā)云的《老海失蹤》中參加對越自衛(wèi)反擊戰(zhàn)的老海堅決不講那場戰(zhàn)爭,因為他十分厭惡那一場戰(zhàn)爭。老海的厭惡不僅僅是回憶慘烈戰(zhàn)爭的痛苦,還有對戰(zhàn)爭暴力的恐懼,這樣的恐懼作為一種精神性創(chuàng)傷乃至在多年之后也成為難以說出的夢魘。陳河在文本層面祛除戰(zhàn)爭表面的暴力慘烈,極力表現(xiàn)和挖掘那些被遮蔽了的生命被戰(zhàn)爭摧殘而導(dǎo)致的永恒創(chuàng)傷,被人們所遺忘的心靈深處的苦難。同時,陳河的戰(zhàn)爭敘事不是單向度的,而是雙向度或者多向度的,他能夠表現(xiàn)戰(zhàn)爭中不同主體的內(nèi)心世界,從而在整體史觀的書寫中注入人類共同體命運的意識。比如對《外蘇河之戰(zhàn)》中美國軍人史密斯的描寫,史密斯是反對和厭惡戰(zhàn)爭的,但是身邊的同學(xué)朋友都為國捐軀,同時戰(zhàn)爭的局勢又使他不安,最終他選擇了參軍。文中寫道:“史密斯對這場戰(zhàn)爭是否定的,但是對于自己參與了這場戰(zhàn)爭還是感自豪,沒有后悔。”⑤陳 河.外蘇河之戰(zhàn)[M].北京:人民文學(xué)出版社,2018:120,139,251,255.陳河對史密斯關(guān)于戰(zhàn)爭思考的書寫具有雙向度的體察,說明了在戰(zhàn)爭面前人的選擇的真實境遇,體現(xiàn)出他對于戰(zhàn)爭的多向度深入思考,隱含著難以訴說的共同的“戰(zhàn)爭創(chuàng)傷”意識,從而延伸了傳統(tǒng)意義上戰(zhàn)爭敘事的視野和格局。
四、結(jié)語
拒絕和抵抗遺忘歷史是陳河戰(zhàn)爭敘事的核心主題,也是最主要的價值訴求。那些被歷史遺忘的熱血英雄和英勇無畏的精神更應(yīng)該被后人崇敬,應(yīng)該被歷史記住,這是陳河在冷靜自然的書寫中蘊含的強大力量和召喚話語。《外蘇河之戰(zhàn)》中,“我”在越南遇見一位拉小提琴的女孩,問她是否知道當(dāng)年美國人轟炸越南北方時中國軍隊幫助越南軍隊抗擊美軍的轟炸。女孩說:“我不知道,沒有人對我們說這些事情。”①陳 河.外蘇河之戰(zhàn)[M].北京:人民文學(xué)出版社,2018:120,251.作品中寫道“如今這里的人們記住的就是袁邦奎一個人,那些打飛機的英雄驚天動地的事跡卻已經(jīng)忘懷了。”②陳 河.外蘇河之戰(zhàn)[M].北京:人民文學(xué)出版社,2018:120,251.那段驚心動魄、震撼天地的歷史早已經(jīng)被后人遺忘,這是歷史之傷、現(xiàn)實之悲。陳河在歷史與現(xiàn)時的對話之中感到一種沉寂的失落感,他希望能夠用文字重新喚醒歷史縫隙中的力量,重新展現(xiàn)沉重的戰(zhàn)爭背后那些被暴力詩意遮蔽的人性和被遺忘的光芒。《沙撈越戰(zhàn)事》的結(jié)尾是“如果要尋找他有沒有血脈留在叢林里,通過DNA技術(shù)完全可以做到。但是不會有人去做這件事的,因為周天化只是一個普通的華裔二戰(zhàn)士兵。”③陳 河.沙撈越戰(zhàn)事[M].北京:作家出版社,2010:240.周天化冒死去游擊隊發(fā)電報,英空軍保住了海上的實力,從而影響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的格局,但最終被神鷹當(dāng)作特務(wù)殺死,他扭轉(zhuǎn)戰(zhàn)局的力量和英勇無畏的品質(zhì)再一次被“掩蓋”。而陳河的戰(zhàn)爭敘事就是為了讓被掩蓋和被遺忘的歷史重現(xiàn)當(dāng)下視野,賦予偉大的“史”的性質(zhì),同時充分挖掘歷史表層之下的“人”的世界、“人”的心靈、“人”的力量。陳河抵抗遺忘歷史的方式是塑造出那些超越種族和階級而為戰(zhàn)爭奉獻青春、犧牲生命的普通軍人,同時深刻描繪出戰(zhàn)爭帶來的創(chuàng)傷性體驗,展現(xiàn)戰(zhàn)爭背后那些閃爍光亮的人性和品質(zhì)。作品中也提及溫哥華軍事歷史博物館、中途島航母博物館、林謀盛和平紀念碑、國會山紀念碑廣場、越戰(zhàn)紀念碑、袁邦奎紀念亭、烈士陵園、紀念公墓等建筑物,還有紀念儀式、戰(zhàn)爭紀錄片、傳記書信等具有隱喻意義的歷史象征物,這些作為空間隱喻與時間隱喻的事物都發(fā)揮著文化記憶和歷史記憶的功能。在側(cè)面書寫的過程中,具有歷史記憶功能的隱喻事物與抵抗遺忘歷史的核心主題形成強有力的呼應(yīng)。
“我是站在普世的人文價值角度去考量筆下的每一個人物,所以每一個參戰(zhàn)的士兵都值得我們?nèi)プ鹁矗麄兊睦硐搿⑺麄兊臓奚紤?yīng)該得到后輩人的尊崇。”陳河用自己的文字向這些為國家為理想獻出青春以及生命的將士致敬,這是他對英勇力量和崇高氣概的致敬,也是在向一段段即將遠去甚至?xí)贿z忘的歷史致敬。陳河在作品中通過戰(zhàn)爭敘事來呼喚歷史深處的偉大心靈價值,銘記和敬畏歷史,致敬一代代熱血將士的英魂,召喚正義的力量,有力開拓了當(dāng)代文學(xué)戰(zhàn)爭敘事的新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