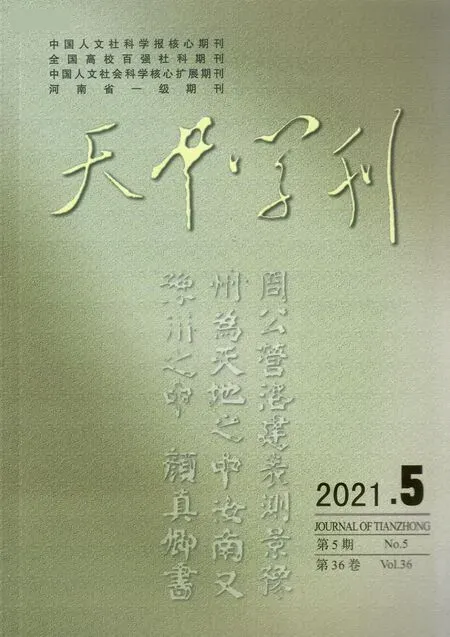近代嶺南報(bào)刊中的粵港澳地區(qū)形象
龍其林
(上海交通大學(xué) 人文學(xué)院,上海 200240)
1815年創(chuàng)辦的《察世俗每月統(tǒng)記傳》是世界上第一份以中國(guó)人為對(duì)象的中文近代報(bào)刊,此后《蜜蜂華報(bào)》《廣州記錄報(bào)》《依涇雜說(shuō)》《中國(guó)叢報(bào)》《東西洋考每月統(tǒng)記傳》等報(bào)刊陸續(xù)創(chuàng)刊、發(fā)行,嶺南地區(qū)創(chuàng)辦報(bào)刊至今已有兩百余年的歷史。這些中英文報(bào)刊中記錄了許多粵港澳地區(qū)早期城市的材料,它們生動(dòng)描繪了早期粵港澳地區(qū)在中西文化碰撞與交融中逐步發(fā)展的情況,為研究者走進(jìn)兩百年前的粵港澳城市生活、生活面貌保留了珍貴資料。
一、早期粵港澳地區(qū)的交通運(yùn)輸與近代醫(yī)療事業(yè)
由于相同的文化、語(yǔ)言、習(xí)俗,粵港澳地區(qū)在經(jīng)濟(jì)貿(mào)易、社會(huì)關(guān)系等方面保持了密切聯(lián)系,人員交往頻繁,這為輪船公司的營(yíng)業(yè)提供了客源保證。19世紀(jì)60年代,廣州、香港、澳門等城市之間已經(jīng)有了常規(guī)的往來(lái)火船,幾個(gè)城市之間人員往來(lái)極為頻繁。同治六年的《中外新聞七日錄》曾報(bào)道1867年正月到六月份之間穗、港、澳三地之間的旅客往來(lái)情況:“火船由羊城往香港自正月至六月,所搭之唐客有七萬(wàn)六千零三人,由香港來(lái)羊城自正月至六月所搭之唐客有六萬(wàn)五千八百七十九人,火船由澳門往香港自正月至六月所搭之唐客有二萬(wàn)三千八百五十人,由香港來(lái)澳門自正月至六月所搭之唐客,有二萬(wàn)一千七百四十二人,公司除費(fèi)用外,實(shí)得銀六萬(wàn)七千三百七十二大圓。”[1]
早期的粵港澳地區(qū)不僅在灣區(qū)內(nèi)部有方便民眾往來(lái)貿(mào)易或探親的常規(guī)往返輪船,還與海外保持了密切聯(lián)系,民眾前往美洲、東南亞謀生也成為當(dāng)時(shí)的一大潮流。1854年,創(chuàng)刊于香港的《遐邇貫珍》就報(bào)道了當(dāng)時(shí)菲律賓的首都馬尼拉(即小呂宋)設(shè)立火輪郵船的消息:“小呂宋總憲現(xiàn)設(shè)立火輪郵船,自彼處到港,往來(lái)絡(luò)繹,每月一次,兩地商民深資其便利。”[2]到了19世紀(jì)60年代,早期粵港澳地區(qū)與海外的交往更加頻繁。據(jù)《中外新聞七日錄》報(bào)道:“近日金山火輪船每月來(lái)往香港,中外國(guó)之客人甚為便捷,查其往來(lái)之客人中國(guó)每多于外國(guó)數(shù)倍。茲聞該火輪船十一月初九日在金山啟行,十二月初九日到日本國(guó),十九日至香港,二十二日又回金山。計(jì)其所搭中國(guó)之客人共一千二百名,所搭之番人止五十五名,共載貨九百頓,銀一百三十五萬(wàn)兩,各客自帶之銀不入內(nèi)。此行一路風(fēng)狂浪巨非常,所幸客人各得平安耳。嘉先生現(xiàn)已回仁濟(jì)醫(yī)局矣。”[3]
1830年,美國(guó)公理會(huì)派遣傳教士裨治文來(lái)到廣州。1834年,美國(guó)公理會(huì)又派傳教醫(yī)師伯駕到廣州,他憑借當(dāng)時(shí)廣州巨富伍秉鑒捐獻(xiàn)的10萬(wàn)兩白銀,于1835年11月在廣州新豆欄開(kāi)辦了眼科醫(yī)局,這是廣州第一所西醫(yī)醫(yī)院。眼科醫(yī)局醫(yī)術(shù)先進(jìn),且免費(fèi)為窮人治病,于是求醫(yī)者日漸增多。看到借助醫(yī)院傳教效果良好,此后傳教士們陸續(xù)創(chuàng)辦了不同的醫(yī)院。到“中華民國(guó)”成立前,廣州一共創(chuàng)建了19所醫(yī)院,其中包括8所教會(huì)醫(yī)院、5所慈善醫(yī)院、2所教學(xué)醫(yī)院、1所軍醫(yī)院、1所公立醫(yī)院、2所私人醫(yī)院。1835年,創(chuàng)辦于廣州的傳教士報(bào)紙《東西洋考每月統(tǒng)紀(jì)傳》發(fā)表了一篇報(bào)道,用熱情洋溢的筆調(diào)描述醫(yī)院開(kāi)設(shè)給民眾帶來(lái)的恩惠及醫(yī)院內(nèi)的醫(yī)療場(chǎng)景,為人們勾勒出廣州近代醫(yī)院的受歡迎程度:“寬仁孚眾,是耶穌門生本所當(dāng)為。今有此教之門徒,普濟(jì)施恩開(kāi)醫(yī)院,廣行陰騭盡情,真可謂懷赒急之仁。每日接雜病人及各項(xiàng)癥效,且賴耶穌之寵祐,醫(yī)病效驗(yàn)焉。有盲者來(lái),多人復(fù)見(jiàn),連染痼疾,得醫(yī)矣。四方之人常院內(nèi)擠擁,好不鬧熱。醫(yī)生溫和慈心,不忍人坐視顛危而不持不扶也。貴賤、男女、老幼,諸品會(huì)聚得痊。”[4]到了19世紀(jì)60年代,廣州城市人口逐漸增加,一些傳染性疾病也在威脅著市民們的生命安全。水痘就是其中一種,它是由水痘-帶狀皰疹病毒初次感染引起的急性傳染病,主要易感人群是嬰幼兒和學(xué)齡前兒童。在1866年的廣州,醫(yī)院已經(jīng)在報(bào)紙上廣而告之,希望民眾廣泛接種痘漿,防患于未然。據(jù)《中外新聞七日錄》報(bào)道:“夫種痘一欸,有益于嬰兒者大矣,愿為者早將小孩布種,以免天行之患。現(xiàn)今博濟(jì)醫(yī)院揀選精壯痘漿布種,七日期滿,必然漿水滿足。至灌足時(shí),每欲取回嬰兒之痘漿為種,以傳于別兒。而為父母者往往不喜歡,不知回漿一道必不損嬰兒,誠(chéng)以回漿之痘,翌日定然復(fù)灌。為父母者,既知其無(wú)患,何樂(lè)而不為哉?”[5]
二、早期粵港澳地區(qū)的規(guī)劃與文明期待
早期粵港澳地區(qū)處于由傳統(tǒng)社會(huì)向近代社會(huì)轉(zhuǎn)型的過(guò)程中,一方面民眾依然過(guò)著男耕女織的生活方式,生活節(jié)奏緩慢;另一方面人們?cè)谂c西方器物、文明的接觸過(guò)程中逐漸打開(kāi)了眼界,對(duì)于近代的西洋發(fā)明充滿了興趣。1865年,香港已經(jīng)開(kāi)始使用氣體路燈,以取代傳統(tǒng)油燈作為夜間城市道路指引,從而掀開(kāi)了早期粵港澳地區(qū)“不夜之城”的序幕。《中外新聞七日錄》曾有過(guò)報(bào)道:“香港于去歲間,有英國(guó)人造行制氣,發(fā)賣華外各班人等,多燒之以代燈油。今聞初創(chuàng)之時(shí),所制之器費(fèi)用甚多,其價(jià)比油更高,恐貧家難以猝買,但多歷歲月,料想其價(jià)必漸減……凡城中道路,皆引筒點(diǎn)氣,以代燈火,輝煌如晝,幾疑不夜之城。在彼貴家行店,莫不接筒買氣用照房、廊。正是日暮不須傳蠟燭,輕煙散入五侯家矣。若在羊城風(fēng)外,亦制此器,豈不大便于各處乎?”[6]
在第一次鴉片戰(zhàn)爭(zhēng)之后,香港被割讓給英國(guó),港英政府順即在香港推行中英文兼顧的書(shū)院教育,以便民眾在接受西式教育的同時(shí)增強(qiáng)對(duì)近代文明的認(rèn)同。到了19世紀(jì)50年代中期,這些近代書(shū)院招收的中國(guó)學(xué)生人數(shù)已頗為可觀,他們成為早期粵港澳地區(qū)進(jìn)行雙語(yǔ)交流與文化溝通的人才。《遐邇貫珍》曾經(jīng)報(bào)道:“本港英華書(shū)院設(shè)立十有余年矣,所收生徒,數(shù)近一百。有唐人先生教以五經(jīng)四書(shū),有英國(guó)先生教以上帝圣經(jīng)、兼及英話,與夫天文地理算數(shù)等學(xué)。向來(lái)生徒不須修金,即米飯亦是本書(shū)院所出。唐人子弟,獲其益者,誠(chéng)多且大也。頻年每月豐裕之家,欲送其子侄入院習(xí)學(xué),情愿補(bǔ)回米飯者,可想見(jiàn)書(shū)院之設(shè),其有裨于唐人之后生小子者,確有實(shí)征。”[7]
早期粵港澳地區(qū)得益于西方近代科學(xué)技術(shù)的引入,較早接觸及享受近代文明的福澤。如果說(shuō)氣燈改變了城市的夜間生活面貌,使之逐步與現(xiàn)代城市有了更多相通之處,那么火車的規(guī)劃則更體現(xiàn)了粵港澳地區(qū)對(duì)近代化的渴望。近代廣州最早興建的三條鐵路分別是粵漢鐵路、廣三鐵路、廣九鐵路,其中粵漢鐵路于1898年動(dòng)工,1936年全線通車;廣三鐵路1901年動(dòng)工,1904年全線建成,是廣州最早建成的一條鐵路;廣九鐵路1907年動(dòng)工,1911年全線通車。但實(shí)際上,早在19世紀(jì)60年代,廣州即開(kāi)始了對(duì)近代鐵路的規(guī)劃和期待。《中外新聞七日錄》報(bào)道:“聞?dòng)?guó)現(xiàn)新設(shè)火車會(huì),預(yù)合會(huì)本銀兩,擬欲在羊城起至佛山,開(kāi)設(shè)火輪車路,以便商旅行人。不久有英人到港,與中國(guó)官酌議舉行。前西國(guó)設(shè)火船、火車時(shí),恐有礙于水陸工人。及既設(shè)后,工夫生意愈多,轉(zhuǎn)覺(jué)火船火車之往來(lái)甚有益也。”[8]
早期嶺南報(bào)刊不僅關(guān)注粵港澳地區(qū)城市內(nèi)部之間的火車交通,而且還關(guān)注廣州至漢口的鐵路規(guī)劃。在報(bào)道中,編寫(xiě)者通報(bào)了洋人準(zhǔn)備建造廣州通往漢口的火車信息,并繪聲繪色地描繪了使用火車交通出行的便利之處,甚至還想象了一下不同區(qū)間的收費(fèi)標(biāo)準(zhǔn):“邇來(lái)西人欲在羊城造一火輪車路,先通至禪山,繼由禪直通至漢口。現(xiàn)已預(yù)備銀兩,專候稟準(zhǔn)大憲,然后與工。此誠(chéng)利便商客行人之事。考火輪車之為用,快逾奔馬,捷勝飛禽,每一點(diǎn)鐘可行一百二十里,其務(wù)求平穩(wěn),不尚疾馳者,亦常行八九十里。若由省抵禪,不過(guò)四個(gè)番字之久,便可到埠矣。車內(nèi)上客位,窗明幾凈,鋪設(shè)整齊,坐臥行走,皆綽有余地。其由省至禪者,每位約收銀七分,次客位宛似火輪船之大艙,亦可坐立,但人數(shù)眾多,頗形狹隘,其由省至禪者,約收銀五分。將來(lái)此路告成,不特省垣百貨流通,即四鄉(xiāng)土產(chǎn),亦必流暢。蓋百物往來(lái),且彼埠所無(wú)者,即來(lái)此埠運(yùn)去。此埠所缺者,即往彼埠販來(lái)。以有易無(wú),交相貿(mào)易,日行千里,絕不廢時(shí),將見(jiàn)趙壁梁珠,悉羅市肆,南金東箭,盡萃民塵,羊城生意興隆,可拭目而待矣。”[9]
隨著早期粵港澳地區(qū)主要城市的發(fā)展,從鄉(xiāng)村進(jìn)入城市的民眾越來(lái)越多,城市管理面臨的壓力逐漸增大。在近代城市管理中,防范火災(zāi)是一個(gè)重要的內(nèi)容。粵港澳地區(qū)的地方官員缺乏近代科技輔助,只能按照傳統(tǒng)方法盡可能地儲(chǔ)水備用,以防萬(wàn)一。《中外新聞七日錄》這樣描寫(xiě)廣州城中的官員防范火災(zāi)的辦法:“近聞蔣撫軍因天旱井涸,無(wú)水可取,各處火燭頻仍,乃出示勸各商民,街設(shè)大木桶二十個(gè),每個(gè)蓄水二十擔(dān),以防回祿,誠(chéng)仁人君子之用心矣。但又既延燒,待車來(lái)救,鋪戶焚已多。”報(bào)道者給出的建議是:“能家家置銅水槍一枝,火仨起時(shí),號(hào)炮一響,近地銅水槍云集,刻即扯水射熄,不至延燒,更有裨益,蓋捷莫捷于此矣。”[10]之所以會(huì)有如此建議,乃傳教士根據(jù)本國(guó)救火方法提出的期待:“我西國(guó)救火之法與中國(guó)不同。國(guó)中人設(shè)有保險(xiǎn)公會(huì),如某鋪出銀若干與會(huì)中,一遇火燒即補(bǔ)回銀若干。前時(shí)救火并無(wú)專司,今則特設(shè)人員司理火燭之事,其人皆選少年氣血強(qiáng)壯者。倘遇某處遭火,用電氣線報(bào)知各處,各處一聞即以車馬火速馳往,立將各馬牽開(kāi),以水倒瀉車中之水柜,用火機(jī)器趕水上牛喉四射火焰起處。此法更捷于用人力,使中國(guó)人依樣為之,則救火又得一捷法矣。”[10]
三、早期粵港澳地區(qū)的海盜問(wèn)題及中外圍剿
在近代嶺南報(bào)刊中,保留了大量關(guān)于早期粵港澳地區(qū)海盜的報(bào)道,他們橫行南海,以殺人越貨、綁票勒贖為營(yíng)生,有時(shí)還直接對(duì)抗官兵,殘殺外國(guó)商旅,使得這一灣區(qū)的商貿(mào)往來(lái)、文化交流面臨著不小的困難。早期粵港澳地區(qū)因?yàn)榭拷虾#鞣缴檀Q(mào)易大多經(jīng)過(guò)南海而進(jìn)入中國(guó)內(nèi)地,政府實(shí)際管控能力的薄弱,導(dǎo)致第一次鴉片戰(zhàn)爭(zhēng)后海盜橫行。《遐邇貫珍》有許多關(guān)于早期粵港澳地區(qū)海盜的記載,其中以粵東地區(qū)的海盜尤為猖獗。粵東即廣東省東部,主要包括潮州、汕頭、汕尾、揭陽(yáng)等城市。值得注意的是,粵東是現(xiàn)代中國(guó)著名的僑鄉(xiāng),有3000多萬(wàn)潮汕人分布在世界100多個(gè)國(guó)家和地區(qū)。但在19世紀(jì)50年代,粵東顯然不是一個(gè)太平的地方。在《遐邇貫珍》的報(bào)道中,粵東海盜的猖獗已經(jīng)到了影響社會(huì)穩(wěn)定的程度:“粵東洋面近有海盜無(wú)數(shù),每有良民連貨出口輒被劫掠,財(cái)命兩喪,殊堪悼惜。”[11]當(dāng)時(shí)的報(bào)紙也曾探討過(guò)海盜群起的原因,認(rèn)為根本原因在于清朝地方政府的失察、無(wú)制:“近日海上盜賊蜂起,不可勝數(shù),此皆因官府無(wú)制,遂使群盜劫掠海岸。既已失察于前,復(fù)不剿捕于后,得毋謂外國(guó)與中國(guó)既通貿(mào)易,而遂委之外國(guó)代除殘暴也耶,誠(chéng)可怪也。夫中國(guó)須當(dāng)懷柔遠(yuǎn)人,今乃反其道,而求之遠(yuǎn)人,此似難解。”[12]由于晚清政府腐敗,管理能力低下,在應(yīng)對(duì)近代海盜問(wèn)題時(shí)常求助于外國(guó)力量,這在傳教士報(bào)刊看來(lái)是一大怪事。而更加令人驚悚的是,由于清朝地方政府的管轄不力,導(dǎo)致南海周邊地區(qū)遍布海盜,有些地方甚至聚集了大批海盜,連官府火船都難以圍剿:“十八日晨早,復(fù)至一村,近古蘭者,遙見(jiàn)其村甚為雄壯,知非四五百人不能取勝,而船只有七十人,與戰(zhàn)無(wú)益,遂返。古蘭近地之村,不能下者,惟此而已。”[12]
早期粵港澳地區(qū)的海盜為了劫掠財(cái)物,手段殘忍,連來(lái)此進(jìn)行貿(mào)易的外國(guó)商船也不放過(guò)。海盜們的作案方式五花八門,有的是直接駕船進(jìn)行強(qiáng)攻,有的則是通過(guò)潛伏偽裝的方式,或偽裝為乘客搭載,或作為水手潛伏船上,伺機(jī)起事。《遐邇貫珍》曾報(bào)道了一艘英國(guó)商船為中國(guó)水手劫掠一案,引發(fā)了官方緝拿兇手:“本月十二日,英國(guó)商船名亞勒頓亞卜駕,猝遇兇橫殘暴之慘。因此船是日出口,行至子刻,船內(nèi)中國(guó)水手十余人忽起,乘船主暨各英人熟寐,持刀將船主等六人砍斃,棄尸于海,將箱匣掀開(kāi),掠所有器物而逸。其本船之印度國(guó)水手等,恇怯畏懦,緣桅匿避。俟兇手等離船,始共駕船回港。惟船主一人垂斃臥船內(nèi),通體鱗傷,狼狽不堪。旁有一犬,其身亦負(fù)重傷。揣度其情,想系因兇手等欲將船主擲海,故此犬戀主爭(zhēng)嚙,致受巨創(chuàng)也。區(qū)區(qū)一畜,具此忠肝義膽,而兇暴之徒,儼然具體而號(hào)為人,乃殘暴兇忍,戕生命而傷天和,殊堪痛恨耳。曾有友人,為作《義犬記》,茲以限于篇幅,未及錄入。現(xiàn)已懸賞,購(gòu)弋正兇潘亞驗(yàn)一名,花紅銀五百圓,余黨每名花紅銀一百圓。”[13]
第一次鴉片戰(zhàn)爭(zhēng)及其隨后的太平天國(guó)運(yùn)動(dòng)、第二次鴉片戰(zhàn)爭(zhēng)、中法戰(zhàn)爭(zhēng)等系列戰(zhàn)爭(zhēng)的發(fā)生,使清政府為維護(hù)搖搖欲墜的統(tǒng)治費(fèi)盡心機(jī)。因而,清政府對(duì)各地的海盜出沒(méi)常常有心無(wú)力,難以進(jìn)行有效管控。早期粵港澳地區(qū)海盜盛行,嚴(yán)重影響地方經(jīng)濟(jì)貿(mào)易發(fā)展,給民眾生命財(cái)產(chǎn)安全帶來(lái)巨大威脅,也影響了英國(guó)政府、清朝地方政府的統(tǒng)治,因此他們也對(duì)海盜的猖獗行為進(jìn)行打擊,有時(shí)還會(huì)聯(lián)手行動(dòng),收到了一定的效果。1854年的《遐邇貫珍》曾有諸多報(bào)道,反映了當(dāng)時(shí)港英政府為解決海盜問(wèn)題進(jìn)行的武力緝捕:“近日香港附近洋面海盜竊發(fā),四處劫掠。有兩枝桅花旗師船出海緝捕,復(fù)有英師船一只出海巡緝。”[14]同時(shí),內(nèi)地政府與澳門政府也為剿滅海盜進(jìn)行了努力:“十一日,有中國(guó)師船在九洲洋面捕獲盜舟二只,駐澳門之西洋師船亦捕獲二只。尚有二盜舟,正在追捕之際,竄逃無(wú)蹤。”[14]
海盜問(wèn)題顯然難以在短時(shí)間內(nèi)得到解決,19世紀(jì)60年代中期仍有反映海盜問(wèn)題的諸多報(bào)道。比如,《中外新聞七日錄》就報(bào)道了由于海盜猖獗,廣州府憲與英國(guó)領(lǐng)事副官?zèng)Q定聯(lián)手圍剿:“近年南洋海賊為患大甚,茲聞廣州府憲與英國(guó)領(lǐng)事副官于十六日統(tǒng)帶華英兵船,出巡海濱賊聚之境,欲設(shè)法防海,以除行船之災(zāi)危,即所以利商賈之往來(lái)也,豈非除害安良之術(shù)哉?”[15]因?yàn)楹1I問(wèn)題困擾地方安寧,地方政府希望能夠盡快剿滅:“廣瀾寧海一帶洋面,素為逋逃淵數(shù),肆行劫掠,莫敢誰(shuí)何。前月十四日,糧道梅大人,會(huì)同英官帶領(lǐng)水師戰(zhàn)艦前往征剿。近聞拿獲盜船二十余只,擊斃匪人無(wú)數(shù),業(yè)已凱旋。現(xiàn)蔣撫又遣彭玉等,搗具巢穴,務(wù)其凈盡根株,無(wú)留萌蘗。”[16]
早期粵港澳地區(qū)對(duì)捕獲的海盜通常予以嚴(yán)厲懲治,吊決是當(dāng)時(shí)較為常見(jiàn)的方式。《遐邇貫珍》就曾報(bào)道:“上一月有外國(guó)船,由三佛蘭錫士歌(即金山)駛赴中土,將入內(nèi)洋。有一搭客花旗人,名巴近士心急,欲速至澳門,遂雇一三抓艇,攜行李放棹前往,后不知去向。旋查得該艇在九洲洋面正在棹行之時(shí),巴近士偃臥艙內(nèi),被該艇水手陳亞川夫妻與數(shù)人將其殺斃、棄尸,劫取衣裝財(cái)物。至五月二十日,跟尋訪緝,獲到兇身夫婦人等。在駐港臬司署審訊不諱,斷以吊決之罪;其妻有孕,且未確知是否逼令幫兇,議以減等,永遠(yuǎn)充軍。其男犯已行刑吊決。”[14]早期粵港澳地區(qū)之間在應(yīng)對(duì)海盜問(wèn)題時(shí),也時(shí)常進(jìn)行一起協(xié)商、緝捕,在審判、處理海盜時(shí)也多有合作。據(jù)報(bào)道:“聞得香港總督用根缽火船出洋拿獲海洋大盜犯十六名,于三月廿四日,解至羊城,交南海縣嚴(yán)審究辦,不日定然處決。”[17]
海盜犯案后大多會(huì)盡快逃遁,以求躲避官方緝捕,保全自身及財(cái)物,但有些海盜膽大包天,殺人越貨、劫掠財(cái)物后還假冒為正規(guī)商賈,試圖瞞天過(guò)海、公然銷贓。《中外新聞七日錄》曾報(bào)道:“五月初三日有番人貨舶,自香港開(kāi)行,向東而駛,突遇賊船數(shù)只,力不能敵,被其路過(guò)船中,將貨物盡行搬取,復(fù)將巾里攬器皿,毀壞而去。是時(shí)番舶在海中,因無(wú)器具,進(jìn)退兩難。幸遇火船拖回港中,即詣衙門控,但賊船已去,何從緝查。豈知此賊膽大如此,自投死地,竟將船駛至港中,詐稱船內(nèi)之貨,系在別處所買,今在港中銷售。當(dāng)番舶告官之后,已出賞格懸購(gòu),時(shí)有同業(yè)之人,知其來(lái)歷,欲得花紅重賞,隨即詣官稟白。遂于五月十四晚,密遣差役,同線人至燈籠洲覆研詰,內(nèi)有五名已由水手等認(rèn)識(shí)。故于禮拜二日定案,照海洋劫盜例,治以問(wèn)吊死罪。”[18]
早期粵港澳地區(qū)的海盜問(wèn)題常常引發(fā)列強(qiáng)與地方政府的矛盾沖突,因此地方政府也采取了主動(dòng)出擊、定期巡緝、嚴(yán)懲不貸等方式加以圍剿、威懾,希望能使海盜問(wèn)題得到控制。只是晚清政府由于治理近代社會(huì)問(wèn)題的能力較弱,始終未能有效地解決這一問(wèn)題。
四、早期粵港澳地區(qū)圍剿海盜報(bào)道的背后角力
早期粵港澳地區(qū)的各地方政府意識(shí)到了海盜問(wèn)題的嚴(yán)重及其危害,決定對(duì)海盜進(jìn)行打擊,在近代嶺南報(bào)刊中出現(xiàn)了描寫(xiě)官府甚至軍隊(duì)與海盜進(jìn)行對(duì)戰(zhàn)的報(bào)道。這些報(bào)道敘事曲折,描寫(xiě)繪聲繪色,充滿身臨其境之感。
1855年,在香港發(fā)生過(guò)一場(chǎng)官船與海盜之間的激烈戰(zhàn)斗:“四月十二日,于港中傳聞,有賊船數(shù)只,在山尾處劫去本港曾經(jīng)掛號(hào)貨船二只。火船聞之,即發(fā)火往追。于十三早到洪海灣,遠(yuǎn)見(jiàn)賊船一幫同聚。賊見(jiàn)火船追來(lái),群驚星散,或有竄往大州,或有竄往三州者,被火船開(kāi)三板數(shù)只追及,壞其賊船五只,殺死賊黨三十余名,生擒者四名。其被劫之二船兼及渡船、漁船各一只,俱被取回,于十四日一同回港矣。二十日,又聞?dòng)匈\船一幫,劫去羅查艇鴉片七十箱往上川灣泊。拉喇火船即時(shí)發(fā)火往追。及到上川而賊船早已移避,于是火船沿濱尋覓。尋至南帆,了無(wú)蹤跡。回港時(shí)路過(guò)萬(wàn)山,遙見(jiàn)有船二只,船人運(yùn)貨上岸。近之,見(jiàn)船上大炮,知是賊船。遂拖出大海,發(fā)火焚燒。喇拉火船之剿賊,其功如此。”[19]
值得注意的是,廣東地方政府與港英政府在圍剿海盜時(shí)曾經(jīng)合作,并取得了系列戰(zhàn)果,但近代嶺南報(bào)刊在報(bào)道二者的貢獻(xiàn)時(shí)顯然各有側(cè)重。《遐邇貫珍》在報(bào)道中著力塑造港英政府在應(yīng)對(duì)海盜問(wèn)題時(shí)的果敢及成績(jī),通過(guò)委婉曲折的事件展示,將港英政府火船拿回貨物、解救人質(zhì)、搗毀匪巢等細(xì)節(jié)進(jìn)行了細(xì)膩地展現(xiàn)。比如,《遐邇貫珍》上曾有一篇系列報(bào)道,先講述了海盜危害之烈,“英十月初五日,有知離國(guó)兩枝半桅船一只,名加地拉者,揚(yáng)帆往金山。開(kāi)行數(shù)日,不料為颶風(fēng)所擊,于是船主尋覓泊船處所,以避風(fēng)險(xiǎn)。遙見(jiàn)一市,市名古蘭,遂就而泊焉,斯時(shí)見(jiàn)有許多小舟同集。泊后,忽有大船無(wú)數(shù),齊來(lái)劫之,悉取其物,并執(zhí)船主”;之后講述船主的急中生智及港英政府的洞察力及行動(dòng)力,“船主哀求賊首帶彼至澳門,俾得銀以易其船。于是有賊匪二人,與之偕行。迨抵澳后,船主詭稱銀兩不便,復(fù)給他同到香港,為差役所獲。至十三晚,人將是事一察,盡得其情,因知有佛廊西一女,及唐搭客一人為賊所擒,即發(fā)火船馬利活娘娘帶齊刀槍兵器,往彼處尋覓二人,是夕船抵古蘭”;待港英政府火船達(dá)到海盜麇集之地后,立即展開(kāi)了激烈的戰(zhàn)斗,“剛遇賊船泊于大市側(cè),遂發(fā)炮相戰(zhàn)。賊戰(zhàn)不利,齊奔上岸,于是舟人直迫上岸,往市中尋覓,竟不獲二人蹤跡,但見(jiàn)有加地拉船破敗之物在彼,遂登舟而返。后復(fù)使火船名晏者往覓,帶水兵七十人同行。至十六晚,船到底流,離人村約七八里許,遂泊于此。次日晨早,遙見(jiàn)岸旁有大船一只及無(wú)數(shù)小船,貨物沉重,船人裝飾齊整。知是賊船,遂發(fā)大炮一口,向大船桅上打去,其船亦發(fā)炮相拒。賊人懼怯,漸退至岸而奔,于是上其船尋覓,幸得二人在彼,遂攜之登火船,盡焚賊船。是時(shí)又遙見(jiàn)大船二只,即使小舟追之,賊棄船奔走。登其船,見(jiàn)有無(wú)數(shù)生口火炮等物,遂取之,乃焚其船。厥后舟人登岸,往村中尋回加地拉船之貨,焚毀各處賊莊,計(jì)是日所焚毀者,不下一百屋宇。復(fù)見(jiàn)一村建于山頂,上村之路甚窄,僅二尺許,便欲上崗擒賊。賊見(jiàn)人上山,即將亂石打下,被傷者甚眾,然舟人奮不顧身,直抵賊巢。賊勢(shì)瓦解,遂盡獲其所有而返”[12]。在《遐邇貫珍》的系列海盜新聞報(bào)道中,港英政府樹(shù)立了保護(hù)地方安定、維護(hù)民眾利益的形象,這對(duì)于第一次鴉片戰(zhàn)爭(zhēng)后才取得香港統(tǒng)治權(quán)的港英政府而言具有重要的意義,圍剿海盜的新聞報(bào)道在某種意義上賦予了港英政府以統(tǒng)治香港的合法性、合理性。
與之形成鮮明對(duì)比的是,廣州的近代報(bào)刊則對(duì)中國(guó)地方官員為剿滅海盜進(jìn)行的努力有著更多的報(bào)道。廣州將軍兼兩廣總督瑞麟管轄廣東、廣西兩省軍民政務(wù),他雖因賣缺納賄而政聲不佳,但在打擊海盜一事上卻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19世紀(jì)60年代中期,瑞麟面對(duì)廣東洋面海盜猖獗的事實(shí),派出兵力圍剿海盜,甚至下屬官員還因此英勇?tīng)奚!吨型庑侣勂呷珍洝吩D(zhuǎn)載過(guò)瑞麟給朝廷的一封奏折,較為詳細(xì)地記載了圍剿海盜的經(jīng)過(guò)及為部下申請(qǐng)撫恤的內(nèi)容。其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關(guān)于與英國(guó)領(lǐng)事官一并出兵一事,瑞麟特別強(qiáng)調(diào)了是對(duì)方主動(dòng)申請(qǐng)清朝地方政府派員前往,而自己更是一向重視派遣水師武弁圍捕海盜:“廣東洋面盜船,出沒(méi)無(wú)常,英國(guó)派船前往緝捕,恐民船與賊船難以分別。奴才向派水師武弁,同往會(huì)拿,俾資辦認(rèn)。茲本年六月初間,據(jù)英國(guó)領(lǐng)事官羅伯遜申請(qǐng),英國(guó)現(xiàn)派火船赴西南洋面巡緝,請(qǐng)派員同往前來(lái)。奴才當(dāng)即派委署大鵬協(xié)都司梁國(guó)定偕往。迨是月十五日,據(jù)羅伯遜報(bào)稱,六月初七日火船駛至崖州屬之三匪洋面,瞥見(jiàn)海隅有大小盜船二十一只。英國(guó)火船立即開(kāi)炮轟擊,匪船亦回炮抵拒,兩時(shí)之久,擊斃淹斃盜匪甚多,將賊船全行燒毀,余賊紛紛鳧水逃走。梁國(guó)定奮不顧身,跳落小艇目前擒拿,被賊鳥(niǎo)槍中傷肚腹各處身亡等情。并據(jù)署瓊州鎮(zhèn)許穎升稟報(bào)前來(lái),奴才查梁國(guó)定素來(lái)緝捕,勤奮忠勇性成,前經(jīng)奏升吳川營(yíng)都司。奴才因大鵬協(xié)都司今因出洋捕盜,中傷亡身,實(shí)堪痛惜,合無(wú)仰懇天恩,敕部照陣亡例,從優(yōu)議恤,以慰忠魂。”[20]考慮到瑞麟的地方大員身份及清朝政府以自我為中心的天朝心態(tài),這樣的奏折更流露出耐人尋味的訊息。
通過(guò)近代嶺南報(bào)刊史料可以看出,今天的粵港澳地區(qū)早在近兩百年前就呈現(xiàn)出現(xiàn)代的雛形,那時(shí)的粵港澳地區(qū)不僅主要城市之間的交通較為便利,城市生活質(zhì)量有所提高,出現(xiàn)了醫(yī)院、書(shū)院、書(shū)局、報(bào)館等近代機(jī)構(gòu),而且與海外之間的經(jīng)濟(jì)貿(mào)易、人員往來(lái)也十分頻繁,對(duì)近代西方文明有了更直接而深入的了解。早期粵港澳地區(qū)最早受到近代西方文明影響,在區(qū)域經(jīng)濟(jì)發(fā)展、社會(huì)生活、文化觀念等方面接受了洗禮,推動(dòng)了中國(guó)社會(huì)由傳統(tǒng)走向近代,由守舊走向開(kāi)放。與此同時(shí),早期粵港澳地區(qū)的海盜問(wèn)題在進(jìn)入19世紀(jì)后逐漸變得嚴(yán)重,一直到民國(guó)時(shí)期都難以得到根治。究其原因,清朝的統(tǒng)治腐朽、官員貪腐、國(guó)防空虛、軍備廢弛都是重要的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