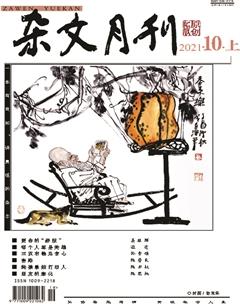文憑這東西
李偉明


文憑這東西,現在好像又特別受到重視了。干部提拔職務,職員晉升職稱,單位引進人才,文憑基本上都是個硬指標。有些地方甚至規定,第一學歷不是本科的,哪怕能力再強、工作業績再突出,職務也不能再上一層樓。至于企事業單位專業技術人員評職稱,文憑沒達標,不管你成果有多豐碩,也只能望洋興嘆。而另一部分人,則因為一紙文憑,仕途上處處綠燈,輕輕松松就到了別人無論如何努力也難以達到的高位,讓人唯有徒生羨慕。
時光倒流幾十年,我還是個中學生的時候,也知道要為文憑而奮斗。不過,那時文憑對我而言,并沒有太立體的感覺。作為一名農家子弟,我只知道考上中師、中專或大學,便能跳出農門,告別烈日下揮汗如雨的艱苦生活,端上一只旱澇保收的“鐵飯碗”,萬萬沒想到文憑與文憑之間還會有那么大的區別。在世俗的眼光里,考出去了,只要能分配一個好單位就行,管它是什么層次的文憑。所以,銀行學校、稅務學校之類的中專,比師范類的大專甚至本科還吃香。特別需要說明的是,那年代在農村,學習成績好而家庭條件一般的,幾乎都在初中畢業時便考中師或小中專去了,為的是早點參加工作領工資,為大家庭減負。我輩學習不如人家的,考不上中師或中專,只好抱著走一步算一步的心態去讀前途未卜(在那個年頭可以說基本上是“兇多吉少”)的高中,最后反而可能混了個“第一學歷是本科”的出身。
我一向以為自己造化欠佳,不受“命運”待見,常常感嘆:每當我找到成功鑰匙的時候,人家就把鎖給換了;每當幸福來敲門的時候,我又偏偏不在家。但現在回過頭來看,卻不禁倒吸一口涼氣,暗暗慶幸自己運氣其實不算太差。這事說來話長。當年高考雖遭遇重大失誤,但還是拿到了一所在當時很沒地位的師范學院的本科錄取通知書。那時家里特別窮,去學校報到前,聽說該校的專科是兩年制的,本科生可以自愿選擇調劑到專科班。為了省學費以及早點出來工作,便和家里商量了準備申請讀專科。沒想到,進了校門才知道,這一年,專科學制改了,由兩年調為三年。想想也就相差一年而已,便決定咬咬牙,干脆讀完四年算了,起碼名聲好聽些。現在就懂了,好在那年專科學制改為三年,不然我主動放棄本科讀專科,那后果可嚴重了。看到很多同齡人參加工作以后還在不斷進取,考這個學歷讀那個學位,便為自己能夠一勞永逸而深感僥幸。
當然,后來形勢不一樣了,高校大擴招,而且不包分配,考上大學不等于端上了鐵飯碗,要進“體制內”工作還得另外再考。這個時候,文憑也不像當年那么珍貴,一起讀中學的小伙伴們走出來,基本都不缺這玩意兒,雖然學校不同,層次有別。“金榜題名”的概念,似乎也被顛覆了,不可和當年同日而語。
正因為時代不同,文憑有變化,所以,對文憑這東西,最好不要一概而論。考量人家的文憑時,還得綜合考慮,看看他是多大年紀的人,手上持的是什么時代的文憑,在什么地方參加的考試。這些因素都會導致文憑到手的情況各有不同。只看那張紙而不管其客觀背景,對某些當事人來說豈非不公平?
更重要的是,歷來文憑與水平、學歷與能力未必完全掛鉤。文憑不是萬能的,學歷不能證明一切。學歷高的人如果入錯了行,能力就未必是他最強。
這樣說,不是有意貶低誰,它就是一個客觀事實。歷來都不乏學歷低甚至沒學歷而有超強能力的人。民國時期的梁漱溟,充其量是中學學歷,卻被蔡元培請到北大做教授;魯迅、沈從文、巴金這些文學大師的學歷也不高,華羅庚也只是個初中學歷,齊白石甚至什么文憑都沒有……你再看看身邊的“成功人士”,不管政界還是商界、學界,就會發現,一個人的成就與文憑,還真未必成正比。
對文憑簡單地“一刀切”,總是難免留下遺憾。在用人的問題上,什么時候能不貼標簽,多看實際能力就好了。想想當年那些優秀的同學因為種種原因未能取得本科第一學歷,我便不禁為他們在工作上吃虧而感到惋惜。現在早就不是“一考定終生”的年代了,還能搞“一紙定終生”嗎?實踐才是檢驗能力的最好標準,讓每一個有實力的人獲得相應的施展身手的平臺,世界才會充滿活力。所以,我以第一學歷“達標”者的身份呼吁,給文憑“不達標”者一個機會,讓他們以實際能力彌補客觀原因導致的缺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