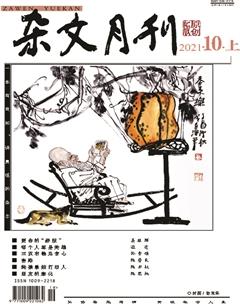人怕出名
楊聞宇


人生世為赤子,一無所有,最早沾身的姓名,是父母給的,改名換姓也常見;青睞少數人的名聲是后起的,則是社會所賜。
文化人一旦染指名聲,再要回頭而不予在乎,極難。原因正如顧炎武說的:“名之所在,則利歸之;茍不求利,亦何慕名?”求利之念先生,沽名之欲后起,名利連襟,是由實際利益粘合在一起的。
名聲分虛與實。培根認為:“名譽猶如一條河流,能載輕浮中空之物,也會淹沒沉重堅實之物。”凡是被歲月長河、被有見地者所推崇的名聲,必然沉重堅實,孔子說“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指的就是實在的名譽,它有點像涂于實物的高級油漆,既可以使物體鮮亮、華美,也能對物體起到相應的保護作用,讓那些瑣碎的細菌、浮蕩的灰塵,不能輕易沾染、隨便侵害。
至于由利益所鉤起的虛譽,則是另一回事。虛譽主要來源于諂諛者之口,它在本質上是一種騙術。諛者的目的只是為了從名人的身上分一杯羹,撈取些油水。正常人主觀上也是厭惡諛風的,面對諛詞而斷然拒絕,是最佳的免疫方式,問題是,文化人面對虛名浮譽(憑它也能撈取些實惠與虛榮,這倒不假),常常覺得順耳中聽而不由自主地中招,一旦中招,初始是弄不清天高地厚,亂了腳步,隨著吹捧升級,便自命不凡,自我神化,接著是膽大妄為,一步步地走上邪路。諂諛之徒臭味相投,拉幫結伙,他們纏裹住利令智昏的被諛者,不厭其煩地頌揚、高抬,實際上是在為被諛者開掘墳墓。對此,明眼人稱之為“捧殺”。捧殺的現象太常見了,不提也罷。
莊子在兩千年前就告誡過:“名,公器也,不可多取。”公器者,社會所矚目的重要目標,所以,對待它要慎之又慎。沽得虛名者,自欺欺人,最容易驟起驟落。孫犁見事透徹,將這等中招者稱之為“浪得名”之人:“自然,這種浪來之名,也容易浪去。”“浪”字在這里太巧妙了,契和著“一條河流”里漂蕩著的泡沫。
明末的張岱,見地更為深刻:“名根一點,堅固如佛家舍利,劫火猛烈,猶燒之不失也。”這個世界上,浪得虛名者終于是極少數,在這極少數里,名根確實是極端頑固,堅如舍利。堅如舍利怎么解釋呢?一是很難放下,對名聲的欲求是得寸進尺,愈演愈烈。二是不懂得轉化(物極必反)的規律。“人怕出名豬怕壯”,這可是一刀封喉的一句諺語。豬壯了,要挨刀的。名根在身者,暈頭轉向,會干出匪夷所思的勾當來,可也未必真的就挨宰,而冒天下之大不韙、違背常識、為社會所難容的大趨勢,卻是注定的了。
海明威早就表示過,他只和死去的作家比,因為活人的名聲“是批評家制造出來的”。杜甫的“千秋萬歲名,寂寞身后事”,字面上說的是李白,其實也在談自己的體會:經得起時光檢驗的名聲,才是名實相符的珍品,身后之名,才是歲月長河里沉淀下來的真家伙。
“人怕出名”,指的是虛名,針對的是沽名釣譽的活人。人一旦辭世,名聲之有無、大小,與本身也就無關了。名人辭世,即使其兒孫輩能隨同沾光,也是微乎其微,沾不上多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