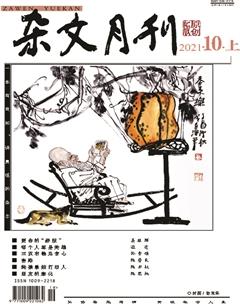治國如治病
王俊良


“治國之有法,猶治病之有方也”,是光緒十四年(1888),康有為《上清帝第一書》中,為清廷開的變法藥方。提“治國如治病”,并強調“病變則方亦變”。
“治國如治病”之說,為唐太宗首倡。《資治通鑒》載,一次,唐太宗與魏征探討治國之道,說“治國如治病,病雖愈,猶宜將護。儻遽自放縱,病復作,則不可救矣。今中國幸安,四夷俱服,誠自古所希,然朕日慎一日,唯懼不終,故欲數聞卿輩諫爭也”。
作為帝王,認識到“病雖愈,猶宜將護”這一層,已屬不易。關鍵是,做到不讓“病復發”。卿輩諫爭,作用于外;自身強化,作用于內。著眼于根治,著力于預防。對此,魏征見解深遠,說“內外治安,臣不以為喜,唯喜陛下居安思危也”。
醫分神庸,治存高下。治不了病,不添病,是境界;治不好國,不亂國,乃訴求。呂誨反對王安石改革,即此心態。其上疏之刻薄,無出其右,“安石初無遠略,惟務改作立異,罔上欺下,文言飾非,誤天下蒼生,必斯人也”。
《宋史》說,宋神宗不為呂誨之言所動。無奈之下,呂誨以身疾諭朝政,說:“臣本無宿疾,醫者用術乖方,妄投湯劑,率任情意,差之指下,禍延四支。一身之微,固無足恤,奈九族之托何!”
事實上,統治者對治國如治病的領悟,與《鹖冠子》中魏文王,對扁鵲三兄弟醫道的理解近似。扁鵲曾說:“長兄于病視神,未有形而除之,故名不出于家。中兄治病,其在毫毛,故名不出于閭。若扁鵲者,镵血脈,投毒藥,副肌膚,閑而名出聞于諸侯。”
醫道即治道。上醫醫未病之病,中醫醫欲病之病,下醫醫已病之病。信奉眼見為實的國人,更在意下醫醫已病之病,對上醫中醫醫未病欲病之病,只當是個傳說。
《韓非子》載,扁鵲見蔡桓公,可證治國如治病之理。扁鵲指出蔡桓公之病,肯定是已病之病。按方用藥,會很快痊愈。反之,養癰遺患,小病釀就大病,終致不治。統治者總是想當然地認為,除自己高明以外,別人都是群氓。諱疾忌醫是表,自己說了算是里。
蔡桓公的病,一次次失去本可治愈的機會。使病痛由腠理而肌膚,再由肌膚而腸胃,最后由腸胃而骨髓,終致不治。扁鵲的遭遇,猶比干之于紂王,張居正之于萬歷,找到了病因,也開出了藥方,卻未能藥到病除。正所謂,治得了病,治不了命。
此番情景,蓋韓愈《醫說》所謂:“善醫者,不視人之瘠肥,察其脈之病否而已矣;善計天下者,不視天下之安危,察其紀綱之理亂而已矣!”懂治國如治病之理,行治者應行治世之道。
“通于此說者,其知所以為天下乎?”其實未必。光緒六年(1880),時年45歲的慈禧病了。此時,朝廷因崇厚擅簽《中俄伊犁條約》,“清流”李鴻藻、張之洞等力主殺崇厚、廢《條約》。左宗棠主戰,李鴻章則云:“左帥主戰,倡率一班書生腐官,大言高論,不顧國家之安危。即其西路調度,不過爾爾,把握何在?”
張佩綸將廟堂之爭與和慈禧之病類比,此數人之治病,正如時賢之治國矣。對此,顧炎武堪得通透:“今之用藥者,大抵雜泛而均停,既見之不明,而又治之不勇,病所以不能愈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