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析日本襲警罪


日本襲警現狀梳理
(一)警察體系
日本《警察法》中對于“警察”是這樣定義的:以保護個人的權利和自由、預防犯罪、鎮壓及搜查、逮捕犯罪嫌疑人、管理交通等維護其他公共安全和秩序為義務。同時,要求所有職員宣誓,捍衛日本憲法及法律,公正執行職務。日本警察廳下設長官官房及生活安全局、刑事局、交通局、警備局、情報通信局,同時為分管地區事務,設六個管區警察局作為地方機關,即東北管區警察局、關東管區警察局、中部管區警察局、近畿管區警察局、中國四國管區警察局、九州管區警察局,各管區警察局下設警察支局。
都道府縣基于本區域內的第二條相關義務設立都道府縣警察。東京都設警視廳,道府縣設警察本部為各地警察總部,全國共計51處,其下設警察署,全國共計1153處,下設派出所,全國共計12505處。都道府縣警察機構除《警察法》中第三十七項規定的警視正以上官員工資及其他補助、地方公務員互助組織承擔及公務災害補償的必要經費,維持警察通信設備的管理及其他警察通信的必要經費,與國家治安相關有關的犯罪及其他特殊犯罪搜查所需經費等13項為國庫支付外,其余經費由都道府縣自行支付。2021年,日本警察廳預算為3195億6800萬日元,都道府縣警察預算共計3兆3960億3458萬日元,職業警察編制總數為29萬6203人,其中警察廳編制8031人,都道府縣警察編制28萬8172人。
(二)襲警現狀
日本警察廳公布的2020年版《犯罪被害者白皮書》中,關于犯罪被害者實施政策基礎資料中第7部分顯示,妨害執行公務罪分別為2691件、2472件、2416件、2375件、2303件。
以上數據中,妨害執行公務案件與公然猥褻案件數量相當,由此可見妨害執行公務案件在日本并不罕見。據日本官方數據統計,自1874年設立警察制度以來的近150年間,約有5600名警察殉職。2019年G20峰會召開在即時,大阪發生的一起襲警奪槍事件,引起了日本社會乃至國際社會廣泛關注。6月16日下午5時40分左右,大阪警方接到110報警稱“有警官流血倒地”。案發當日吹田警察局千里山派出所有三名警察執勤,犯罪嫌疑人飯森裕次郎通過附近公用電話亭報假警引出兩名警官后,用菜刀刺傷了古瀨鈴之佑警官,并奪取其配槍(含五發子彈)。古瀨警官左胸部、大腿、手臂等多處受傷,左胸部傷口穿透肺部直達心臟,一度昏迷。2021年8月10日,大阪地方裁判所公開審理中對其作出了有期徒刑12年的判決。盡管被告人在起訴前后的精神鑒定中被診斷為精神分裂癥,但在判決中通過被告人以報假警的方式使自己僅面對被害警官一人、逃跑時丟棄作案衣物等行動,判斷報告人“能夠隨機應變、采取合理行為、判斷是非,并不是處于完全沒有控制行為能力的狀態”,認定其為限制行為能力。同時,法庭以“犯罪行為具有顯著危險性,給當地社會造成極大威脅、給居民造成強烈不安全感及恐懼心理”為量刑理由,駁回了辯護方的無罪主張。

2018年6月,在富山市奧田派出所,犯罪嫌疑人刺傷稻泉警官,搶奪其配槍,造成一名警察一名保安死亡;2019年1月24日,同樣是在富山市,發生了一起大學生假借來撿拾物品襲擊警察事件,該人用錘子擊打警察的頭部并用小刀劃傷了警察面部,后警察將男子制服,以殺人未遂犯罪嫌疑人將其逮捕;2019年9月19日,在仙臺市東仙臺派出所,一名大學生用刀重傷一名警官后被警察擊中,該二人送醫后均搶救無效死亡。
通過以上對近年來發生的襲警案事件的不完全舉例,我們不難看出,在治安環境全球首屈一指的日本,犯罪率雖然連續13年下跌,謀殺案比例僅為十萬分之零點三,但襲警事件仍屢見不鮮。日本警方通過增強日常訓練、增配防搶奪配槍裝備、增設監控攝像頭、避免一人勤務等方式來預防此類事件。那么日本法律如何規制上述已發生的襲警行為,本文將通過法律條文梳理及具體案例分析進行探討。
日本襲警罪法律規定
與我國單設“襲擊罪”不同,作為典型的大陸法系國家,日本刑法主要通過《刑法典》第2編第5章第95條第1款對襲警行為進行規制:“當公務員執行公務時,對其實施暴力或者脅迫的,構成妨害執行公務罪,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監禁或處50萬日元以下罰金。”同時,根據實施暴力、造成結果的程度亦可通過《刑法典》第2編第26章第199條殺人罪“殺人者處死刑、無期徒刑或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及第203條殺人未遂罪“犯第199條及202條罪未遂的進行處罰”。
(一)對象方面
依據日本刑法典第7條之規定,第95條中的“公務員”包括“國家或地方公共機構的職員”和“依照法令執行公務的議員、委員及其他職員”,如除警察之外自衛隊員、消防員、市區街道鄉政府職員、公立學校教師、公立醫院醫生、國會議員等均在其列。
(二)行為方面
日本刑法中將危害行為規定為“暴力、脅迫”,而其并不單指拳打腳踢等暴力或“要殺了你”等施加危害的語言。其“暴力”含義較刑法第208條暴力罪中定義的“使用非法的有形力量”進行了擴大解釋,即將即使不接觸身體可能對對方身體造成物理性影響的行為全部包含在內。比如拽住衣領、用力拉扯、推搡、向其腳下投擲異物、踢飛隨身物品等,除此類暴力罪中的暴力行為外,如踢踹警車等行為亦有被認定為妨害公務執行罪中的暴力行為。同樣,本罪中的“脅迫”亦不限于上述直接告知的語言,能讓對方感受到恐懼的內容均屬可能適用本條。
(三)法律適用
當一個行為觸犯多條法律時,日本司法實踐中多以想象競合,根據刑法典第54條第1款之規定:“比較競合罪名的刑罰,按照較重的刑罰處罰。” 2021年7月在東京新宿區一名抗議東京奧運會的男子與警察發生肢體沖突,警方以妨害公務罪將其逮捕。如在此案中對正在執行公務的警察有“駕車沖撞”的行為將構成暴力罪,如警察因此受重傷將構成故意傷害罪,如查明該人有殺人的故意將構成殺人未遂罪。此時將按照上述規則處較重的刑罰。
日本相關案例分析
(一)襲警行為的認定
1989年9月26日,日本最高法院第二法庭作出的判決書中對于是否應當認定為襲警行為作出了如下詳盡說明。
大阪高等法院通過“1986年1月1日晚8時48分左右,在大阪府八尾市某老人福利中心門前道路上,被告人吐的口水落在正在進行交通疏導等勤務的大阪府警察B警官身上,B警官認為被告人故意向自己吐口水,將其作為可能實施犯罪的對象為進行職務詢問,抓住其胸口欲將其壓在人行道上。被告人一邊大喊‘咬你了啊!’‘放開!’一邊踢B警官左膝數下,并擊打其面部,此行為妨害了B警官進行職務詢問”的事實認定,以及通過B警官的證言及當時情況綜合考慮,認定“為詢問被告人B警官一邊說‘你在干什么’一邊抓住被告人胸口將其壓在人行道上的行為,為依據《警察管職務執行法》第2條規定的執行職務行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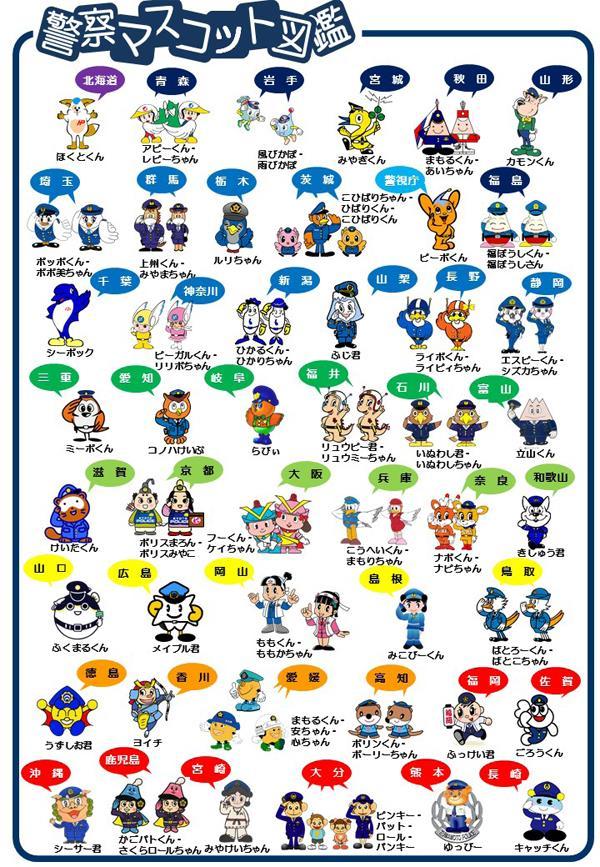
最高法院作出判決“考慮當時所處情況,即使是普通人有人向其吐口水也會問他理由,更何況是穿著制服執行公務的警察,考慮其作做出上述行為的目的是什么,會不會有更嚴重的暴力行為或者作出妨害執行公務等犯罪行為并不是沒有道理的。如果這樣,B警官對于被告人進行職務詢問是必然的,因此上述程度的行為作為職務詢問附帶行使的有形力應該說是當然被允許的。因此,原判決上述判斷是正確的”。而審判員島谷六郎提出了反對意見:因被吐口水的警官抓住被告人胸口欲將其壓在人行道上,被告人才踢警官左膝,進而擊打其面部,是否構成襲警行為值得懷疑。被告人是“故意”向警官吐口水還是吐出的口水偶然沾在了警官的衣服上尚且存疑,即便是按照原審判決中認定的“將被告人作為可能實施犯罪的對象為進行職務詢問,抓住其胸口欲將其壓在人行道上”,警察職務執行法第2條第1項中規定“警察通過異常舉動或周圍情況合理判斷后,有足夠的理由懷疑某人犯罪或預謀犯罪的,可以對其進行詢問”,本案中是否具備該要件未必明確。即使假定具備要件,根據原審判決所述,警官認定被告人吐口水后一邊說“你在干什么”一邊抓住其胸口欲將其壓在人行道上,只是警官當時的瞬間反應,是否可以認定為為進行職務詢問的執行公務值得商榷。如果進行職務詢問,作為警官直接詢問被告人即可,突然抓住被告人胸口的行為作為職務詢問是不合法的。且根據原審判決及訴訟記錄中完全看不到被告人有想要逃離的意圖,作為警官為詢問抓住被告人的胸口是沒有必要的,可以被認定為違法行為。由于不能認定為合法的執行職務行為,被告人不構成妨害公務罪。
由此可見,“職務行為的合法性”是襲警罪的基礎性條件。
(二)同時觸犯多個罪名的法律適用
2011年3月22日,日本最高法院作出的維持名古屋高級法院原判的判決書中對于被告人各行為觸犯刑法的敘述十分具有說明性:
案件中被告人為挽回前妻,準備槍支并將前妻約出見面表示想要復婚遭到拒絕后,將前妻、長子、次女一起帶到自己辦公室。為阻止此事,其長子、次女撥打110報警,警察趕到后被告人有以下行為:(1)向警察頸部開槍并擊中,妨害該名警察執行公務,同時對其造成不能痊愈之傷害,殺人未遂,此行為構成殺人未遂罪、妨害公務執行罪。(2)明顯有殺人故意地對其長子開一槍,擊中左上腹造成其需要治療三個月傷勢,構成殺人未遂罪。(3)對次女以傷害的故意開一槍,擊中右小腿,造成需治療兩個月傷勢,構成傷害罪。(4)將前妻帶入辦公室非法拘禁,構成監禁罪;同時,將前妻作為人質與警察對立。(5)此間對前妻施加暴力,造成需治療一周傷勢,構成傷害罪。(6)向不特定多數人開放的辦公室門前道路上的,執行抓捕被告人、解救人質任務的著防彈衣警察開一槍命中其左胸,妨害其執行公務并造成其死亡,構成殺人罪、妨害公務執行罪、違反《槍炮刀具持有管制法》。
最高院量刑著重考慮以下方面:首先,行為(1)(2)中以殺人的故意近距離開槍,造成被害人重傷,尤其是行為(1)的被害人是警察,造成其胸部以下癱瘓的嚴重后果。其次,行為(6)射殺執行公務的警察。因此,最高院認為“檢察官提出被告人應當處死刑的主張不是不能理解”。筆者認為此處鮮明地體現了日本法律中襲警造成傷害或死亡的,以“結果加重的傷害罪”或“結果加重的殺人罪”處罰。但結合行為(6)不能確認殺人的故意、一系列犯罪行為沒有周密的計劃性、對被害人家屬的認罪態度、無犯罪前科等多種因素,最高院維持一審處無期徒刑的判決。
【作者簡介】 劉羽佳,中央民族大學日本語言文化專業學士、山東大學法律碩士,北京市公安局朝陽分局民警。曾赴日本名古屋市立大學交流學習,2019年碩士畢業課題研究《中日公司司法解散制度比較研究——以中小股東權益保護為視角》,獲得優秀畢業論文。
(責任編輯:古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