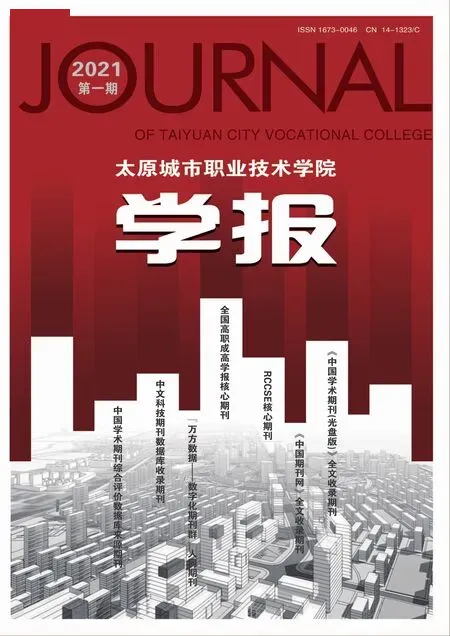法定解除權(quán)約定排除的實證研究
■張完連
(無錫商業(yè)職業(yè)技術(shù)學(xué)院,江蘇 無錫 214000)
一、問題提出
全國人大2020年5月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以下稱《民法典》)在第五百六十三條規(guī)定了法定解除權(quán)(該權(quán)利原在《合同法》第九十四條規(guī)定),在合同履行過程中若出現(xiàn)法定情形,如“不可抗力”“預(yù)期違約”“遲延履行”等導(dǎo)致合同目的無法實現(xiàn)時,法律賦予相關(guān)主體可直接解除合同的權(quán)利。但在司法實務(wù)中出現(xiàn)了當事人用約定方式排除或限制了法定解除權(quán)的使用場景,常見類型如下:第一種,直接排除法定解除權(quán)的適用,如合同約定“除不可抗力外,雙方均不得以任何理由解除合同。”第二種,合同中已存在約定解除權(quán)條款,并以此排除法定解除權(quán)的適用,如合同約定“除合同中規(guī)定的解除事由外,任何一方不得以其它理由解除合同。”第三種,雙方承諾放棄法定解除權(quán),如合同約定“為表明雙方履行合同的誠意,甲乙雙方承諾,除不可抗力外,任何一方不會基于任何理由解除本合同。”
合同中存在上述條款,但在合同履行過程中,出現(xiàn)合同法第九十四條(除第一項不可抗力外)情形之一的,當事人是否還能基于該條法律規(guī)定解除合同,在司法實踐中存在兩種觀點。
二、觀點之爭
觀點一:合同約定有效,當事人不享有法定解除權(quán)。案情及判決:北部灣有限公司(原告)與金程公司(被告)以及海宏公司被告三方簽訂一份《船舶買賣租賃合同》,約定:除非金程公司依照合同約定行使撤船權(quán)或喪失船舶所有權(quán),北部灣公司不得以任何理由退船,包括強制性及非強制性因素,否則應(yīng)按照合同約定的租期計算租金賠償金程公司損失。后在合同履行過程中,北部灣公司認為金程公司交付的標的不能實現(xiàn)合同目的,要求依據(jù)《合同法》第九十四條第四款規(guī)定的法定解除權(quán),解除合同。
在審理中,北海海事法院認為,關(guān)于合同的約定解除,《海商法》第六章未作出明確規(guī)定,但《合同法》第九十三條第二款“當事人可以約定一方解除合同的條件”之規(guī)定賦予了合同當事人約定解除權(quán),基于合同自由原則,合同當事人可以通過約定解除權(quán)對法定解除權(quán)作出具體補充或改變。關(guān)于該合同中排除法定解除權(quán)的約定是否有效的問題,一審法院認為,該條系原被告在審慎評估交易風險、權(quán)衡商業(yè)利益的基礎(chǔ)上簽訂,為各方當事人真實意思表示,原告為達成交易目的自愿對其享有的合同法定解除權(quán)進行約束,并未違反法律法規(guī)強制性規(guī)定,不屬于《合同法》第五十二條第五款規(guī)定的情形,故合法有效,對原告具有約束力。該案終審法院維持一審法院的判決,但未對一審的該項觀點做出評議。
該觀點的法律依據(jù)和論證思路是:第一,契約自由精神是合同法最根本的精髓和原則,尊重當事人合同約定是該項原則最重要的體現(xiàn)。第二,對合同法第九十四條予以文意解釋,“出現(xiàn)以下情況,當事人可以解除合同”,因其中使用“可以”一詞,所以該條屬于任意性法律規(guī)范,任意性規(guī)范屬于指導(dǎo)性規(guī)范,當事人可以排除適用。第三,從法條設(shè)計角度而言,法定解除權(quán)設(shè)置在約定解除權(quán)之后,是約定解除權(quán)的有益補充,而不能成為優(yōu)先于合同約定的存在。
觀點二:合同約定無效,當事人仍然享有法定解除權(quán)。
案情及判決:宏達公司與駿馬公司簽訂《設(shè)備開發(fā)協(xié)議》,約定宏達公司為駿馬公司開發(fā)機心插件安裝機。雙方約定,簽訂協(xié)議后,任何一方均不得退出該協(xié)議。在設(shè)備交貨后,因設(shè)備一直未能調(diào)試成功,駿馬公司要求解除合同。宏達公司認為,根據(jù)合同約定,雙方均不得退出合作,因此駿馬公司單方解除合同構(gòu)成違約,雙方就此發(fā)生爭議。
本案經(jīng)廣東高院最終裁定認為,涉案兩公司簽訂的《設(shè)備開發(fā)協(xié)議》是雙方真實意思表示,對雙方均具有法律約束力。根據(jù)約定,提供合格設(shè)備是宏達公司的合同義務(wù),其開發(fā)的成果需要委托方駿馬公司驗收合格。宏達公司一直未能舉證證明其在交付近兩年時間內(nèi)已交付合格設(shè)備,駿馬公司的合同目的不能實現(xiàn),因此其享有法定解除權(quán),即享有僅憑法定事由作出的意思表示即可使雙方現(xiàn)有的法律關(guān)系消滅的權(quán)利,該權(quán)利不能以協(xié)議約定排除,其發(fā)函要求解除合同合理合法。
該觀點的主要論點和論證思路是:第一,如果排除法定解除權(quán)的約定有效,將會導(dǎo)致一方當事人在另一方出現(xiàn)嚴重違約情形或不能實現(xiàn)合同目的的情況下,仍不能解除該合同,非違約方仍需受該合同義務(wù)的約束,明顯有悖公平。第二,該條使用“可以”而非“應(yīng)當”一詞,旨在表明法定解除權(quán)是當事人的一種法定權(quán)利,在合同履行中,如一方出現(xiàn)合同法第九十四條規(guī)定之情形,另一方即享有解除和他的權(quán)利,該項權(quán)利是一項法定權(quán)利,不可以約定排除,但當事人可以自主決定是否行使。
三、立法剖析
法定解除權(quán)作為一項基于法律規(guī)定而產(chǎn)生的權(quán)利,該權(quán)利不能通過雙方約定直接或間接予以排除,亦不能以事先承諾的方式予以放棄,否則與立法本意相悖,亦于當事人不公。具體理由如下:
(一)法定解除權(quán)基于法律規(guī)定而產(chǎn)生,不屬于民事法律行為,不宜以任意性規(guī)范和強制性規(guī)范的視角予以定性和歸類。
就法定解除權(quán)的權(quán)利屬性而言,其既非人身權(quán),亦非財產(chǎn)權(quán)。依據(jù)《民法典》第一百二十六條和第一百二十九條相關(guān)規(guī)定,法定解除權(quán)應(yīng)當屬于法律規(guī)定的民事權(quán)利,該項權(quán)利既不是基于當事人的主觀意思產(chǎn)生的民事行為,亦不是通過事實行為而為當事人所取得,更非基于客觀事件而發(fā)生,而是基于法律的直接規(guī)定產(chǎn)生的民事權(quán)利。
市場活動中的不同主體之間的交易關(guān)系,在合同領(lǐng)域最終表現(xiàn)為雙方通過民事法律行為創(chuàng)立、變更、終止某種債權(quán)債務(wù)關(guān)系。民事法律規(guī)范主要是對當事人通過自己的意志確立的交易關(guān)系進行調(diào)整、規(guī)范和評價的法律規(guī)范,該等法律規(guī)范,從法律屬性上分為任意性法律規(guī)范和強制性法律規(guī)范。對于任意性法律規(guī)范,法律只是指導(dǎo)當事人行為,雙方如有約定則“約定大于法定”,對于強制性法律規(guī)范,應(yīng)依法行事。但是,法定解除權(quán)并非基于民事法律行為產(chǎn)生,而是基于法律規(guī)定直接產(chǎn)生的一種法定權(quán)利,所以,其不宜納入民事法律行為所形成的權(quán)利義務(wù)的框架下定性、歸類。
(二)法定解除權(quán)屬于形成權(quán),該項權(quán)利在合同簽訂時尚未現(xiàn)實化、確定化,無法成為處分行為的客體,因此事先的處分行為無效
法定解除權(quán)屬于形成權(quán)。從法律概念上講,形成權(quán)是指當事人一方可以根據(jù)自己的意思行事,從而使法律關(guān)系發(fā)生改變的一種權(quán)利。形成權(quán)有追認權(quán)、選擇之債的選擇權(quán)、合同的撤銷權(quán)等[1]。形成權(quán)的概念屬于法學(xué)理論范疇,在現(xiàn)有法律規(guī)范中未有形成權(quán)的定義、種類、行使方式和消滅制度。
在我國《合同法》中未明確解除權(quán)的性質(zhì),因此在法學(xué)理論界對該項權(quán)利的定性一直存有爭議,《民法典》第五百六十四條關(guān)于合同解除權(quán)的行使期限的規(guī)定使得這一問題的答案更加明朗化。第五百六十四條第二款規(guī)定參照了合同撤銷權(quán)期限和行使規(guī)則的相關(guān)內(nèi)容,印證了合同解除權(quán)和合同撤銷權(quán)在性質(zhì)上屬相同或類似權(quán)利。《民法典》規(guī)定了合同解除權(quán)的行使期限,但未規(guī)定合同解除權(quán)的拋棄制度,為了使可解除的合同在當事人之間的狀態(tài)盡快明確化,該項內(nèi)容可以參照《民法典》總則的相關(guān)內(nèi)容。
參照《民法典》第一百五十二條第三項規(guī)定,法定解除權(quán)亦可以明示或默示的拋棄使其消滅。筆者認為,法定解除權(quán)的拋棄制度應(yīng)當解讀為:首先,法定解除權(quán)并非自始存在,該項權(quán)利在當事人之間是否產(chǎn)生以及產(chǎn)生的時間點具有不確定性。其產(chǎn)生的時間點既不是合同簽訂時亦并非合同生效時,而是在合同履行中出現(xiàn)法定解除權(quán)的情形后才產(chǎn)生。那么,在合同簽訂之初,當事人如何能對一項尚未產(chǎn)生的權(quán)利作出界定或約定排除呢?其次,法定解除權(quán)的享有主體在合同簽訂之時仍未確定。對于合同雙方當事人而言,在合同法定解除權(quán)情形出現(xiàn)之前,究竟哪方是將來享有解除權(quán)的當事人仍屬未知,又如何能做出放棄權(quán)利的意思表示?明顯與常理相悖。再次,法定解除權(quán)作為形成權(quán),對該權(quán)利的約定或處分只能發(fā)生在權(quán)利產(chǎn)生之后,對未來權(quán)利特別是存在與否仍不確定的權(quán)利的處分不能成為有效的處分行為。因此,權(quán)利人在享有法定解除權(quán)后,可以明確表示或自己的積極行為表明其不行使法定解除權(quán),才是法定解除權(quán)的正確實施之道。
(三)法定解除權(quán)是法律賦予一方當事人的救濟選擇權(quán),該項權(quán)利的設(shè)置既是市場經(jīng)濟效率原則的要求,同時亦是法律公平公正原則的體現(xiàn)
根據(jù)《民法典》第四百六十五條之規(guī)定,合同一經(jīng)有效成立,就在當事人之間具有法律效力,當事人需恪守合同。但在合同履行過程中,由于情況變化致使合同履行不可能,合同繼續(xù)存在已失去積極意義,法律理應(yīng)賦予相關(guān)主體救濟選擇權(quán),通過行使解除權(quán)使雙方的法律關(guān)系歸于消滅,使其能從合同中解脫出來,以盡快進入下一個交易關(guān)系中,這也是市場經(jīng)濟效率原則的體現(xiàn)。
《民法典》第五百六十三條所列舉解除的情形,除不可抗力外,均是一方嚴重違約致使不能實現(xiàn)合同目的的情形,若該等情形出現(xiàn),非違約方仍需恪守己方合同義務(wù)或仍需被迫繼續(xù)等待違約方履行合同,明顯有悖法律公平公正。當然,享有法定解除權(quán)的權(quán)利主體自愿繼續(xù)等待或接受現(xiàn)狀,是其對權(quán)利的自由處分,法律理不應(yīng)予以干涉。
《民法典》中的合同解除制度是以約定解除權(quán)和法定解除權(quán)為根本、以特定有名合同中的任意解除為特例構(gòu)建合同解除制度。法定解除權(quán)的設(shè)置所保護法益是市場經(jīng)濟的效率原則和法律制度的公平公正理念,約定解除權(quán)的設(shè)置所保護的法益是契約自由精神。法定解除權(quán)就其權(quán)利屬性、權(quán)利本質(zhì)以及立法目的而論,均不可以通過合同事先約定排除適用,如果約定解除權(quán)排除法定解除權(quán)得到認同,那么法定解除權(quán)就有可能被隨意架空,法律創(chuàng)設(shè)該制度的目的將付之東流。因此在合同條款中出現(xiàn)的任何形式的排除條款均應(yīng)當認定為無效,而該權(quán)利的消滅可依法定期限的經(jīng)過和當事人的放棄而歸于消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