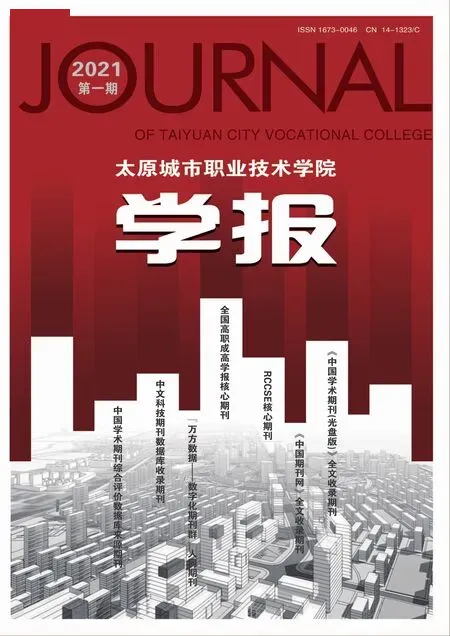事件特征與民眾普遍信任的關系:災難性思維與人格特征的作用
2021-02-26 14:13:10■雍藝,張野
太原城市職業技術學院學報
2021年1期
■雍 藝,張 野
(沈陽師范大學,遼寧 沈陽 110034)
在新冠肺炎疫情肆虐期間,封城、生活醫療物資的短缺、無法復工復產等問題都在一定程度上加劇了民眾恐慌,對疫情的防控工作造成影響。而民眾的普遍信任則是有助于國家進行疫情管控,盡可能地減少疫情損失帶來的重要心理變化。普遍信任是指個體對自己不認識的、不熟悉的或者任何關系之外的其他人的信任,即對陌生人或公眾的一般化、社會性信任[1]。普遍信任是社會秩序的源泉、潤滑劑與黏合劑,在經濟發展、社會管理中具有無可替代的作用[2],它與整體社會的團結和穩定程度都息息相關[3]。在此次疫情突發事件的應急管理中,民眾是突發事件應急管理的基本依靠力量,而普遍信任是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治理的重要民眾心理基礎。新冠病毒肆虐下,由于疫情的迅速傳播和蔓延給民眾帶來極大的焦慮、恐慌,疫情的人傳人特點也造成了民眾間的信任難題,并成為影響疫情防控效果的重要因素。因此,探索新冠疫情事件對中國民眾普遍信任的關系,對于出臺引導民眾心態、促進民眾共同參與疫情防控的措施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
有關事件影響民眾心理與行為的研究、事件系統理論近年來受到學者們的普遍關注。Morgeson等[4]于2015年提出的事件系統理論(event system theory,EST)是將特征導向理論和事件導向理論相結合,用以解釋事件如何從強度、時間、空間3個維度對組織行為產生影響的研究方法[5]。趙紅丹等(2018)認為可從強度屬性(新穎性、顛覆性、關鍵性)、時間屬性(事件時機、事件時長、事件強度)、空間屬性(方向性、發散性、起源)三個屬性來定義事件[6]。……
登錄APP查看全文
猜你喜歡
小哥白尼(野生動物)(2022年6期)2022-08-17 08:05:28
小哥白尼(野生動物)(2022年4期)2022-07-16 03:37:32
小哥白尼(野生動物)(2022年2期)2022-06-01 06:21:20
小哥白尼(野生動物)(2022年1期)2022-04-26 14:01:18
音樂天地(音樂創作版)(2022年1期)2022-04-26 13:51:10
環球時報(2022-04-25)2022-04-25 17:20:21
今日農業(2021年15期)2021-10-14 08:20:18
人大建設(2020年5期)2020-09-25 08:56:22
快樂作文(1.2年級)(2020年8期)2020-09-10 07:22:44
人大建設(2020年3期)2020-07-27 02:48: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