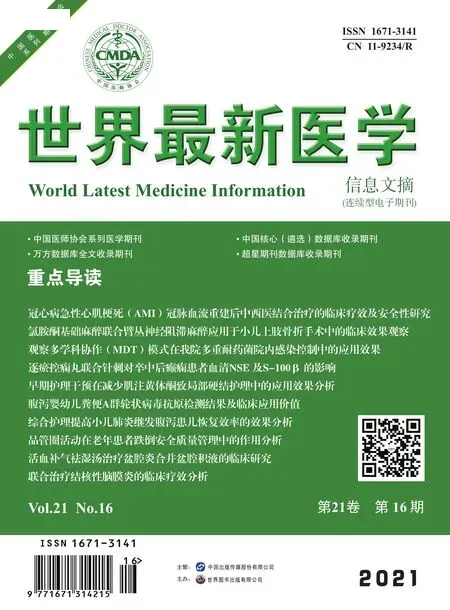中性粒細胞/淋巴細胞比值在頭頸腫瘤-喉癌中的預后作用
韋廷佳,溫麗慧
(廣西欽州市第二人民醫院 耳鼻咽喉頭頸外科,廣西 欽州)
0 引言
喉鱗狀細胞癌(Laryngeal Squamous Cell Carcinoma,LSCC)是頭頸最常見的癌癥之一,占全世界所有惡性腫瘤1%~2%[1],喉癌是一個多因素的過程,其具體機制沒有完全闡明,傳統的預后因素,如腫瘤分期、淋巴結包膜外擴散和外科切緣,已普遍用于預測喉癌患者的預后。目前盡管有ERRC1、p16、K-ras、EGFR、EGFRvIII 等生物標志物,但由于其在臨床應用、可重復性和費用上的局限性,上述生物標志物均未在頭頸腫瘤中得到常規和廣泛的應用。因此,尋找更多新的生物標記物,具有重要意義,而中性粒細胞- 淋巴細胞比率(NLR)作為全身炎癥反應生物標志物被推廣。
1 NLR 與炎癥
炎癥是腫瘤進展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它與各種腫瘤的預后不良有關,是癌癥和免疫細胞(如中性粒細胞、T 和B 淋巴細胞)的標志之一。頭頸腫瘤由多種免疫細胞浸潤,如中性粒細胞、T 和B 淋巴細胞,這些細胞產生細胞因子、趨化因子和炎性介質,與宿主相互作用引起全身炎癥反應,導致血循環白細胞水平的變化[2],包括中性粒細胞性白細胞增多癥和淋巴細胞減少癥,可為癌癥患者的預后提供參考價值。
NLR 增高被證實為炎癥標記,并顯示對許多腫瘤的預后具有意義。有人報道,它可以通過增加可用性生長因子,血管生成因子和其他癌前信號分子促進癌細胞增殖來預測不良的愈后[3]。NLR 可能代表了共存于癌癥患者內兩個對立的炎癥和免疫通路,炎癥和免疫系統的激活具有抗腫瘤活性,它們在腫瘤發生、生長和腫瘤進展中起作用[4]。炎癥在癌癥發病機理中的作用得到了廣泛的研究。
1.1 間接作用
一些促炎細胞因子通過抑制細胞凋亡、促進血管生成和DNA 損傷而強烈影響免疫狀態[5],從而促進腫瘤細胞的增殖和存活,并產生全身炎癥反應,包括白細胞的變化[6]。腫瘤相關炎癥通過募集調節性T 細胞和激活趨化因子抑制抗腫瘤免疫,導致腫瘤生長和轉移。
1.2 直接作用
炎性細胞因子也可能直接導致惡性腫瘤進展,并可通過誘導致癌突變、基因組不穩定、早期腫瘤生成以及增強血管生成而促進腫瘤發展[7]。
1.3 相互作用
癌癥治療還可以通過引起創傷、壞死和組織損傷來觸發炎癥反應,從而刺激腫瘤的再次出現和對治療的抵抗。然而,炎癥并非都促進腫瘤進展,在某些情況下,治療引起的炎癥可以增強抗原呈遞,導致免疫介導腫瘤根除[8]。NLR 反映全身炎癥反應,可作為反映炎癥細胞活性的綜合評分,促進腫瘤生長和進展,是一個簡單有效的預測患者炎癥和免疫狀態的標志物。
2 中性粒細胞與腫瘤
中性粒細胞在腫瘤惡化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首先,中性粒細胞為腫瘤的進展提供所需的生物活性分子,包括血管生成因子、上皮和基質生長因子和基質重塑酶[3],因此,中性粒細胞可能通過血管內皮生長因子、白細胞介素-8 和基質金屬蛋白酶-9 刺激腫瘤的生長和血管生成,而血管生成在惡性腫瘤的生長和轉移中起重要作用,如腫瘤相關中性粒細胞(TANS)通過血管生成促進腫瘤生長[9],有絲分裂分子-中性粒細胞彈性蛋白酶,則起抗腫瘤免疫抑制作用[10];此外,TANS 通過轉移癌細胞促進轉移,此效應可能是由中性粒細胞胞外的染色質和分泌的蛋白酶形成的陷阱介導的[11];其次,中性粒細胞通過產生活性氧、精氨酸酶和一氧化氮來抑制淋巴細胞的細胞毒活性[12]。相反的,癌癥也可以促進中性粒細胞增多,癌癥可以產生髓樣生長因子,如粒細胞集落刺激因子、腫瘤壞死因子-α、白細胞介素-1、白細胞介素-6等可能影響腫瘤相關白細胞和中性粒細胞增多[13]。如在喉癌患者外周血中性粒細胞計數升高,并且可以將喉癌和喉部良性病變區分開[14],因此,中性粒細胞計數增加可作為喉癌患者預后的指標。
3 淋巴細胞與腫瘤
在腫瘤微環境的免疫細胞中,淋巴細胞的作用已經得到廣泛的研究。浸潤腫瘤組織的淋巴細胞具有腫瘤抑制功能,該功能受到腫瘤免疫逃逸系統的抑制,腫瘤浸潤淋巴細胞(TIL)的增加與許多類型癌癥的預后有關,比如TIL 可以改善包括HNSCC 在內的幾種實體癌的預后[15]。
T 淋巴細胞是宿主免疫系統中非常重要的血液細胞,可以促進細胞因子分泌、激活巨噬細胞,調節細胞的免疫作用,促進效應細胞發揮抗癌效應,對于抗腫瘤反應具有強烈激活作用[16];因此,LSCC 中淋巴細胞數量的減少通常被認為呈現免疫抑制狀態,并且可能減弱淋巴細胞介導的抗腫瘤免疫[17]。
4 NLR 與喉癌
NLR 與頭頸部惡性腫瘤密切相關,高水平的NRL 已經證實與喉癌有關系。有研究報道,高水平的NLR 可能增加腫瘤的復發、侵襲性、轉移傾向并與預后不良有關[18]。這意味著NLR 可以跟當前TNM 分類相結合用來提供預后信息。
NLR 可用于早期喉癌的篩查:有研究發現喉鱗狀細胞癌與良性和喉癌前病變相比較,NLR 顯著升高[19-20],因此NLR是一個區分良性和惡性喉部病變的有用炎性標志物;NLR 也可用于局部晚期喉癌患者放化療預后的有用指標:可預測化療療效和生存時間,表明NLR 可作為危險分級簡單可靠的預后因素,并可為局部晚期喉癌患者放化療提供更好的治療方案;另有研究發現,低NLR 與提高臨床效益相關,并且NLR被證實可獨立預測局部晚期喉癌放化療患者的無進展生存期和總生存率,因此,盡管局部晚期喉癌化療敏感性低,但NLR 仍可作為局部晚期喉癌放化療患者的一種實用臨床指標,可以篩選高NLR 患者進行更積極的監測和治療。通過對喉癌局部復發患者的研究發現,平均NLR 值明顯高于非復發患者,但喉癌組織中腫瘤的大小和分期無明顯差異。因此,治療后高NLR 可能是頭頸部鱗癌復發和腫瘤特異性存活的另一個預測指標,提示NLR 可作為喉癌良、惡性病變的診斷、預后或復發的有效鑒別指標。
雖然許多研究證實NLR 升高與預后不良有關,但其機制尚未完全闡明。一種可能的解釋是血循環中性粒細胞數量相對增加,可以促進癌細胞生長和轉移和/或抑制淋巴細胞活性,產生和分泌血管生成調節生長因子、趨化因子和蛋白酶,因此,升高的中性粒細胞計數刺激腫瘤血管生成,并有助于腫瘤的進展。另一種解釋是宿主對腫瘤的免疫應答是淋巴細胞依賴性的,淋巴細胞可以攻擊癌細胞并清除新生的腫瘤細胞,NLR 升高的患者通常具有相對淋巴細胞減少,事實上,淋巴細胞負責抗癌免疫應答,而CD8+T 細胞通過凋亡和細胞毒作用特異性地控制腫瘤活性。因此,淋巴細胞計數與癌癥的嚴重程度呈反比。
5 結語
中性粒細胞、淋巴細胞和NLR 聯合作為宿主炎癥的標志物,已被確定為不同惡性腫瘤的獨立預后因子,但是NLR 在預后上可能優于中性粒細胞和淋巴細胞,并且炎癥導致的高NLR 值被認為與較差的預后相關。
由于NLR 易于獲得和測量,成本低廉,與性別無關,并且隨著年齡增加而穩定,可以為臨床決策建立預后因素,也可作為分期、淋巴結轉移及遠處轉移的預測因子,因此它可作為LC 的常規預后生物標志物,但需要進一步的前瞻性研究,用標準化的截斷值進行LC 的風險分層和確定預后和生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