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色搖滾與黑色幽默
胡繼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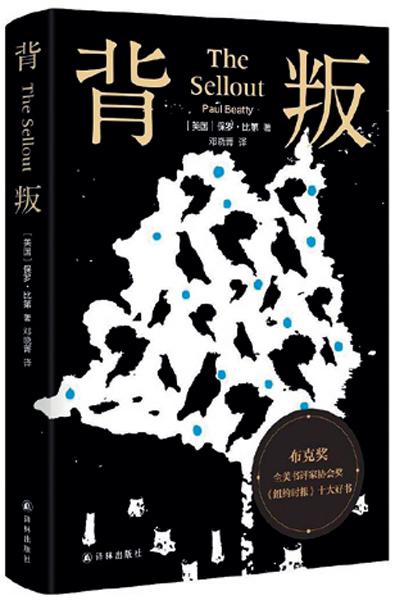
《背叛》
(美)保羅·比第著
鄧曉菁譯
譯林出版社
2020年9月
“我痛,故我寫;我寫,故我痛。”對(duì)于保羅·比第而言,這一怪誕的惡性循環(huán)邏輯貫穿著他的生命,扭曲了他的群族的歷史,還籠罩著他及其群族的未來。悖論乃是一朵曼妙的“鷹風(fēng)”云,出沒在洛杉磯縣“狄更斯”鎮(zhèn)上空,壓抑著比第筆下的雜色人等。
于是有了《白種男孩的混局》,有了《沉睡國(guó)土》,有了《塔芙》,有了《扯淡》,更有了《背叛》。2016年,比第以《背叛》摘取了布克文學(xué)獎(jiǎng)桂冠,成為歷史上第一位獲此殊榮的美國(guó)作家。
平心而論,《背叛》是一本對(duì)讀者不太友好的小說。敘述開篇,將近100頁的文字幾乎語無倫次,時(shí)刻在惹是生非,情感節(jié)奏推進(jìn)與展開令人窒息。比第用文字玩起了搖滾,讀著讀著,讀者將會(huì)情不自禁地隨著這震蕩的獨(dú)白節(jié)奏、訪談對(duì)答節(jié)奏而瘋狂起舞。他用黑人獨(dú)特的象征程式表演了后種族主義時(shí)代黑人的荒誕生存處境、甚至還有當(dāng)代人類的荒誕生存處境。
藝術(shù)風(fēng)格:黑色搖滾
非裔美國(guó)黑人,一個(gè)特殊的族群。他們遺忘了對(duì)家園的記憶,生活在一個(gè)后種族主義時(shí)代。我們不知道,后種族時(shí)代究竟從何時(shí)開始?始于廢奴法案?始于馬丁·路德·金的那個(gè)偉大夢(mèng)想?始于新冠疫情下黑人弗洛伊德事件引發(fā)的全球反種族歧視熱潮?好像一切都是標(biāo)志。“我寧可被九個(gè)人復(fù)審,也不想被一個(gè)人裁決。”一個(gè)毫無過錯(cuò)更談不上犯罪的非裔美國(guó)人,在通往美國(guó)最高法院的臺(tái)階上坐著,抽著大麻,幾百年種族主義與反種族主義的歷史在他狂野的心中如潮涌動(dòng)。在這個(gè)“歇斯底里、危機(jī)四伏”的時(shí)代,非裔美國(guó)人也像其他族群一樣,將“不曾被征服,也不會(huì)被征服”的口號(hào)銘刻在種族的靈旗上。為了族裔,可以做一切!緊接著另一句話則令人毛骨悚然:離開族裔,什么都不是!以黑人搖滾的文學(xué)風(fēng)格,比第開始敘說一個(gè)不可敘說的“破碎故事”,黑人心靈的奧德賽伴隨著搖滾樂的節(jié)奏忘情展開。
故事以洛杉磯縣一個(gè)消逝的“狄更斯”小鎮(zhèn)為中心展開。一個(gè)無名的敘述者,不知道自己自何處而來,更不知道自己往何處而去。被他變態(tài)的父親當(dāng)做試驗(yàn)品,敘述者度過了恐怖而至麻木、好奇而至冷漠的童年。被他的相好稱為“棒棒”,敘述者一頭扎進(jìn)了秩序混亂、充滿了欺詐與暴力的荒誕人際關(guān)系中。他的父親成為警察執(zhí)法暴力的犧牲品。他將父親埋葬在后院,死者的冤魂便成為種族主義時(shí)代的幽靈。“我是誰?我怎樣才能成為我自己?”敘述者子承父業(yè),成為一名黑人勸語者。他整個(gè)一生,都在用這兩個(gè)“不解之問”折磨著他的顧客——一個(gè)永遠(yuǎn)也不會(huì)知道自己“緣何而來”的群體。對(duì)于敘述者所屬的這個(gè)苦難群體,世界距離他們?cè)絹碓竭h(yuǎn),他們的生存境遇越來越凌厲。一如漢娜·阿倫特所說,一旦喪失記憶,一旦失落未來,人就充滿恐懼,從不太友好、甚至萬分凌厲的世界抽身而出,反求諸己。反求諸己的內(nèi)省、沉思、思辨甚至狂想,貫穿在比第筆下無名的敘述者的言說之中:父親慘死,家園消逝,語言喪失,最后主張重建種族隔離制度以便重建人類的和睦關(guān)系。
和整個(gè)狄更斯小鎮(zhèn)的人沒有什么兩樣,敘述者是他父親的兒子,后種族時(shí)代環(huán)境的畸形產(chǎn)物。除此之外,他什么都不是。狄更斯小鎮(zhèn)就是敘述者,敘述者就是敘述者的父親。小鎮(zhèn)淡淡地消逝,父親慘烈地死去,家園和祖先都從他的生命之中被抹去了,沒有留下一點(diǎn)痕跡。于是,背叛就是生命被背叛和自我背叛,記憶的被出賣和自我出賣,歷史的被涂抹和主動(dòng)涂抹。存在的證據(jù),絕對(duì)地消逝了,不留痕跡、不余灰燼地消逝了,天空地白。對(duì)《背叛》的作者而言,對(duì)“出賣”的敘述者而言,哀悼是不可能的。非裔美國(guó)人族群沒有時(shí)間觀念,只有瞬息體驗(yàn)。一切轉(zhuǎn)瞬即逝,執(zhí)手已違,敘述者冷漠地說:“忽然之間,我不知道我是誰了,對(duì)于如何成為我自己便是一無所知。”
這種荒誕的美學(xué)是黑人搖滾風(fēng)格的精髓。荒誕是一種徹底的異化感,一種時(shí)刻與悖謬的生存處境遭遇、卻永遠(yuǎn)無法克服生存悲劇的生命體驗(yàn)。呈現(xiàn)荒誕幾乎就是與荒誕抗?fàn)帲鲃?dòng)遺忘本質(zhì)上就是與遺忘搏斗。《背叛》將搖滾風(fēng)格夸張地表現(xiàn)到了極限,將荒誕的美學(xué)提升為一種生存的藝術(shù),一種讓整體族群克服苦難的狂歡藝術(shù)。回應(yīng)滾石樂隊(duì)的采訪,比第坦言,黑人文學(xué)的搖滾風(fēng)格構(gòu)成了荒誕美學(xué)之內(nèi)核:“我的小說迫不及待地?fù)肀铄涞乃椎溃簿褪钦f,擁抱荒誕。原因在于,那些極端不得體的素材,卻總是命運(yùn)之巔峰,美的至境。”《背叛》的敘述包孕在搖滾樂一般的激劇節(jié)奏之中。諷刺之犀利,遠(yuǎn)祧蘇格拉底,近緣斯威夫特和馬克·吐溫。悲劇之徹骨,則比肩梭羅與卡夫卡。在文學(xué)的精致與歷史的敏感之間,《背叛》的敘事充滿了強(qiáng)大、深邃的張力,指向玄遠(yuǎn)、廣闊的未知。
令人忍俊不禁的笑話和讓人黯然神傷的悲情,并行不悖地流蕩在敘述的話語詞鋒之中:一方面,穆罕默德、拿破侖、查理曼大帝、古希臘俊美少年,沿著歷史的幽深河流順勢(shì)而來,向非裔美國(guó)人傳遞著民主和公平競(jìng)爭(zhēng)的信息,支撐著支離破碎的世界和無家可歸的人;另一方面,好萊塢大片,黑臉丑娃娃,《搗蛋鬼》式的滑稽劇,公交車上的狂歡派對(duì),詹姆斯·迪恩對(duì)黑人文化的沉思,又在變態(tài)的世紀(jì)和狂熱的當(dāng)下將人類拖向紊亂的深淵。黑人驅(qū)趕著白人,讓白種男人和白種女人夾著尾巴和假想的歷史離開,消逝在茫茫夜色中。但黑人卻真的不知道“到底什么才是我們的東西”?永遠(yuǎn)不明白,黑人和白人都一樣,困境無分種族。
比第將悲劇與滑稽、嚴(yán)肅與幽默融為一爐,鑄造黑色搖滾風(fēng)格,呈現(xiàn)他的種族主義體驗(yàn),展開后種族主義時(shí)代的人類關(guān)切。他半開玩笑地說,要發(fā)明一種“種族主義的里氏震級(jí)儀器”。在美國(guó)加州,在云煙之城“狄更斯”,小震可能比大地震令人不安,小震預(yù)兆大地震,大動(dòng)蕩即將到來。于是,比第以黑色搖滾開啟了當(dāng)代黑人的靈魂啟示錄。風(fēng)趣而又睿智,明快而又緊張,喜劇的至境是悲劇,滑稽的巔峰是崇高。所以,《背叛》便是為了忘卻的記憶,為了永別的哀悼,為了死亡的重生。
歷史蘊(yùn)藉:黑人意指,意指黑人
黑人家園失落,無名氏重建隔離區(qū)。黑人身份疏離,無名氏竟然養(yǎng)護(hù)黑奴。被養(yǎng)護(hù)的黑奴,是民間黑人藝術(shù)家,自殺未遂,主動(dòng)為奴。無名氏與老黑奴之間,一種畸形變態(tài)的溫情,在這個(gè)凌厲世界、風(fēng)險(xiǎn)社會(huì)、敵對(duì)沖突的人際關(guān)系中,反而顯得是一份令人動(dòng)容的溫情。奴隸制已經(jīng)廢除200多年,可是黑人仍然在自己的家園流浪,而他們的家園也消逝了,慘淡而且無聲無息。
老奴與無名氏敘述者之間變態(tài)的依戀關(guān)系,不妨視為一個(gè)新奇的隱喻,意指著族群艱難的自我認(rèn)同,同類之間惺惺相惜,彼此守望,相對(duì)溫暖。“把狄更斯找回來。”“你知道這是不可能的。城市一旦消失,就再也回不來了。”黑人只有無休止地浪游,浪游便是一種自愿的放逐。但是,他們究竟應(yīng)該到何處去安放“同一個(gè)身體、同一種思想、同一顆心靈、同一份愛”?永遠(yuǎn)忠誠,永遠(yuǎn)時(shí)尚。以無名氏父子、老黑奴霍米尼、女公交車司機(jī)為代表的非裔美國(guó)人,在永無止境的流浪中獲得了一份豐厚的文化資本,其精神光譜涵蓋了高雅文化與大眾文化,白人文化與黑人文化。在小說中,黑人在特定位置上獲得的文化,并沒有再次展開為一種特殊的文化。他們的文化并非號(hào)稱的美國(guó)“文化多元主義”的標(biāo)本。他們的黑色搖滾與荒誕美學(xué),乃是對(duì)“文化多元主義”的顛覆性戲仿。
《背叛》的敘事,因此就成為一種黑人文學(xué)的意指。小亨利·路易斯·蓋茨指出,黑人文學(xué)的意指之中,“意指”和“表意”制造了一種沉默中喧囂的混亂,體現(xiàn)了黑人意指的雙聲性。于是,矛盾、對(duì)立、悖論、絕境,成為黑人文學(xué)的文化無意識(shí)。《背叛》之中,新奇的隱喻、畸形的象征、含糊的意象比比皆是:敘述者的后院埋葬著亡父,還有一株為閃電燒焦的玉蘭樹;被上帝觸摸過的白人女性白色的肌膚;黑蛾子與老黑奴都長(zhǎng)著一副與生俱來屈從的臉;穿越狄更斯城的公交車上有一個(gè)通往自身的種族漩渦,老黑奴的座位就是種族主義旋轉(zhuǎn)的中心;敘述者將公交車開成一種文化批判的手段,正如戈達(dá)爾把電影拍成斗爭(zhēng)的工具。
因此,黑人文學(xué)的意指乃是“述行話語”的典范,它不是記述一段歷史,而是創(chuàng)造一個(gè)新天新地。像一切語言形式一樣,文學(xué)的意指假設(shè)讀者主動(dòng)參與一場(chǎng)對(duì)話,進(jìn)入一個(gè)巨大的話語和知識(shí)庫藏,但立即顛覆了這些話語、這些知識(shí)。與一切語言形式不一樣,文學(xué)的意指要求不斷在非裔美國(guó)文化傳統(tǒng)和其他文化傳統(tǒng)之間進(jìn)行語碼切換。意指黑人就是黑人意指。正如阿多諾所說:“美學(xué)的身份同一性……必須襄助非同一身份者反抗統(tǒng)治著外在世界的壓抑性認(rèn)同強(qiáng)制。”在后種族主義時(shí)代,壓抑性認(rèn)同的強(qiáng)權(quán)依然存在。《背叛》的敘述者將救贖的希望寄托在復(fù)活種族主義、重建種族隔離之上。仿佛種族隔離的幽靈,讓云煙消散的狄更斯城再次凝聚起來。保羅·比第妒忌老黑奴的健忘,但歷史的難題永在。他深知,歷史不是印刷文字的紙,而是記憶,但記憶是時(shí)間、情感和歌聲。總之,歷史是那些與我們?nèi)缬半S形的東西。
(作者為北京第二外國(guó)語學(xué)院教授;編輯:臧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