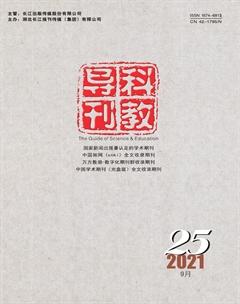形象學視域下博爾歇特文學作品中的德國形象
摘要在形象學視域下以博爾歇特文學作品為研究對象,從其戲劇和短篇小說的文本中梳理歸納出兩種德國形象:戰爭中的德國和廢墟中的德國。這兩種形象涵蓋了博爾歇特不同題材的文本對于20世紀30-40年代德國形象的表述。以這兩類德國形象的角度可以較好地概括博爾歇特文學作品塑造的“德國形象”的性質,從中可以分析博爾歇特在二戰時和二戰后對德國多維度的反思視角、樣式和表述策略。
關鍵詞 形象學 博爾歇特 德國形象 德國文學
中圖分類號:I106.4文獻標識碼:ADOI:10.16400/j.cnki.kjdk.2021.25.017
The Image of Germany in Borchert’s Literary Work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conology
LI Tingting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Jinggangshan University, Jian, Jiangxi 343009)
Abstract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magology, this paper takes Borchert’s literary works as the research object, and summarizes two kinds of images of Germany from his plays and short stories: Germany in war and Germany in ruins. These two kinds of images cover the expression of German images in the 1930s to 1940s in Borchert’s texts of different them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se two types of German images, we can better summarize the nature of“German image”created by Borchert’s literary works, and analyze Borchert’s multidimensional reflection perspective, style and expression strategy on Germany during and after World War II.
Keywordsimagology; Borchert; Germany’s image; German literature
比較文學形象學主要研究文學作品、文學史及文學評論中有關民族亦即國家的“他形象”和“自我形象”。形象學的研究重點并不是探討“形象”的正確與否,而是研究“形象”的生成、發展和影響;或者說,重點在于研究文學或非文學層面的“他形象”和“自我形象”的發展過程及其緣由。形象學的一個文學研究視角指出,形象存在于文學批評以及文學史編撰和文學研究中。任何國家的形象都是由各種文學和非文學的力量交織在一起的復雜組成,它間接反映了一個國家的社會和文化狀況。文學作品中的國家形象指的是文學作品的題材、人物、環境、主題喚起人們對一個國家社會生活的印象、評價和想象。
1博爾歇特及其主要作品
沃爾夫岡·博爾歇特短暫的26年時光基本上與德國納粹政權的崛起與滅亡同步。作為一個敏感的作家,但也作為一個應征加入納粹德國軍隊的士兵,博爾歇特直接或間接地在文學作品中寫下了他在20世紀30-40年代德國社會經歷。博爾歇特以自己的親身經歷為基礎創作的文學作品為納粹極權統治下的德國社會生活以及戰后廢墟中的德國社會生活提供了紀實和抗議。從中國知網文獻檢索的結果來看,國內對德國二戰后“廢墟文學”先驅沃爾夫岡·博爾歇特的文學研究基本上還構不成完整的體系,僅有一篇核心論文發表于1984年,其主要內容是對戲劇《在大門外》的主題和主要人物形象進行分析。七篇一般期刊論文也主要針對戲劇《在大門外》和幾篇著名小說《老鼠夜里是睡覺的》《面包》和《廚房鐘》結合作者的經歷進行內容和主題方面的剖析。國內碩博論文方面,僅有五篇相關碩士學位論文。其中三篇碩士論文主要是結合話劇《大門之外》及其他幾部作品對其中的戰爭主題和反戰主題進行了分析;后兩篇碩士論文中第一篇主要是對沃爾夫岡·博爾歇特在其敘事三部曲中展現的城市意象。而第二篇碩士論文只在第一章分析博爾歇特等幾位德國作家的“廢墟文學”作品的三大表現主題。因此,對于博爾歇特作品的研究仍然有較大的發掘空間和意義。本文在形象學視域下以博爾歇特文學作品作為研究對象,從其戲劇以及短篇小說的文本中梳理歸納出兩種德國形象:戰爭中的德國和廢墟中的德國。這兩種形象涵蓋了博爾歇特不同題材的文本對于20世紀30-40年代德國形象的表述。以這兩類德國形象的角度可以較好地概括博爾歇特文學作品塑造的“德國形象”的性質,從中可以分析博爾歇特在二戰時和二戰后對德國多維度的反思視角、樣式和表述策略。
2博爾歇特作品中的德國形象
2.1戰爭中的德國
被囚禁、喪失自由,似乎彌漫在博爾歇特的文學表達之中,這種表達是由一種不容忍個人自由的制度強加而來的。博爾歇特曾經在給親友和導師的信件中,公開批評納粹德國政府,這進一步表明他無法抑制自己對納粹政權的反感和反對。在納粹德國統治時期,政府將其控制范圍擴展到了德國社會生活的每一個階段,從報紙、書籍、電影、廣播、到教育以及信仰。在納粹政府統治時期,高達97%的中小學教師是納粹教師協會成員,甚至37%是納粹黨正式成員。納粹在德國掌權不久,就迅速開始了宗教控制的一系列行動。在1938年,納粹德國的所有學校就被禁止播放圣誕頌歌和圣誕劇。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圣誕節一詞在納粹德國被正式禁止。因此,很明顯的,生活于1933年至1945年期間的德國人所經歷的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都很大程度上被嚴密控制著。這是一個沒有其他政黨可供選擇的社會,生活的每個階段都有納粹的印記,無論是學校、教堂還是工作,人們讀的報紙新聞,聽的廣播,看的電影、戲劇,送孩子去的學校,做禮拜的教堂,在納粹德國的社會里,沒有人有自主的存在。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受到納粹極權的統治,整個民族、整個國家都被重組,所有人在所有可能的情況下,都要穿上統一的制服。任何不愿意服從這個制度的人,都會被強迫進入這個制度或者最終淪為被強迫的沉默者。這種對生活方方面面的嚴密控制以及博爾歇特自己在納粹德國的親身經歷,使他將戰爭中的德國社會看作是一座可怕的監獄。
在《一個周日的早晨》中,硬硬的皮質警帽邊將獄警的腦袋勒出了深深的皺紋,在不可違背的執勤規章中,帽邊必須和這條皺紋嚴絲合縫搭在一起,這是士兵服從命令的象征;監獄里的大多數人喪失了自己的個性,失去了人情味,表現出的是聽命與服從。只有三個被囚禁的人徒勞的以自己的方式在抗爭,雖然最終都只是以失敗告終。這種監獄和監獄生活證明了一個世界變得荒謬的景象,人只不過是一個數字,被剝奪自由的人,在牢房門后的孤寂中,只能或是對著空蕩蕩的空間呆坐,或是機械、重復地撕掉34張廁紙,或是思念著家人無助絕望地哭泣。博爾歇特在《瑪利亞,一切都是瑪利亞》中則通過一個波蘭籍天主教徒和他虔誠信仰的圣母瑪利亞畫像,以隱喻的方式展示了極權政府對公民生活的負面入侵,公民失去了與正常生活和現實世界的所有聯系以及經歷過納粹德國極權政府控制的人是如何被孤立的過程。
在《這個星期二》系列的八個故事中,博爾歇特揭露了戰爭的殘酷現實,不僅譴責了強迫人們參與戰爭的納粹政權,而且還譴責了戰爭本身。故事中的小女孩在學校里必須學會書寫戰爭和坑道(壕溝)這些與戰爭有關的詞匯,必須重復讀寫十遍以此熟知“所有的父親都是參戰的士兵”;中小學校的老師必須讓學生認識和了解自己的生活與戰爭的緊密聯系;前線的士兵必須服從命令、勇往直前,不畏死亡;后方的平民們必須全身心投入和奉獻于和戰爭相關的各個領域。博爾歇特筆下的德國社會不僅受到高度的支配和控制,而且還彌漫著一種普遍的情緒——恐懼。制造恐怖、散布恐怖是納粹極權政府的一種極其有效的控制手段。《夜鶯唱歌》中的孤獨哨兵提姆在站崗時因為恐懼而自言自語甚至模仿夜鶯唱歌,隨即就被上級因為其不受控制、不聽(閉嘴)命令槍殺;在《貓在雪地里凍僵了》中,納粹政府簡單粗暴的對一個又一個的村莊發起了戰爭與屠殺,這種暴力手段帶來的恐懼彌漫在村莊與民眾之間。恐懼讓村民們只能靜靜地在黑夜里看著屠殺與焚燒進行著,只剩亡魂慘叫嘶嚎。
博爾歇特的文學作品中描述了人在戰爭中從事的生存和破壞的行為。但是作者在對這些人的刻畫并不是他自己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經歷所獨有的。相反,這些故事描繪了所有人在所有戰爭中的共同痛苦,并通過暗示和隱喻,譴責戰爭本身的罪惡。博爾歇特在作品《保齡球道》中講述了兩個士兵在壕溝中射殺了無數他們根本不認識的人,從未傷害過他們的人,并且還因為會有獎賞而感到開心,甚至覺得好玩。他們射殺的人頭多到可以堆成一座大山,而那些人頭多到四處滾動,如同保齡球在保齡球道上滾動一樣。被滾動聲吵醒的兩個士兵在聊天中承認自己實際上是在玩這種令人毛骨悚然的死亡游戲,甚至還覺得挺好玩。作者在這里展現出了戰爭中人性的淪喪。而《四個士兵》中,四個由木頭、饑餓、泥土、暴雪、鄉愁和胡須組成的士兵在戰壕中服從不可違背的命令,在紛飛的炮火中,在異鄉戰場上,失去了人性,麻木冷漠地堅守著陣地,則表現出參與戰爭的人們機械地像保齡球、泥人或木偶一樣活著,在一個荒謬和破壞性的游戲中被戰爭、被罪惡操縱著。
2.2廢墟中的德國
通過對戰后德國日常社會生活中物質與精神方面的藝術感悟進行撰文,博爾歇特試圖提醒那些后來者戰爭固有的愚蠢。正如《在大門外》的主角貝克曼在俄國前線受傷的膝蓋和防毒面具不斷地提醒著他和周圍的人一樣,博爾歇特筆下廢墟中的德國和精神殘疾的人物都在提醒人們:“這些紀念館很好,否則你會很快忘記戰爭”。無論是毀壞的建筑物還是精神崩潰的人物,往往都是一種更深刻的精神崩潰的癥狀。博爾歇特見證了也描繪了德國這種精神崩潰的過程。如《廚房鐘》中長著一張非常蒼老的臉的二十歲年輕男人抱著一個停擺在兩點半的廚房鐘在廢墟中向其他人講述關于他手中的廚房鐘的故事。廚房鐘上的兩點半曾經是年輕人深夜回家的時刻;曾經是年輕人的母親守門并在廚房給他做吃食的時候;卻是年輕人在戰爭中(轟炸中)失去父母與家園的時刻;也是戰爭帶給人們身心劇痛的時刻。周圍人們或冷漠麻木或感同身受的表現,則展現了戰爭給人們帶來了共同的無法磨滅的苦難折磨。《櫻桃》中生病的孩子誤會父親偷吃了來之不易的櫻桃而產生了委屈不甘、懷疑怨懟的情緒。新鮮櫻桃實際上并沒有被吃掉,父親被染紅的雙手是因為長期忍饑挨餓導致頭暈眼花、手腳無力,不小心在上臺階的時候打碎了杯子受傷所致。盡管被孩子埋怨誤會,可父親還是一如既往的向孩子表達了愛意。孩子的自私、羞愧和父親的無私、寬容展示了戰后德國普通民眾的困苦生活以及家庭親情關系在這種環境下面對的危機和困境。
理解戰爭的真正非人性化的一個方法就是去研究戰爭對于那些參與戰爭并從戰爭中歸來的人的影響。如《在大門外》的主角貝克曼和《烏鴉晚上飛回家》中蒂姆以及他的朋友的見聞感觸和遭遇均展現了戰后大多數德國歸鄉士兵的境遇——無家可歸、無處可去、無處容身的絕望和痛苦。博爾歇特的文學作品中很少直接出現戰爭這個詞語,更不用說具體提到第二次世界大戰了。博爾歇特試圖在他的文學作品中傳達希望的信息,在黑暗之中投射一道光芒,照亮人類的生活。博爾歇特的文學作品也反映了對愛與希望的肯定,如在《城市》中夜里月光下美麗的銀色鐵軌通向天際一道亮色——漢堡。趕路的夜行者充滿對新生活的憧憬,帶著堅定的決心:生活的確有著無盡的恐懼,但是也有著讓人向往和渴望的,向著天際那個明亮的斑點——城市大步而去。在黑暗中投射出一道光芒,這就是人類生活的希望。在《面包》中,戰后資源匱乏、食物緊缺,沒有吃飽的丈夫深夜在廚房偷吃面包發出了聲響,被妻子發現后驚慌失措下撒了謊企圖蒙混過關。妻子對丈夫和對家庭的愛意,讓她幫著狼狽不堪的丈夫圓謊并且還撒了自己不太能吃面包的謊,只是為了讓饑餓的丈夫能夠吃飽,為了這個家庭能夠繼續維持下去。在《三個黑暗國王》中,三個戰后歸鄉、身心俱疲且帶殘疾的士兵如同耶穌誕生傳說中從遠方而來的三位圣人一樣,留下了他們當時最珍貴的東西:煙草、一只木雕驢子和兩塊黃色的糖,作為充滿愛意的禮物與祝福,贈予黑暗的城市廢墟之中新生的嬰兒——博爾歇特筆下的希望與生命的象征。在《夜里老鼠們要睡覺》中,小男孩尤爾根獨自一人睡在廢墟邊守護著小弟弟的遺體以此避免被老鼠啃食。一位路人通過一個善意的謊言——贈送一只白色小兔子,帶領小尤爾根從死氣沉沉、充滿戒備的灰色悲傷世界走出來,回到陽光明媚,充滿希望、信任、生命和活力的綠色世界。
3結語
博爾歇特的文學作品被稱為對戰爭的宣戰和抗議,同時也是一種警告,其目的是避免納粹德國或任何類似的事情在任何地方重演。這些文字都是揭露社會錯誤的一種手段,并且是作為喚醒那些追隨這種社會錯誤的危險意識的一種范例。作家的職責讓博爾歇特必須為他所經歷的20世紀20-40年代德國的社會現狀發聲,他在文學作品中警告道,在國家和世界事物之中,不反思、不批判的人性具有可怕的破壞性。
基金項目:本文系吉安市社會科學研究項目課題“形象學視域下的博爾歇特文學作品的德國國家形象研究”(21GHC393)的研究成果。課題負責人:李婷婷
參考文獻
[1]狄澤林克.比較文學形象學[J].方維規,譯.中國比較文學,2007(3): 152-167.
[2]鞏志華.文學視域下的國家形象研究[J].前沿,2016(4):14-19.
[3]帥巍巍.文學作品中的中國國家形象及其當下構建[D].江西:江西師范大學,2011:12.
[4]沃爾夫岡·博爾歇特.夜里老鼠們要睡覺[M].任衛東,邱袁煒,譯.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7:1-8,33-43,59-69,77-83,94-98,121-126, 179-182, 219-228.
[5]沃爾夫岡·博爾歇特.在門外[J].王星,譯.戲劇(中央戲劇學院學報),2006(3):108-148.
[6]WolfgangBorchert. DasGesamtwerk[M].Reinbek:Rowohlt,2007:61.
[7]馬修·休茲克里斯·曼鐵血與面包:第三帝國社會生活史[M].于倉和,譯.北京:中國市場出版社,2018:49-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