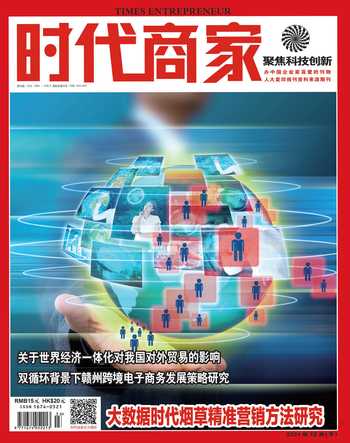可持續(xù)發(fā)展背景下農產品綠色包裝的作用、問題和對策
黃楨 李蔓熠
摘要:隨著“十四五”規(guī)劃的持續(xù)推進,可持續(xù)綠色經(jīng)濟已經(jīng)成為經(jīng)濟模式轉型的重要方向。本文分析了可持續(xù)發(fā)展背景下農產品綠色包裝的作用、問題和對策,提出農產品綠色包裝有助于宣傳可持續(xù)發(fā)展理念、確立綠色化的競爭優(yōu)勢、滿足消費者的審美需求、凸顯地方文化特色等觀點,而當前農產品包裝存在可持續(xù)發(fā)展意識薄弱、包裝設計缺乏特色、忽略包裝延續(xù)性功能的問題,本文結合了秸稈雞蛋托包裝的案例,提出我國農產品綠色包裝要增強農產品包裝的可持續(xù)發(fā)展意識,培養(yǎng)農產品包裝的設計理念,實現(xiàn)農產品包裝材質的延續(xù)化。
關鍵詞:農產品;綠色包裝;綠色環(huán)保;自然生態(tài)
根據(jù)我國“十四五”的規(guī)劃綱要,碳達峰已經(jīng)被納入可持續(xù)綠色經(jīng)濟體系的行動方案中,我國發(fā)改委、國務院、生態(tài)環(huán)境部相繼印發(fā)了《關于促進應對氣候變化投融資的指導意見》、《關于加快建立健全綠色低碳循環(huán)發(fā)展經(jīng)濟體系的指導意見》等文件,這也說明低碳環(huán)保已經(jīng)得到較大配套性政策的支持,這也顯示了“綠水青山”對建設下一個全新小康社會的重要性。今年3月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在低碳環(huán)保和科技創(chuàng)新領域發(fā)表過多次重要講話,在中央財經(jīng)委員會第九次會議、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九次集體學習中,習總書記強調了碳達峰和碳中和對于新經(jīng)濟發(fā)展的重要性,并提出在2030年要達到碳達峰和碳中和目標,而科技創(chuàng)新是企業(yè)完成綠色低碳經(jīng)濟轉型的關鍵路徑。
可以看出,低碳、綠色、環(huán)保、可持續(xù)等理念已經(jīng)成為下一個五年規(guī)劃的重心,這也對經(jīng)濟、社會、商業(yè)、生活等方面產生了深遠影響(羅欣,2019)。一直以來,農產品都是我國鄉(xiāng)村經(jīng)濟的重中之重,可持續(xù)發(fā)展觀也在不斷滲透到農產品生產、流通和銷售的各個領域,隨著我國對低碳循環(huán)經(jīng)濟的重視力度提升,在農產品包裝設計領域也開始被逐步關注,綠色環(huán)保包裝既反映了農產品行業(yè)接軌低碳經(jīng)濟,滿足國家對綠色生態(tài)的要求,也能作為文化習俗、地域特色、精神內涵、和諧健康等概念的載體(宋曉丹,2020)。從某種意義來看,農產品綠色包裝可以同時將地域文化和綠色生態(tài)理念融入到社會大眾,從精致的綠色環(huán)保包裝來顯示出視覺美感、品牌賦能和綠色形象,這也有利于我國農產品的全球化發(fā)展(顧志星,2019)。因此,本文探討了農產品綠色包裝的作用、問題和對策,并借助秸稈包裝盒的案例來探討其可行性,希望能幫助我國農產品包裝的綠色化、低碳化和循環(huán)化升級。
一、當前我國農產品綠色包裝的問題
(一)可持續(xù)發(fā)展意識薄弱
長期以來,我國農業(yè)企業(yè)都不注重產品的包裝營銷,過度信奉“質量好才賣得好”,沒有認識到可持續(xù)發(fā)展的趨勢,也就沒有形成生態(tài)和諧、環(huán)境保護、綠色自然的意識,所以在包裝設計上盡可能降低成本,只考慮農產品損耗率、運輸費用、倉儲成本等,并沒有考慮過農產品的包裝材料設計。因此,大量農產品企業(yè)仍然在使用塑料袋、泡沫箱等污染材料,這也給鄉(xiāng)村生態(tài)帶來一定的影響,不符合綠色可持續(xù)發(fā)展的基本理念。另外,在一些高端農產品的市場營銷中,經(jīng)營中也過度講究農產品包裝的“面子”作用,所以采用了過于奢華的包裝材質,這也違背了可持續(xù)發(fā)展的初衷。
(二)包裝設計缺乏特色
包裝設計在產品市場營銷中扮演了吸引消費者注意力的角色,包裝設計也是農產品讓消費者記住品牌的重要舉措,但是鄉(xiāng)村農產品普遍缺乏現(xiàn)代化設計能力,各大農產品的包裝方式過于同質化,彼此之間相互模仿或抄襲,缺乏與眾不同的特色,不但沒有反映綠色環(huán)保的信息,更缺乏設計美感和文化底蘊。具體而言,農產品包裝環(huán)節(jié)是依靠縣城里的企業(yè)、工廠、作坊等小型組織來完成,流程環(huán)節(jié)都是流水線式、照片嵌套式的印刷,這類組織也同時承接農副產品、工業(yè)品等的包裝,所以包裝工藝并不能凸顯出農產品的特色。舉例來說,地域文化是農產品包裝的特色競爭力,但是大部分農產品企業(yè)并沒有重視這一特色,不注重這一特色與可持續(xù)發(fā)展理念的融合,這也造成品牌包裝設計混亂不堪。
同時,隨著城鎮(zhèn)化的發(fā)展,城鄉(xiāng)就業(yè)環(huán)境、基礎設施、政策支持和社保條件都有較大差距,農村地區(qū)人才不斷涌向城鎮(zhèn)地區(qū),這造成農村地區(qū)的設計人才貧乏,難以吸引城鎮(zhèn)地區(qū)的專業(yè)人才,鄉(xiāng)村農產品的包裝設計也是停滯不前。就算是將鄉(xiāng)村農產品包裝設計外包到城鎮(zhèn)地區(qū),而城鎮(zhèn)人才也不了解當?shù)氐霓r產品特色,也無法設計出有特色的包裝。
(三)忽略包裝延續(xù)性功能
在可持續(xù)發(fā)展理念的農產品包裝設計中,應當考慮包裝材料的延續(xù)性功能,即循環(huán)經(jīng)濟。換而言之,循環(huán)經(jīng)濟要求包裝不僅僅起到呈現(xiàn)商品信息和保護商品的功能,還應當為包裝的延續(xù)性處理提供解決方案。但目前,由于我國鄉(xiāng)村農產品產業(yè)鏈的發(fā)展較為滯后,農產品深加工水平?jīng)]有達到全面支持綠色包裝的水平,仍然存在大量塑料包裝生產的產能,同時成本價格也較為低廉,這也進一步讓農產品包裝設計陷入經(jīng)濟利益的博弈,仍然有大量經(jīng)營者會選擇污染材料作為包裝材料,不少企業(yè)甚至為了降低包裝成本、提高產品運輸損耗率而添加增塑劑、防老劑、重鉛、重油墨等,這不僅不符合可持續(xù)發(fā)展的理念,更是會對居民的飲食安全和身體健康帶來不利影響。
二、農產品綠色包裝的案例分析
(一)企業(yè)介紹
秸秸高農產品內襯包裝有限公司的總部位于上海市浦東新區(qū)川宏路365號,企業(yè)針對當前市場中綠色包裝的痛點問題而開發(fā)了可回收、可降解的雞蛋托包裝產品,目標市場是高品質高價雞蛋的包裝需求,最終市場是愿意為高品質雞蛋承擔高價格的城市居民,企業(yè)采用秸稈作用農產品包裝材料,利用秸稈作為原材料,將農田秸稈磨碎后以滴膠(糯米膠)固定成型,生產一種無毒無害、透氣性佳、防震環(huán)保無污染的雞蛋包裝盒。
(二)秸稈包裝的優(yōu)勢分析
1.成本低、取材廣
秸稈材質包裝原材料是秸稈,其競爭品材料是塑料泡沫、廢紙、化學原料等,相比來看,秸稈是來自農作物種植的副產物,農作物光合作用的產物有一半以上存在于秸稈,成本相對較為低廉,可以輕易采購得到。同時,秸稈在包裝的循環(huán)利用也符合了循環(huán)經(jīng)濟的特性。
2.無毒無害無污染
由于秸稈是一種多用途的可再生的生物資源,成分中有大量的粗纖維,過去農村還用于羊、牛等牲畜的飼料,廢棄后降解效率較高。相比之下,聚乙烯、聚丙烯等材料不易降解,紙漿的制作和廢棄后仍然有一定污染,降解速度不夠快。秸稈并非是人工制品,相比其他材質有更大優(yōu)勢。
3.透氣性強
秸稈是一種粗纖維含量達到30~40%的農作物,透氣性較強,可以滿足農產品的保鮮需求,降低農產品流通的損耗率,改善銷售網(wǎng)點中的農產品品質。
(三)秸稈包裝的環(huán)保特色
1.體積小
秸稈雞蛋盒包裝機的體積小,對場地要求不嚴格,解決了其他設備體積大、不適用于家庭的問題,其體積和占地上的優(yōu)勢使得應用范圍更廣。
2.流程少
秸稈雞蛋盒包裝機操作步驟較為簡單,只需將秸稈放入打碎后等待機器加工,待機器加工完成后將雞蛋盒拿出即可。競爭對手的雞蛋盒包裝機由于特殊的工藝,具有較為復雜和專業(yè)化的流程,操作復雜、工序步驟更多。
3.環(huán)境污染低
競爭對手設備耗能較大,對于水力電力的消耗遠大于秸稈雞蛋盒包裝機。同時本設備采用針頭注膠方式,將針頭插入秸稈碎內,快速完成注膠,確保配比,安全可靠,也降低了秸稈焚燒的可能,加強了廢棄秸稈的利用率,對環(huán)境污染低。
三、我國農產品綠色包裝的發(fā)展對策
(一)增強農產品包裝的可持續(xù)發(fā)展意識
首先,農產品企業(yè)需要建立可持續(xù)發(fā)展意識,通過內部培訓、參與講座、網(wǎng)絡課程等形式來學習國家可持續(xù)發(fā)展的理念,并了解綠色包裝的前沿理論和技術,提高對可持續(xù)包裝的重視和認知,通過理論、案例、實地考察等方式深入了解傳統(tǒng)包裝對資源污染、生態(tài)和諧、經(jīng)濟轉型、生活健康等方面的危害,將“碳達峰”“碳中和”納入到企業(yè)未來的發(fā)展規(guī)劃。同時,企業(yè)管理人員也要將包裝綠色環(huán)保作為首要戰(zhàn)略,主動放棄塑料包裝的蠅頭小利,將眼光放得更加長遠,在包裝中反映綠色環(huán)保的信息,將企業(yè)可持續(xù)發(fā)展理念貫穿到包裝設計之中,在市場中呈現(xiàn)低碳綠色環(huán)保的品牌形象,保障品牌能在一、二線城市的未來市場份額。
在包裝設計中,也要避免過度注重浮華、奢侈和高檔的元素,在包裝中可以考慮使用可循環(huán)利用的環(huán)保材質。在包裝設計上,表現(xiàn)出企業(yè)抵制資源浪費、高污染材質的決心,并向消費者宣傳可持續(xù)的包裝理念,讓消費者認同綠色包裝的積極價值,傳遞新包裝安全健康的理念,提高消費者對品牌的肯定評價,從而否定傳統(tǒng)污染包裝,減少消費者對環(huán)保材質包裝的誤解。
(二)培養(yǎng)農產品包裝的設計理念
綠色環(huán)保和設計美感的融合依賴于設計師的專業(yè)能力,這也要去企業(yè)培養(yǎng)農產品包裝的設計理念,才能將美學賦能于農產品包裝中。為了避免出現(xiàn)同質化的綠色包裝問題,農產品企業(yè)應當聘請專業(yè)設計師來專門設計一套包裝方案,將綠色生態(tài)融入本土風氣、歷史人文和地方民俗中,并發(fā)揮出環(huán)保包裝的時尚感,加強品牌的設計感。舉例來說,設計師可以根據(jù)農產品物理特征來設計一套農產品環(huán)保包裝,材質上選擇和農產品相關、契合的種類,為農產品講好一個“故事”。與此同時,企業(yè)可以利用各種材質、顏色或圖案來構成藝術造型,利用立體材質來描繪當?shù)靥赜械奈幕⒚袼椎葍热荩x予包裝鮮活特性,引發(fā)和加深消費者的興趣和印象,讓消費者對地方特色產生好奇心,提高農產品品牌的忠誠度。
(三)農產品包裝材質的延續(xù)化
包裝延續(xù)性關注到了包裝材質和設計的易降解、循環(huán)利用等特色。對此,本文建議要選用綠色的包裝材料,根據(jù)當?shù)氐姆煞ㄒ?guī)來選擇低污染的材料,避免包裝材料成為白色污染的源頭,比如選用生物制包裝材料,如秸稈、竹、柳條、瓦楞紙等,這類包裝材料直接來自大自然,滿足無毒、無公害、無污染的要求,這也能達到“取之自然,用之自然”的效果。另外,也能采用草、竹、貝殼等傳統(tǒng)材料進行包裝,體現(xiàn)地域歷史特色,在包裝中引導消費者對民族歷史的認同感和歸屬感,這也賦予中國農產品與眾不同的特色。
參考文獻:
[1]羅欣.生態(tài)文明視閾下龍虎山綠色農產品包裝設計研究[J].藝術品鑒,2019(02):267-268.
[2]宋曉丹.自然元素在農產品包裝設計中的應用[J].農家參謀,2020(14):263.
[3]顧志星.新疆農產品品牌營銷策略探析[J].北方經(jīng)貿,2019(01):76-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