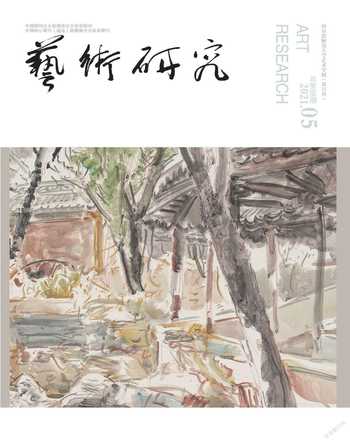“有意味的形式”與情感的表現:論貝爾的藝術理論
趙梓銘
摘要:英國美學家克萊夫·貝爾(Clive Bell)在1913年出版的著作《藝術》(《Art》)中提出了“有意味的形式”這一概念,并以此概念為中心構建了自己的藝術理論體系,論證了藝術的本質、藝術創作的原則和藝術史發展等問題。該理論產生了很大的影響,一方面是因為它被認為很好地解釋了現代主義藝術,另一方面是因為它代表了一種極端的形式主義理論。實際上,后一種對貝爾理論的理解是一種誤讀,貝爾的理論并不是一種形式主義理論,他所關注的核心問題是藝術家的情感表現。
關鍵詞:有意味的形式 形式主義 形式 表現論情感表現
貝爾在《藝術》一書中的理論在近現代西方藝術界產生很大影響,一方面是因為它被認為很好地解釋了現代主義藝術,另一方面是因為它代表了一種極端的形式主義理論。以往的研究認為貝爾所提出的概念“有意味的形式”,意味著藝術的本質在于色彩和線條的組合方式,同時排斥再現性藝術,即類似于畢達哥拉斯學派的理論,認為藝術的本質是比例和諧。實際上,這是對貝爾理論的一種誤讀,貝爾的理論并不是一種形式主義理論。
貝爾提出了兩個核心概念,審美情感(Aesthetic Emo-tions)和“有意味的形式(The Significant Form)”,并從兩個方面闡釋了他的觀點,一方面,他運用“有意味的形式”這一概念,來解釋欣賞者的審美接受問題,即通過對作品的欣賞獲得審美情感。另一方面,他提出:藝術作品是藝術家審美情感的表現,藝術作品之所以感動我們是因為它表現了藝術家的審美情感。這樣欣賞者就有兩條獲得審美情感的路徑,本文通過分別考察這兩方面,來研究貝爾如何建構起他的表現論美學。
一、有意味的形式
若要理解貝爾的理論,首先要從“形式”這一概念出發。“形式”通常具有以下兩種不同的含義:在“內容與形式”這一對辯證關系中,通常將美術作品的主題理解為內容,將作品的部分理解為形式。而在另一種理解中,將畫面中的色彩、線條等的組織方式理解為形式,如在畢達哥拉斯學派的理論中,認為美是數的和諧,如黃金分割理論。這兩種理解的不同之處在于,前一種理解認為作品的一部分物理性質(色彩、線條等)是形式;而后一種理解認為,色彩或線條之間的組織關系是形式,相較于前一種形式所具有的物理性質而言,后一種形式是一種抽象關系,通常將其稱為“形式美”。而這兩種不同的理解也將引導出不同的藝術觀念,前一種理解在堅持“內容與形式的辯證統一”中踐行著傳統具象美術,而后一種理解則會引導出拋棄具象內容的抽象藝術和藝術設計。而貝爾在解釋“有意味的形式”這一概念時稱,“線條和色彩以特定的方式組成確定的形式和形式之間的關系,它們激起了我們的審美情感”1。在這一段論述中,貝爾的闡述是模糊的,如果形式指的是前述的第一種理解,那么形式之間的關系指的就是后一種理解,這樣貝爾對形式概念所界定的范圍就會相當地大。這需要從貝爾的其他論述中著手。
審美情感和有意味的形式是貝爾理論的核心概念。貝爾認為有意味的形式是能夠引起審美情感的形式。審美情感和宗教精神具有相同的含義,就是把一個物體看作是它的目的本身
(As Ends in Themselves)時所產生的感受。把一個物體看作是它的目的本身也就是把物體看作是純形式(Pure Forms),純形式指的是不涉及功利性的、信息性的、工具性的形式,與之相反的是把物體看作是手段,如通過作品傳達信息。“有意味”一詞在原著中以“Significant”表示,指“重要的”“重大的”“有意義的”,如“參加了一次有意義的學術研討會”。是指藝術形式是一種有意義的形式,它的意義就在于能夠使人獲得審美情感。本文認為將“significant”譯作“意味”并不準確,“意味”在中文中有趣味的含義,與原意并不相符,但為了便于閱讀,本文仍將其寫作“意味”。
貝爾是一個虔誠的宗教信徒,他認為藝術和宗教是兩個呈現宗教精神的載體,它們共同所達到的目標——宗教精神——就是把一個物體看作是它自身的目的,他稱之為“終極現實”(Ultimate Reality),他認為一個物體最本質的意義就是它的現實意義(指存在意義,而不是現實主義理論中的批判性意義),而對現實意義的捕捉靠的是對物體的沉思行為(Con-templation),即冥想,這也就是藝術家獲得審美情感的方法。然而這種沉思并不一定需要物體在場,藝術家可以通過想象或回憶等多種方式進行沉思。這樣藝術家就通過沉思進入迷狂(Ecstasy)的狀態,也就獲得了宗教精神。
由此可知,審美活動的核心不是物體的形式如何,而是看待物體的態度。貝爾沒有通過描述特定的審美對象來定義形式,而是通過看待形式的態度來定義形式,這本身就是反形式主義的。如果一個人可以把任何一個物體都能看作是純形式,那么他就具有很強的獲得審美情感的能力,也就是沉思的能力;反之則不然。貝爾認為,藝術家和普通欣賞者獲得審美情感的能力是不同的,只有最純粹的形式能使普通欣賞者獲得審美情感;而藝術家能通過任何一個物體獲得審美情感,因為他們有能力排除出功利性的因素,只把物體看作是純形式。
雖然“最純粹的形式”這一段表述容易讓人理解為貝爾在肯定只有抽象形式才是純形式,但是他的其他論述推翻了這個可能。他認為一件藝術作品可以具有再現性因素。因為平面藝術具有三個要素,形式、色彩和空間感。前兩者都可以成為非再現性因素,但平面藝術中的空間感必然是一種再現性因素,因為它再現了三維空間2。貝爾認為這種三維空間雖然是可有可無的,但如果把一幅繪畫看作是平面的,就喪失意味了。這表明貝爾更傾向于在繪畫中保留有三維空間,同時他對塞尚作品的評論也具有這層含義。他認為音樂家和建筑師所創作出的作品是抽象的,是僅僅憑借想象就可以達到現實感的典型,他們的作品中所含有的僅僅是宇宙中事物的物理存在;而塞尚不是這類藝術家,他的藝術從美術傳統中發展而來,他需要一種有形的支點來探尋有意味的形式,因此他沒有創作出純粹抽象的形式。“有形的支點”指的就是塞尚作品中的再現性因素,貝爾和弗萊的藝術理論以捍衛后印象派繪畫為目的,而后印象派繪畫都屬于具象繪畫,這一點是完全被貝爾所包容的,他并不認為這些再現性因素和“有意味的形式”相矛盾。
除此之外的再現性因素,如具象的物體,也是可以出現在畫面中的,但最重要的是普通欣賞者不應該過多注意這些再現性因素,因為過多的信息會分散普通欣賞者的注意力,使他們無法把作品看作是純形式——也即進入迷狂狀態。這就表明一個形式是否是純形式取決于觀賞者自身的沉思能力,而不取決于作品。而貝爾提出要控制作品中的再現性因素,是為了迎合普通欣賞者的審美水平而做出的調整,并不是具有普遍性的藝術法則,因此并不能說明貝爾反對再現性藝術。
貝爾在解釋“線條和色彩的組合”其含義時稱,“形式”包含著線條和色彩,而線條和色彩是相互依存的,即線條一定是有某種顏色的線條,而色彩一定是成某種形狀的色彩,在這部分,線條是形狀的概括。在油畫當中,畫的邊界之內一定有內容,而內容一定是被畫面的邊界所框定的,貝爾用這樣一連串的舉例來說明,線條和色彩的組合指的是作品邊界之內的一系列事物,也就是物理意義上的作品,也即形式3。因此,回到貝爾對“有意味的形式”這一概念給出的定義中,“確定的形式和形式之間的關系”是相對于作品的內容、即再現性因素來談的,而不是相對于“另一種形式和形式之間的關系”來談的。如果把這句話補全,應該是“激起我們審美情感的是作品的物理性質(即現實意義、存在意義),而不是作品的內容(主題)”。只有這樣理解,上下文的邏輯才是通順的。
在欣賞時排除了再現性因素后,是否就一定能得到藝術作品了呢,貝爾的答案是否定的。貝爾認為“有意味的形式”之所以能夠打動我們,是因為它傳達了創作者的情感;而自然物不能打動我們是因為它們沒有傳達任何東西,因為它沒有作者。例如蝴蝶的翅膀,它是美麗的形式,但不是“有意味的形式”4。同時,在對中世紀建筑的論述中,貝爾贊揚了羅馬式和諾曼式建筑氣勢恢宏,抨擊了哥特建筑,認為它們以顯示高超的建筑技巧為目的,只是一種雜耍5。若是以一般的形式主義觀點來看,哥特式教堂的建筑形式相當地突出,火焰式的尖塔、成比例的肋拱、以及彩色玻璃窗都顯示出其在建筑過程中所注入的形式美元素,但貝爾卻并不為之所動,因為他所關注的是藝術家傳遞出的情感,而不是這種裝飾性。
因此,貝爾的理論存在著這樣一個邏輯過程,在第一階段,他認為藝術的本質不在于模仿對象,而在于作品的形式本身,應該排除作品的功利性;在第二階段,他認為作品的形式之所以能夠引起觀眾的審美情感,是因為傳遞了作者的審美情感。但在這之中,藝術家和觀眾的區別在于:對于藝術家來說,事物本身并無所謂是否是藝術品,它們都可以成為藝術品,因為藝術家有能力對任何事物產生審美情感。而對于觀眾來說,自然物由于本身沒有作者,沒有情感被傳遞出來,因此無法成為審美對象。這是由于觀眾的審美能力相對較低導致的。因此這就賦予了藝術家一個創造能被觀眾審美能力所接受的藝術作品的任務,在這個過程中,藝術家具有顯而易見的主導地位。
綜上所述,貝爾對“有意味的形式”這一概念的解釋并不是循環論證。他提出“有意味的形式是能引起審美情感的形式”,但是并沒有用“審美情感是由有意味的形式引起的情感”這一命題來解釋審美情感,而是用“把一個事物看作是它自身的目的”這一命題來解釋審美情感,對審美情感的論證并沒有建立在前一個命題的真實性之上。
二、審美情感的表現
在貝爾研究的第二方面,他從藝術家的角度來闡釋審美情感:藝術家進行創作的目的是表現自身的審美情感,將他的審美情感物化,而不是為了引起觀眾的審美情感6。在這一部分,貝爾認為藝術活動是藝術家情感的表現,這和表現論美學的觀點是一致的。克羅齊認為,藝術活動就是直覺活動,心靈通過直覺活動給材料(感受)賦予形式,這才成為心靈的內容。如果材料沒有被直覺到,它就處在直覺線之下,那么它就還不是心靈的內容,只能假定它們存在。他也將直覺稱為“形式”,這使人認為他混淆了直覺和作品形式之間的區別,這是因為他采用了“形式”一詞的另一個含義。在亞里士多德的理論中,事物都是由質料和形式構成的,如一個大理石人像,大理石是它的質料,人的形態是它的形式,形式起到的作用是給質料賦予形式。克羅齊采用的不是后來美術史研究中使用的,存在于作品中的形式,而是作為哲學意義上的形式。
在科林伍德的三個層次理論中,他認為高一水平的經驗并不是取代了低一水平的經驗,如意識水平中的情感并沒有取代心理情感,而是以一種疊加的狀態附加在它的上面。這就說明在審美情感當中包含了主體對客觀事物最初的反映,同時,在理智活動中也囊括了意識水平階段產生的審美情感。這表明表現理論并不排斥再現性,它是包含了再現性,是再現性理論的發展。7在再現性理論發展到一定階段時,理論家發現再現并不能定義藝術,因為有非再現性藝術存在,于是他們想要將這兩種藝術進行調和,統一在一個更高一層級的藝術理論之下,于是就出現了表現論。這樣就可以解釋為什么貝爾的理論不排斥再現性因素,實際上他所推崇的藝術都是再現性藝術,如塞尚的作品和中世紀的拜占庭藝術,他所反對的是把再現性因素等同于藝術。同時,由于審美情感本質上是一種意識活動,因此和表現理論的立場一樣,作品對于藝術活動是可有可無的,起到的是一種工具性作用,是對頭腦中藝術活動的記錄,它記錄的是頭腦中被賦予形式的心靈內容。
綜上,這種“表現”并沒有明確的接收客體,科林伍德在他的理論中也指出,表現情感和通過作品引發觀眾的情感是兩回事8,那么欣賞者在欣賞藝術作品的過程中如何獲得審美情感就值得考察。
三、欣賞者的審美活動
由于欣賞者的審美能力有限,他們不能欣賞自然物,只能把藝術家的作品當做審美對象,在這個欣賞過程中產生了兩種
邏輯,第一種是把藝術作品當作它自身的目的來看待,也就是
純形式;另一個是把藝術作品當作是藝術家自身情感的傳遞中
介來看待,根據貝爾的理論這兩種說法都成立,那么它們之間
有什么聯系呢。
貝爾認為藝術作品之所以讓欣賞者產生審美情感是因為它表現了藝術家的審美情感9。同時,藝術家用以表達自身情感的形式,并不能通過外觀來判斷它是否是由藝術家的審美情感所創造的10,這說明藝術家的審美情感無法體現在作品的形式上。貝爾舉例稱,兩個外觀相同的藝術作品,如一個是原作,一個是復制品,但它們并不具有相同的藝術價值,因為復制品并不能復制藝術家在創作時產生的審美情感。所以原作由于是藝術家在擁有審美情感的情況下創作的,因而能使欣賞者獲得審美情感;而復制品由于復制者不具有和藝術家同樣的審美情感,所以不能達到同樣的目的,除非復制者以同樣的心理狀態來進行復制。這樣欣賞者如何通過藝術作品獲得審美情感似乎就產生了困難。
貝爾所舉出的關于原作和復制品的例子再次說明他反對形式主義的立場,藝術價值要從藝術家的主觀活動上去判斷,而不能通過作品本身來判斷,因為作品并不能承載藝術家看待事物的方式。這和形式主義美術史家沃爾夫林希望建立一個“無名的藝術史”的觀點相反。然而藝術家看待事物的方式只有他自己可以知曉,因為它只存在于藝術家的頭腦中,因此貝爾說“我們無法知道藝術家到底在想什么,我們只能知道他創作了什么”。貝爾并沒有解釋欣賞者如何才能知曉藝術家所表現的審美情感,但在科林伍德的理論中,他認為這依靠的是“交感”原理。在生活中,情感的蔓延與傳染往往是無需運用理智活動進行分析,僅僅依靠直覺就可以實現的,這是由于個體與個體之間具有共同的情感經驗。即當觀眾和藝術家有著相同的情感經驗時,觀眾就能夠理解藝術家的審美情感。這種相同的情感經驗顯然先于藝術家創作的作品,觀眾不是通過作品了解了藝術家,而是他原本就了解藝術家,作品只是一個將他們聯系起來的符號。這種解釋符合了貝爾理論中反對運用信息傳遞、反對將作品工具化的立場。因此,我們只能相信由于這種特殊的原因,欣賞者可以理解藝術作品中藝術家所要傳遞出的感情,甚至能夠識別在外觀上相同的仿制品。
本文認為這是貝爾理論中的矛盾,因為,把藝術作品當做它自身的目的來看待,和把藝術作品當做是藝術家自身情感的傳遞中介來看待是兩種完全不同欣賞過程,甚至欣賞者是否能夠準確地把握住藝術家所感受到的情感都是不能確定的。但如果要調和這兩者,使其達到統一的話,那么只能在欣賞者的欣賞結果上達成統一,也就是欣賞者最終獲得審美情感和藝術家的審美情感是相同的,從這個意義上講,可以說欣賞者“接收”到了來自藝術家的審美情感。
四、藝術創作
通過對藝術創作過程的考察可以了解貝爾對作品評價的標準。貝爾認為創作有兩個步驟,簡化(Simplification)和構圖(Design)。簡化和沉思是同樣的含義,指剔除功利性因素的過程,相當于克羅齊理論中的“直覺”。在構圖當中有兩個互相關聯的因素:藝術家的設想(Conception)和表現(Expression)。設想就是簡化,表現是將這種審美情感表現出來的過程。成功的藝術作品就是設想和表現得完全一致,就是抓住并表達出藝術家獲得靈感——即直覺——的時刻11。
貝爾在論述西方藝術史發展時稱,文藝復興盛期的藝術,如達·芬奇的藝術,遜色于8世紀拜占庭藝術的原因是這些藝術家在創作時只想著如何逼真的再現對象,而沒有宗教情感的注入。他沒有從作品自身的性質去判斷藝術價值,而是訴諸于藝術家的主觀活動,這和表現論的傾向是一致的。因此在貝爾看來,藝術作品價值的量化標準就在于藝術家對作品的設想和實際作品之間的契合程度,鑒于“實際作品”這一概念在貝爾理論中處于被架空的狀態,那么量化的標準其實是藝術家對自身意識活動的自覺程度。
藝術創作對于藝術家的意義在于,藝術家通過藝術創作來使自己的靈魂達到救贖(Salvation)12,因為在藝術創作的過程中,藝術家的設想與表現達到完全一致,處于一種迷狂狀態,最終達到了宗教境界,藝術作品作為最后的產物是沒有意義的,它只是達到宗教境界的手段而不是目的,因此藝術家可以把作品丟掉了。
貝爾承認藝術活動是一種感性認識,但是他認為這種感性認識并不是低級的,而是具有終極價值的,是“直接達到善的方法”13。宗教活動的目的在于從根本上拋棄物質世界,進入純粹的精神世界。在諸多宗教的修行活動中,都存在著從運用特定事物來修行(如特定的語句、宗教儀式等)——進入冥想狀態,到擺脫事物的幫助而獨立進入冥想狀態的修行過程。貝爾將欣賞者等同于宗教修行的初級階段,即運用藝術作品來獲得審美情感的階段;將藝術家等同于高級階段,達到了擺脫藝術作品束縛的階段,貝爾認為成熟的藝術家可以在沒有任何對象的情況下獲得審美情感。因此藝術作品就成了審美欣賞過程中必然要被拋棄的東西,它只具有階段性的學習意義,而不具有和審美欣賞相關聯的本質意義。
由此可知,貝爾對藝術作品好壞的評價標準,是藝術家能否表現出自己的情感,雖然這只有藝術家本人才能知曉,但這表明了藝術家的創作只對自己負責,這不是一個服務行業;同時它不能從作品本身的性質上去判斷。這也意味著藝術評價和作品形式無關,他在反對對作品形式的關注。
結語
貝爾的藝術理論以捍衛后印象派繪畫為目的,他所要抨擊的是文藝復興以來,把再現作為繪畫評價標準、和以再現為創作目的的藝術理念。在這一時期他主要的抨擊對象是印象派畫家,因為他們以自然主義為創作信條,貝爾認為后印象派的出現是自然主義發展到極致所必然走向衰落的轉折點,即后印象派是以印象派為代表的自然主義繪畫理念的掘墓人。為了將繪畫從“模仿自然”的理念中“拯救”出來,貝爾提出“藝術以自身為目的”的理念,即藝術區分現實,然而這并不能很有效地瓦解自然主義。在貝爾抨擊模仿論的過程當中,混淆了“把再現性繪畫當作現實”和“以純粹欣賞為目的的再現性繪畫”這兩個概念。貝爾所反對的是把再現性繪畫當作獲取信息的工具,也就是反對把繪畫當作現實生活,這主要指歷史畫、以及紀實題材的繪畫。但是除此之外還有一種虛構的再現性繪畫,它并不指向某種歷史中真實存在人或事,它的內容是虛構,它之所以是再現性的,是因為它運用了透視等視錯覺手法進行描繪。這種繪畫雖然是再現的,但沒有人會把它們當作是現實生活。從“一幅繪畫是再現的”,到“把一幅再現性繪畫當作是現實生活”,這之間仍然有著很大的一段距離,這也是貝爾并不真地反對再現性繪畫的原因。歸根結底,貝爾的理念來自于康德美學中對“審美活動無功利性的”闡述,這是在現代主義藝術發展早期,為這些在形式上和傳統繪畫不同的作品——主要是意象藝術、或表現主義藝術——所進行的辯護。
但貝爾仍處于浪漫主義思潮的后期,藝術創作中的天才觀念深深影響著他,他認為藝術是藝術家的創造,是藝術家自身特性的體現,因此當他希望藝術擺脫外界的控制時,自然就將對藝術的主導權收回到藝術家手中。而他的理論中看似談論了許多關于形式、關于作品本身的東西,但實際上都是為了理解藝術家而服務的,他的藝術批評也就帶有明顯的傳統闡釋學的傾向。在為后印象派藝術辯護的過程中,通過訴諸于表現和情感,雖然擊潰了來自傳統藝術的教條,但貝爾將“表現”和
“形式”這兩個概念交織在一起所進行的闡述,卻沒有辦法兼顧這兩方面。因為這兩個概念從根本上是矛盾的,如果藝術家的情感表現完全在形式中呈現出來,那么我們只要關注作品本身就可以了,因為僅靠形式就可以對藝術家的創作進行闡釋;如果相反,那么形式就會被架空,其實也就是作品被架空,藝術品的概念將會被瓦解,并最終都指向藝術家的情感或意圖。
注釋:
12345671011121314Clive Bell, ART, New York: Frederick A. Stokes Company, 1913,p.
889科林伍德,王至元,陳華中譯.藝術原理[M].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5年,第153頁。
注:本文系黑龍江省哲學社會科學研究規劃項目“東北解放區紅色文藝(美術、歌曲、歌謠)的文獻整理與展演”階段性成果,項目編號:20YSB0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