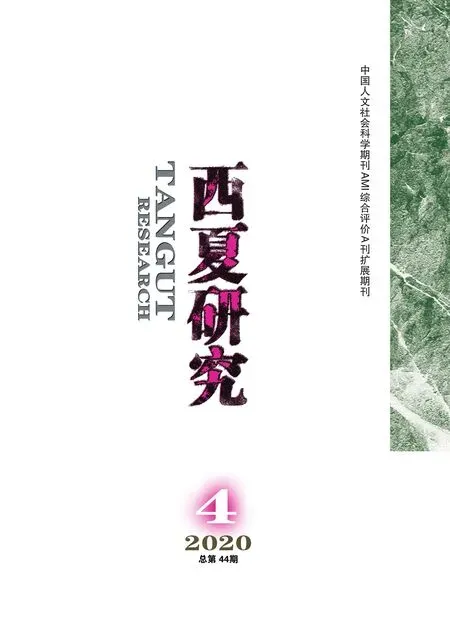俄藏黑水城西夏唐卡《摩利支天》供養人解讀
□朱淑娥
俄藏黑水城西夏藝術品中佛教題材居多,供養人畫像作為佛教繪畫題材的組成部分,是西夏時期社會發展狀況及西夏社會價值觀的真實體現。目前資料上看到的俄藏黑水城西夏藝術品中供養人有30多身,從畫像可大約判斷供養人有帝王、貴族、婦女、兒童、僧侶、平民等。
目前學界對西夏供養人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石窟方面,劉玉權對榆林窟第29窟營建時間和功德主做了深入考察;張先堂對西夏供養人做了集中專題研究,探討了西夏時期瓜州軍政官員營建佛教石窟的重要現象;沙武田在《西夏時期莫高窟的營建——以供養人畫像缺席現象為中心》一文提出西夏后期石窟中供養人的缺失成為西夏石窟藝術的一個特征,表明瓜沙地區在面對全新的藏傳圖像時出現的不一樣的文化認同和心理選擇。對黑水城藝術品供養人的研究上,國外以薩瑪秀克為代表,在《西夏繪畫中供養人的含義和功能》一文中對西夏繪畫中供養人的功能進行了基本解讀、考證和闡釋,從供養人在畫面中的位置、世俗人物佛教僧人、手勢和人物的性質、在場僧人、執行宗教儀式的祭祀工具五個標準來判斷供養人的意義和功能。國內對黑水城藝術品供養人的研究主要以供養人服飾為主,如任懷晟在《西夏僧人服飾谫論》中對西夏僧人服飾進行考證,而對于俄藏黑水城藝術品中供養人專題性研究則涉獵較少。因此,本文以唐卡《摩利支天》(圖1)為例,對西夏供養進行專題性分析論證。
《摩利支天》,絹本彩繪唐卡,80 厘米×53 厘米(原作裱裝130 厘米×64 厘米),現藏圣彼得堡冬宮博物館。其繪制精美,表現技法嫻熟,整幅畫面以紅、白兩色為主色,呈暖色調。畫面布局如下:摩利支天位于畫面正中,雙腳踩于云端上,左右兩下角有三位供養人,正下面是有石頭的風景,石頭壘成小山狀,山石兩邊零星的花草,畫面人物布局延續傳統,供養人布局沿襲傳統,位于畫面底部。與西夏人比較崇尚白色和紅色有關,三位供養人著裝色系基本相同,著紅色上裝、白色下裝。唐卡在西夏社會文化中占據重要地位,“西藏唐卡進入西夏的時間可能很早,但西夏人將這種藝術形式轉化為自己的一種繪畫樣式并能夠熟練應用,則是在12世紀初葉以后”[1]。從其表現風格看,這幅唐卡有明顯的漢、藏風格,從作品的繪畫技法可以初步斷定作品年代為12世紀初—13世紀。

圖1 :《摩利支天》(原圖來源于《俄藏黑水城藝術品Ⅱ》,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圖122)
一、關于供養人身份問題的探討
關于《摩利支天》中供養人,薩瑪秀克這樣描述,“下面是風景畫,右角一僧人執香爐做法事。左角一婦女,著褐色左開襟的衣服,中原式的發型,雙手合十,執一枝花,旁邊一小孩雙手舉向菩薩以求保佑。這母子是唐卡和法事的供養人”[2]。也有學者認為“其中有小孩及父母的圖像”[3]。兩位學者對供養人的身份關系有不同的見解,以下就供養人身份進行分析解讀。
分析供養人畫像,男供養人(圖2)面部方正,鼻梁高挺,蓄有胡須,身披白色縵衣,著紅色僧衣,偏露右肩衣,手持紅色香爐,可以斷定是蓄須發的胡僧。右邊女供養人(圖3)身著長袍,梳高髻;小孩禿發,留小辮,二人大概是母子關系。在西夏唐卡中供養人類型較多,其中“無論是繪畫還是宗教儀式中的供養人都有一個共同的中間人來執行宗教儀式”[4],很明顯,右邊男供養僧人的作用是引導母子來做法事。由此,筆者認為這幅唐卡中所繪供養人并非一家三口,而是僧人引導母子在做法事。
“唐古特人的文化,同任何一個民族的文化一樣,有著自己獨特的根……它已經是在漢族文化和藏族文化的強烈影響下作為佛教文化形成起來的。關于這一點也許還可以爭論,但是西夏文化已經不單純是作為唐古特人的文化,而是……在臨近各個國家和民族文化的影響下形成起來的,同時它也不同于藏族文化,或者甚至于蒙古族的文化,而直接附屬于遠東地區的文化。”[5]這些民族文化融合的特征在供養人身上很直觀地反映了出來。

圖2 :男供養人線描(注:本文中線描圖均為本文作者所繪,下同。原圖來源于《俄藏黑水城藝術品Ⅱ》,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圖122)

圖3 :女供養人及小孩線描(原圖來源于《俄藏黑水城藝術品Ⅱ》,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圖122)
從供養人頭飾上比對,也可以看出西夏文化的多元共融性。元人馬祖常《河西歌》中描述到“賀蘭山下河西地,女郎十八梳高髻,茜草染衣光如霞,卻召翟縣做夫婿”[6],西夏女子發式多為高髻,《摩利支天》中女供養人梳高髻,發髻邊簪花。同時期,“宋代婦女發式多承晚唐五代遺風,亦以高髻為尚”[7]。宋代婦女高髻(圖4)形式多樣,其中“同心髻形制較為簡便,一般是將頭發挽至頭頂,然后攏編成一個發髻即可,發髻具有一定的高度。發髻的造型設計得相當簡潔,線條柔和優美,易體現出女性的溫婉飄逸、淡然若素之態”[8]。從圖中看,女供養人(圖3)的發髻和宋代婦女的同心髻頗為相似,都是在頭頂編一個發髻。“克孜爾壁畫中的回鶻婦女也留這種發式,吐蕃人的頂髻也是這種發式,可見西夏人在發式上,既有北方民族習俗特點,也吸收了中原、回鶻、吐蕃民族發式的特點。”[9]在俄藏黑水城藝術品中,類似的還有《咕嚕咕咧佛母》X-2386(圖5),絹本彩繪唐卡中左下角兩個跪著的婦人,佛事的供養人,由于畫面已模糊,這兩位婦人的著裝不是非常清晰,但從發式上依稀可以看出也梳高髻。《不動明王》X-2375(圖6),麻布彩繪唐卡右下角一男一女供養人,女性發型依稀可見也為高髻。

圖4 :宋代婦女發式(圖片來自沈從文《中國古代服飾研究》,上海書店出版社,2018年,第331頁)

圖5 :《咕嚕咕咧佛母》供養人線描(原圖來源于《俄藏黑水城藝術品Ⅱ》,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圖168)

圖6 :《不動明王》供養人線描(原圖來源于《俄藏黑水城藝術品Ⅱ》,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圖159)
從以上分析可知女供養人的發式,是在中原、回鶻、吐蕃女性發式影響下形成的西夏婦女特有的一種發型,或許因為這種發型很適合西夏貴族婦女戴桃形頭冠而頗為流行。
史金波先生認為“西夏平民女子及侍女也大都梳高髻,但髻上無任何飾物,有的僅簪一朵花,如黑水城出土《摩利支圖》右下角即如此”[10]。史先生認為此女供養人為平民女子。那么這個女供養人身份是否就是平民呢?下面從其服飾來分析。
西夏人對于服飾顏色有明確的規定:“文資則幞頭、靴笏、紫衣、緋衣;武職則冠金帖起云鏤冠、銀帖間金鏤冠、黑漆冠,衣紫旋襕、金涂銀束帶,垂蹀躞,佩解結錐、短刀弓矢韣。馬乘鯢皮鞍,垂紅纓,打跨鈸拂。便服則紫皂地繡盤球子花旋襕,束帶。民庶青綠,以別貴賤。”[11]167據此可知,西夏時服色中貴紫、緋,賤青、綠,《摩利支天》中女供養人著紅褐色窄袖長袍,小孩也身穿紅色上衣,可見女供養人和小孩身份尊貴。此外,“西夏人極愛用金……制作金線用來制造面料或盤繡衣紋……袍服上金線織繡的各種紋飾,華貴、高雅”[12]72,《天盛改舊新定律令》第七《敕禁門》中指出:“全國內諸人鎦金、繡金線等朝廷雜物以外,一人許節親主、夫人、女、媳,宰相本人、夫人,及經略、內宮騎馬、駙馬妻子等穿,不允此外人穿。”[13]283《摩利支天》女供養人長袍上繡金色團花花紋,小孩紅色上衣也繡有金色花紋。由此可以判斷出,此供養人身份并非平民女子,因為只有貴族才可以穿繡有金色花紋的衣服。
另,在《天盛改舊新定律令》第七《敕禁門》中提到“其中冠‘緬木’者,次等司承旨、中等司正以上嫡妻子、女、媳等冠戴,此外不允冠戴”[13]283,說明只有身份地位較高的婦人才可以帶頭冠,此女供養人不戴頭冠,地位并不是很高。“嫡”為宗法制度下指家庭的正支(跟“庶”相對),從上面的文獻可以看出只有嫡妻才可以戴冠,那此女供養人不戴頭冠,或許是貴族家的“庶”妻子。
此外,孩童著紅色短襖,短襖上繡有和其母親同樣的金色團花花紋,下身穿白色黑花長褲,西夏人尚白色,由此也可判斷其為貴族家庭的孩子。筆者認為《摩利支天》中供養人母子身份應為貴族。
二、畫面中石頭的宗教含義
《摩利支天》畫面底部是有石頭的風景畫(圖7),供養人置于風景畫兩側。畫面正中,以墨線勾勒的幾塊石頭壘成小山,并施以簡單的皴擦,兩側以沒骨形式表現了零散小花草。在小山兩側有單塊的石頭和零散的花草,表現形式同前,中間的石頭聯系著兩側站立的供養人,從畫面布局看,石頭在此唐卡中屬于重要的組成部分,到底石頭只是景色的一部分還是另有含意呢?

圖7 :《摩利支天》下面石頭線描(原圖來源于《俄藏黑水城藝術品Ⅱ》,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圖122)
《圣立義海研究》提出“從已發表的文獻資料判斷,大石可蘭石可能是蒼天和大地的來源……至高無上的神圣的嚜山。當天和地尚未形成時,神圣的可蘭石就已長成,后來就成為嚜山。有意思的是,在佛經手稿的書尾題署中提到的唐古特人中,竟也有姓‘嚜山’的人”[5]5。石頭在西夏人觀念中是萬物根源,在西夏人的宗教信仰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
在唐古特人神話中,認為在原始的空虛(混沌)中生出來一個具有生育能力的石頭,石頭生出來山,山具有生長壯大的能力,山的頂峰由神仙居住。石頭生出了陰極和陽極,隨后有了空氣、風、鳥以及宇宙開端的英雄。
“除了神圣的可蘭石之外,在《圣立義海》中還提到另一塊神圣的屈石,它也具有生育的特性,因為人們在七月里向它奉獻祭物,來表示對父母的愛……國內舉行盛典:國君、官員和百姓們滿懷孝悌之情,在屈石前擺滿祭品,深深懺悔。”[5]6在《摩利支天》中石頭位于畫面正中,兩側的供養人面向石頭,說明石頭在這里是被膜拜的,由此,筆者認為《摩利支天》中所繪石頭有可能是《圣立義海》中提到的屈石。屈石在西夏人的意識當中是神圣的,畫于唐卡中,有其深遠的意義。
藏傳佛教中,“摩利支天的地位與菩薩相等,保護信徒遠離各種危險——饑餓、疾病、戰爭、死亡和惡魔,是她最重要的功能之一”,“從宋代開始,摩利支天的諸多功能中有一項逐漸突出,這就是護人于兵革的功能”。[14]西夏人篤信佛教,佛教是他們的精神寄托,對父母的祈福也自然就寄托在了摩利支天身上。《摩利支天》這幅唐卡“它顯然是依照訂購而制作的;訂購它的一對夫婦在左下角落,面貌極似肖像畫的人物。此唐卡顯然是為祈求遠離疾病和惡魔而制作的”[3]。同時,《摩利支天》畫面中的石頭有可能暗含著對父母的祈福,僧人引導母子為其父母親祈求庇護。
西夏人遵守以“孝”為核心的親屬關系,諸種親屬關系中,父母與子女的關系尤為重要,在《圣立義海》中提出,“父者,生子本根,教令長身得安。母者成身,堅養育。其恩如大寶,如天高,子勤孝回報”[5]41。反映了當時西夏以“孝”為大的社會價值觀。在崇尚佛教的觀念下,西夏人“子勤孝回報”的最好方式就是以供奉的形式為父母盡孝,祈求神靈保佑父母遠離疾病和惡魔。因此,《摩利天枝》中的石頭,聰明的西夏人賦予了它神圣的含義,借以對它的膜拜而寄予對父母深深的愛。
三、供養人的藝術表現
(一)肖像畫的寫實風格
“五代時期的曹氏畫院遺留的大量畫家,也應對西夏繪畫發生影響。”[15]170曹氏畫院的主旨為弘揚佛教,在供養人像的表現上“畫像內容已超出崇拜佛釋的本意,而帶有家廟宗祠的意味”[16]23,曹氏畫院在敦煌莫高窟留下的作品很多,以莫高窟98窟為代表的曹議金功德窟,里面的供養人畫像約290多身,供養人畫像肖像畫特征明顯,西夏繼曹氏占領河西走廊一帶,曹氏畫院的這種寫實風格,對西夏繪畫中佛教美術的影響較大。
與西夏同時期的宋代,人物畫進入了寫實期,“宋代圖像和寫貌繪畫的制作,完全踵繼唐代形勢發展,而呈現寫貌超前圖像興盛的趨勢”[17]164。宋代寫實風格的流行,也影響著西夏。當時,“西夏人以國君為模特,造像置于孔廟。可見寫實傳統由來已久”[6]184。
俄藏黑水城西夏藝術品中供養人畫像較多,其真實地反映出西夏繪畫藝術寫貌的寫實性風格,這些供養人畫像大多刻畫深入,表現精細入微,民族特征較強,這種民族繪畫傳統技法,塑造了各時代善男信女外貌的類型美,表現了虔誠供養、消災祈福這一“共同的內在精神,特別在姿態動作,五官表情‘寂默一心,定睛出神’上,樹立了延續千年的供養人這一獨特的肖像畫的典型”[18]。
《摩利支天》中的男女供養人神情肅穆、謙恭,面容刻畫生動,“人物面部豐滿而微長,鼻梁較高,與史料記西夏人面部特征‘圓面高準’正相符合”[19]146。男供養人臉型方正、短發、高鼻梁、眼睛較大,留有短胡須,具有北方游牧民族的特征。其身披白色縵衣,著紅色僧衣,偏露右肩衣,手持蓮花香爐。女供養人面部有明顯唐古特人的特征,大鼻子、寬下巴和橢圓形的臉,梳高髻,簪花。身穿紅褐色繡金色團花花紋長袍,左掩襟,內穿白色襯裙,黑色翹頭鞋履。孩童的刻畫也是甚為精準,西夏孩童的特征盡展眼前,橢圓型的臉,鼻梁高挺,大眼,禿發,后梳小辮。身穿紅色小褂,衣襟敞開,下身穿白底黑花長褲,小手豐腴,神態聰慧。三位供養人畫像刻畫惟妙惟肖,神態各異,人物造型嚴謹,代表了西夏時期不同身份、不同年齡人的普遍特征。
在俄藏黑水城藝術品中多身供養人,肖像畫特征都很明顯,如《阿彌陀佛頭圣》絹本彩繪(圖8)中,右下角的男女供養人,人物五官塑造精致,女供養人身著紅色長袍,頭戴紅色桃形頭冠,腳穿黑履。面部表情肅穆謙卑,面色紅潤,臉部有明顯的“妝靨”。在《普賢菩薩與供養人》X2435(圖9),佛座前方兩位女供養人,穿紅色綴金色或白色碎花的唐古特服裝,左掩襟。唐古特式發型,結很高的發髻,用透明絲綢包裹……她們的年齡不同,也許是婆媳或母女。 前面的年長一些,榜題是“ 白氏桃花”,年輕婦女的榜題是“新婦高氏引見香”。菩薩和官員以及兩婦人的人類學臉型都是唐古特的:大鼻子、寬下巴和橢圓形的臉。這些供養人畫像,都充分表現出西夏時期人物畫的肖像化寫實性風格。

圖8 :《阿彌陀佛頭圣》(局部)(圖片來源于《俄藏黑水城藝術品Ⅱ》,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圖12)

圖9 :《普賢菩薩與供養人》(局部)(圖片來源于《俄藏黑水城藝術品Ⅱ》,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圖30)
(二)風俗畫的表現風格
風俗畫在宋時頗為流行,市井生活成為畫家的表現對象,兩宋“由畫院開始的風俗畫創作,在其發展過程中,也逐步由城鎮擴展向鄉村,有大景象滲透向小情節”[15]154,“五代至宋元時期,世俗的人物畫則沿著張萱、周昉開創的綺羅人物演進,作風更加細密精麗,刻畫人物的內心世界更加精妙入微”[20]173。這種風俗畫的表現風格對西夏繪畫影響深遠。
在《摩利支天》中,供養人表現風格有明顯的宋風俗畫的特征,左下角小孩雙手做合十狀,回首顧盼,在母子身后是寫意的小風景,有石頭和零散的路邊小花,母親手中所拿的供物正是路邊采摘的花束,母子和僧人之間以風景為聯系。神圣的唐卡是用來供奉的宗教繪畫,但在《摩利支天》中小孩動態的表現,生活氣息濃厚。不同于供養人虔誠的神態,孩童回頭看著母親,頭上的小辮隨之飛動,雙腳分開站立,表現出母子在路邊的生活場景,濃濃的生活氣息,和路邊石頭小景相配,風俗畫風格彰顯無遺。此種畫法明顯受宋代文人風俗畫影響,“南宋畫院畫家所描繪的民間風俗,要是民間生活和勞動場景,被稱為‘田家風俗’”[15]159。《摩利支天》中供養人表現了西夏人供奉時的生活場景。
在俄藏黑水城藝術品中,類似風格的還有《月孛》X2454(圖10),麻布彩繪,右下角男性供養人,身后以高聳的竹子為風景,畫面下面繪有花草,以小寫意形式表現。“此畫用西夏文字題的榜題,解釋為:好心者葉,即供養人葉氏(或耶氏)。”[2]236作品中石塊勾勒較為隨意,但也不缺少皴擦點染,花卉用寥寥數筆,表現出了生機勃勃的小場景,極富有生活氣息。說明宋代風俗畫對西夏繪畫的影響較大,由此也反映出此時期西夏佛教的進一步世俗化。

圖10 :《月孛》(局部)線描(原圖來源于《俄藏黑水城藝術品Ⅱ》,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圖51)
四、結 論
從以上討論可知《摩利支天》中供養人是西夏貴族婦女帶領孩子在胡僧引導下為父母祈求遠離疾病和惡魔的。供養人肖像畫和風俗畫藝術風格的表現,反映了西夏佛教的世俗化與功利化。“西夏社會的特征導致了西夏佛教一個顯著的特點,那就是極強的實踐性和高度的包容性。”[1]《摩利支天》正體現了西夏佛教文化的包容性。黑水城藝術品中供養人畫像具有豐富的歷時性,受到當時西夏社會歷史的變遷、民眾宗教信仰的演變和繪畫藝術表現形式變化等多種因素影響,使得西夏時期的供養人畫像在歷史上不同的時期呈現出不同的時代特征。“西夏藝術在漢地河隴繪畫風格為主體和多種藝術風格成分融合的結果。除了藏傳繪畫風格外,尚有回鶻風格和其他中亞風格成分。”[1]從供養人畫像中可以看到西夏社會文化在特定的時期受吐蕃、漢文化的影響,形成了民族共融的社會文化,這種多種文化的交融,使得西夏藝術展現出其獨特的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