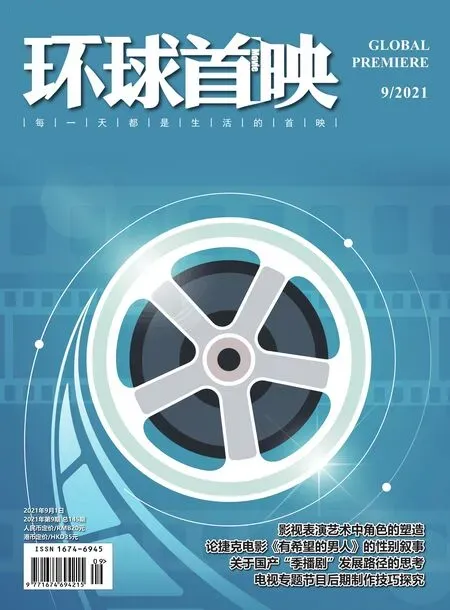論舞蹈藝術之“真”
王勝利 廣西藝藝貳柒文化傳播有限公司
舞蹈作品貼近生活,更容易使觀眾產生共鳴,也更容易被大眾接受。舞蹈藝術的“真”實際上就是指真實的生活表達,是舞蹈藝術追求善與美的前提。眾所周知,舞蹈是靠肢體動作的發展來傳達思想和內心情感功能的,它是一種無聲的肢體語言,易抒情、難敘事。大多數觀眾的不同的觀點,一是舞蹈盲目表達自我,很難感受;二是敘事直白,像啞劇。筆者認為這是舞蹈大眾化發展的很大障礙,解決這一問題就需要在兩者間尋求平衡,也是舞蹈編導應該思考的問題。
一、舞——起于情、源于真
(一)情以動舞
舞蹈是人類早期在祭祀、祈福、勞動等一些生活體驗中創造出來的一種藝術表現形式,它與生活息息相關。據《漢書·李廣蘇建傳》記載,“昭帝始元六年,匈奴與漢和好,釋放了漢使蘇武歸漢,李陵置酒為蘇武踐行,對蘇武說:此一去,永訣別!說完,李陵情不能已,一邊起舞一邊唱。歌舞畢,李陵潸然淚下,與蘇武告別。”李陵為什么在悲痛之時即興舞蹈呢?人類語言是有其自身局限的,當他不能確切、準確地表達出他的情感時,就必然出現言不盡意的情況。舞蹈用肢體成象能夠呈現出更加直觀的讓人感受到情緒和情景。
舞蹈是人類在生活體驗的過程中創造出來的,所以沒有生活作為基礎,今天的舞蹈便不復存在。當今中國有56 個民族,幾乎每個民族都有自己的舞蹈風格特點,這么多舞蹈風格的出現就說明各民族的人民都熱愛舞蹈,并且每個民族的傳統、文化、生活習俗和勞作方式等都有不同。甚有一個民族出現多種舞蹈風格。比如漢族,雖以秧歌為主,但又分東北秧歌、膠州秧歌、海陽秧歌和谷子秧歌,還有安徽花鼓燈和云南花燈等,這些民間廣泛流傳并形成各自特色的舞蹈更能說明舞蹈與生活的密切關系。生活無處不帶有情感,舞蹈其本身就應該是生活情感的表達,也可以說舞蹈是“跳動的生活”。舞蹈是人類生活體驗的智慧結晶,也是智慧融入生活的一種表現。
(二)舞動以真
新中國成立以來,舞蹈在思想內容和形式特征上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出現了一大批經典之作。以20 世紀60 年代中期的舞蹈《洗衣歌》為例,其情節為:一群到河邊洗衣的藏族姑娘偶遇解放軍炊事班長去洗衣,姑娘們設法讓小卓嘎引開班長,以達到幫解放軍洗衣的目的。作品繼承了藏族傳統樂舞的特點,再現了軍民一家親的現實情境,在當時成為膾炙人口的作品,整個舞蹈活潑風趣,體現了藏族人民報答解放軍的真實情感,將洗衣、搓衣、踩衣、擺衣、撩水等生活動作節奏化、動律化,充滿生活氣息,洋溢著軍民團結的真摯情感。
由此,我認為舞蹈舞動下更執于追求真情實感,追求的是在自我的生命中最為“真”的情感體驗,這是舞蹈藝術生命的根基,斷了根的舞蹈就像斷了線的風箏,像無家可歸的流浪者,像那些戰敗后沒有政府的國家。旁人很難給他一個定義,很難理解他的去向,也很難接受它的存在。從事舞蹈的人,總希望舞蹈更加繁榮,為了不再讓人們以冷漠的態度對待舞蹈,就要以真實的舞蹈情感換取人們對舞蹈藝術真切地熱愛。
二、舞——真而盡善
新中國成立以后,國民的綜合素養整體提升,人們的審美層次也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以往單一的藝術形式已不能滿足人們的需求,在追求美的同時,還追求思想升華和哲理啟迪。所以,舞蹈創作不能脫離生活憑空想象、閉門造車。否則,離大眾越遠舞蹈就越難被大眾接受和認可。于是,從上述探求而知舞蹈起于情源于真,如此,便可從當今舞蹈藝術中“真”來從觀眾角度探討舞蹈作品中的“情”感連接。
(一)舞動于真,情動于人
群舞《中國媽媽》從主題上歌頌的是偉大的母愛,不僅是對自己孩子的愛,也是對別人的孩子。這種大愛與大恨的強烈對比體現出母愛的無私與偉大。它是一部大眾都看得懂的作品,因為動作語匯來源于生活,開場的一個“指”,然后到捶腿、跺腳、再到掐脖子等一系列表現憤怒、仇恨的動作都非常生活化,處處質樸無華卻不平凡的表演中,把觀眾帶入其情感中。一個優秀的文藝作品,不管是主題選材還是動作提煉和加工,都要源于生活,否則,很難打動觀眾。正如瑪莎·格萊姆在尋求新方式去表達自由時所說的那樣:“我希望自己的舞蹈以現實為基礎,并且為想象所照亮,成為有機的而非合成的東西,從觀眾中喚起一種確定的反應,并且為生活的戲劇作出貢獻。”
(二)真后定善,以善相連
舞蹈可以寫實或寫意,它就像中國的書法、水墨畫一樣善于留白,給人更大的想象空間。2005 年春晚的舞臺上,聾啞演員將舞蹈《千手觀音》演繹得惟妙惟肖,這部作品是從中國敦煌壁畫中吸取的創作靈感,舞蹈形象以敦煌石窟中的“千手觀音”像為原型,“千手”表示大慈悲的無量廣大,“千眼”則代表智慧的圓滿,不僅視覺效果好,而且寓意深厚。《千手觀音》給予人們心靈美和藝術美的啟示,舞蹈演員所詮釋出的祥和、端莊的千手觀音形象給予了我們一種正能量,在欣賞的同時,也傳遞出善與愛的力量。甚至演員的表演也是相當震撼,可以說,舞蹈演員們是用生命在舞蹈,他們所詮釋的千手觀音的真善美,是他們戰勝殘疾的精神力量。千手觀音其實是演員的人格化身,體現出了一種純凈善良的正能量,既感染了自己,也陶冶了他人。其實我們都明白,觀音是不存在的,但每個人心中都擁有一顆博愛之心,在欣賞同時,也傳遞出了善與愛的力量。從而教化我們、感染我們,帶給我們的想象和思考是藝術的最大“魅力”。所以,人的內心向往的美好生活也是舞蹈創作的根源。
三、舞——盡善則盡美
舞蹈藝術中的真與善,實際上是追求美的終極關懷,因此,舞蹈創作者都盡力在追求真的情懷,從而達到善與美的境界。
(一)“真”于舞蹈創作
舞蹈創作要“接地氣”,反映普通民眾的愿望、訴求、利益。不能浮于表面,而要踏踏實實,深入人心。這樣才有底氣,才有生命力,才會創造出“有思想的舞蹈藝術”與“有舞蹈藝術的思想”和諧統一的優秀作品。這一通俗之詞便恰如其分地表達了舞蹈創作者對于“真”的生命熱忱和融于作品中藝術境界的提升。正如王玫老師在一篇文章中所述:“舞蹈的質量源于編創,更源于生活,不同的生活決定著不同的舞作,也決定著舞作不同的質量。”所以,經典的舞蹈作品一定是編導通過生活的體驗創作出來的。生活便是本真,是舞蹈藝術創作的根源。
(二)舞蹈創作“真”于“善、美”的時代追求
1.與時俱進下的時代訴求
在不同時代背景的影響下造就了不同舞蹈創作者對于人生觀與價值觀的追求,革命年代經典芭蕾舞蹈作品《紅色娘子軍》中,舞蹈編導執于追求之“美”便是民族堅強不屈的精神和昂揚向上的品格;和平年代作品《冬古拉瑪情》中,編導盡心抒發之“美”表現出人間真情無限,大愛無疆的高尚境界。因此,不同時代的舞蹈創作者應跟隨時代的腳步,在所處時代“真的情感”下以“善的關懷”創造出藝術“美”的境界,而非局限在相對歷史的角度。
在全世界舞蹈的發展中,反而越是民族的,更得到世界認可,這已為大多數人所認同。很多編導在舞蹈創作的過程中,不斷深挖本舞種可創造性和本民族所特有的舞蹈語匯,將創作出新的肢體語匯呈現出獨特的民族氣息,致力于發展民族獨有的文化底蘊,傳達通俗易懂的民族特性。如《踏歌》《東方紅》《翻身農奴把歌唱》《千手觀音》等作品,其創作思路趨向更深的層面,體現了中國人的民族個性、民族的審美意識和民族精神狀態。在整個創作表演過程中,但凡優秀的作品都能給社會有所啟示,都能較深刻地揭示人類的心路歷程。
2.與時俱進下的創新追求
近年來,我國的舞蹈藝術創作,由于引入了大量的現代觀念與編舞技法,極大地豐富了舞蹈創作,呈現出多元化、多樣化、個性化的創作發展趨勢。
張藝謀導演的民族芭蕾舞劇《大紅燈籠高高掛》,結合了大量的中國舞和現代舞語匯,講述了一個美好而又悲慘的故事,它的情節緊緊抓住了觀眾的心,處處可見導演藝術上的豐富想象。業內人士雖對此評價不一,但是觀眾卻覺得很新鮮,這種多元化和邊緣化創作作為先鋒的藝術潮流和創作趨勢,也不失為一種新的探索。
歐建平先生認為:“計算機編舞”將成為未來舞蹈創作的一種科學而實用的工具,為“身體力行”和“口傳心授”等傳統編舞模式提供其他選擇余地,并能夠借助互聯網,展開異地間的遠程合作,創造出一種超越肢體活動范疇的“網絡舞蹈”形式,利用高科技的手段,形成多元化的藝術形式。
中國歌舞團的《秘境之旅》,同樣采用了現代手段,打破了傳統的模式。它的舞蹈既有藏族踢踏舞、傣族孔雀舞這些民族的元素,也有現代舞的表現手法,為群眾所喜聞樂見。由此可以看出,將民族性與時代性和現代性緊密結合、不斷創新是中國舞蹈創作的重要發展趨勢。
無論其作品的創意、表現形式、語言載體、方法如何變幻,都必須堅持堅定不移、高瞻遠矚的創新精神,繼承傳統、發揚傳統,根據新的生活內容和塑造新的人物形象的需要,在原有民族舞蹈基礎上進行新的創造,才是我國舞蹈創新發展的一條大道,也是我國舞蹈事業興旺和繁榮的一條必經之路。
四、結語
近年來,舞蹈創作中更加傾向于發掘作品的文化內涵,編導從現實生活出發,把握生活的源泉,創造出嶄新的舞蹈形象,著重讓舞蹈產生創造性,把舞者生存的困惑、人性的復雜與矛盾、對生命本質的追問以及渴求自我表達的內在沖動融入作品中,把它作為藝術存在的根本理由和舞蹈創作的更高依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