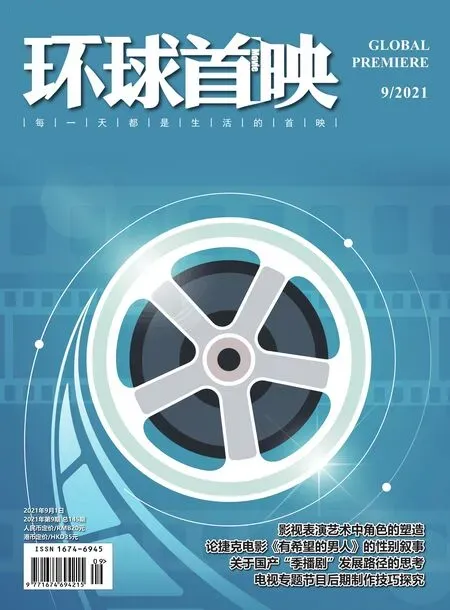淺析戰“疫”微紀錄片的特點和價值
張曉萱 重慶郵電大學
當今時代媒介高度融合,人們的思維方式和生活習慣發生了很大的變化,習慣了快節奏的受眾面對紛繁復雜的媒介信息逐步形成了碎片化的接受趨向,順應人們快節奏、碎片化的需求各種“微”信息進入人們生活,微博、微信、微電影、微小說等微文化形態的出現直接宣告著微信息時代的到來。在媒介融合的推動下,紀錄片也做出了改變,誕生了新的形式——微紀錄片。
庚子年初,一場突如其來的疫情席卷中國。與此同時,關于疫情的輿論信息錯綜復雜,一些負面的信息給群眾帶來不必要的恐慌,參差不齊的輿論信息也給宣傳防控工作帶來了困難。面對如此局面,國家、地方以及各新媒體平臺積極推出微紀錄片來記錄戰“疫”實況,涌現出一批優秀的戰“疫”微紀錄片,這些微紀錄片用真實的素材向觀眾傳達著人文精神,在新冠疫情期間起到了積極的輿論引作用。
一、創作特點
在新媒體語境下誕生的微紀錄片在創作方面既保留了傳統紀錄片紀實的創作原則,創作從實際出發,取材源自生活。同時又具有了不同于傳統紀錄片的特征,創作又高于生活,是生活的凝練和提高,其創作的核心“微”主要表現在其拍攝、制作、敘事等方面。
(一)微拍攝
微紀錄片時長相對較短,主要在幾分鐘到十幾分鐘之間,這是微紀錄片和傳統紀錄片相比最為顯著的區別。無須宏大的場面,不需要專業的拍攝團隊也不需要高超的拍攝技術,微紀錄片更加注重表達深層的主題內容和展現細節,只需在短時間內向觀眾傳達觀念和信息。因此,微紀錄片在拍攝上呈現出“微”的特點,其拍攝設備、拍攝主體多元,拍攝時空自由,投資小,近來拍攝微紀錄片的人也越來越多。
專業的拍攝設備更新換代,除了專業拍攝影像的攝像機,相機也加入了拍攝視頻的功能,單反相機被廣泛應用在微紀錄片的拍攝中,人們開始使用單反甚至微單進行相對專業的微紀錄片拍攝。隨著單反相機像素不斷提升,畫面質量和清晰度更高,可以拍攝4K 的畫面,實現高質量的畫面傳輸,且越來越智能,越來越輕便,更方便上手。與此同時,手機拍攝也已廣泛普及,拍攝門檻大大降低。加之播出平臺普遍化,新媒體短視頻平臺的出現更是提高了人們日常用影像記錄生活的意識。在這個全民記錄的時代,越來越多的普通人變身導演,拍攝和記錄自己感興趣的事物,Vlog 的產生和發展就是很好的例子。有了非專業拍攝人員也可以熟練掌握的拍攝工具——手機,許多非專業人員也能輕松完成微紀錄片的創作,手機拍攝成了創作微紀錄片的重要途徑,一個人拍攝微紀錄片成為可能。
疫情暴發后,主流媒體充分運用微紀錄片中微拍攝的特點,倡導微紀錄和新聞的融合,新聞報道者帶著簡單的拍攝設備親身體驗疫情下的武漢,或直接選用武漢市民、武漢志愿者以及醫護人員拍攝的視頻,通過直觀的記錄真實反映社會問題,微拍攝的畫面鏡頭質量也許并不盡如人意,但真實直擊人心的現場畫面直接賦予其巨大的感染力,讓微紀錄片成為疫情中人民看向外面真實世界的窗口。
(二)微制作
微紀錄片素材相對較少,故事情節緊湊,無須復雜的剪輯技巧,制作周期短,制作成本低,整體上呈現出微制作的特點。如今各種視頻后期軟件越來越便捷,一般的電腦甚至手機都可以對拍攝的素材進行后期編輯,視頻制作軟件的種類也越來越多,如PR、Final cut、InShot、剪映等,這些制作軟件都簡單易上手,即使沒有任何視頻制作經驗的人也可以通過簡單的學習快速掌握使用技巧,并且許多軟件也為方便視頻制作加入了新的功能,如一鍵拼接、一鍵字幕、濾鏡、音樂和現成的片頭結尾等,更方便了微紀錄片的制作。
(三)微敘事
不同于傳統紀錄片的宏大冗長,微紀錄片更傾向于在宏大主題下進行微觀敘事,聚焦小人物的故事,扣住鮮明的主題,通過微觀的敘事方式表達宏觀的思想內容,具有一定的思想深度,能夠引發觀眾思考,產生情感共鳴,給受眾留下深刻的印象。由于微紀錄片的時長較短,很多紀錄片往往選擇在一個點上進行敘事,或抓住一個人物的一個方面來講,準確地圍繞這個小點來表達主題。有學者說:“在長篇作品中,8 分鐘的段落已成為公認的規則,甚至短短的4~5 分鐘的片段也開始盛行。《舌尖上的中國2》就具備了標桿性的敘事模式。”①
微紀錄片通常將視角聚焦在普通的小人物身上,甚至很多紀錄片直接才采用第一人稱視角,用Vlog 的形式講述發生在自己身邊的事,拍攝者本身的言行也被記錄在影片當中。這樣微敘事視角的切入充分表現了真實的生活,更加貼近人民、貼近生活,以小見大,這種獨特又親近的平民化視角更能夠讓觀眾產生情感共鳴。
二、現實價值
互聯網和新媒體快速發展,視聽媒介傳播訊息十分普遍,新媒體平臺發布的影響視頻成為群眾了解信息的重要來源途徑之一,微紀錄片具有真實、準確和可信賴的特點,這些特點使得紀錄片具有極強的公信力,對疫情期間緩解恐慌、凝聚人心、彰顯民族精神、增加國家認同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一)實時記錄,疏解情緒
在媒介融合的時代背景下,微紀錄片打破了傳統紀錄片的各種局限,創作門檻降低、時長變短、制作多元、敘事簡單,在傳統紀錄片真實性的基礎上,微紀錄片具有了時效性的特點,實時紀實,及時地回應熱點問題,引導群眾情緒。有學者提出,在新冠疫情期間人們被動待在家,時刻通過各種平臺關注著全國疫情資訊,而在紛繁復雜的輿情訊息下,謠言摻雜其中,各種不確定的因素給群眾帶來了不必要的恐慌和不安,這時候微紀錄片要做的就是整合人民訴求,及時回應、解決人民的困惑和問題。戰“疫”微紀錄片第一時間將鏡頭對準疫情中的故事,記錄一線抗疫信息,及時回應群眾問題,用影像向宅在家的群眾真實還原了抗疫現狀。
2020 年2 月,中央廣播電視臺同各新媒體平臺合作推出微紀錄片《武漢:我的戰“疫”日記》,通過將大眾Vlog 畫面進行包裝處理,以醫護人員、志愿者以及武漢市民記錄的畫面向大眾展示武漢疫情的最新情況。這些畫面記錄者大多以自己的第一人稱視角記錄生活,觀眾通過這些畫質略低且有些晃動的鏡頭直擊武漢。微紀錄片制作周期很短,在制作過程中根據群眾反映以及輿論熱點進行調整和回應,第一時間將事實投放,有效抵制了負面輿論,直接對抗謠言和恐懼,大大緩解了群眾焦慮,讓觀眾對疫情實況有了正確的認知。
(二)全息紀實,以人為本
在疫情期間,除了專業的拍攝人員,更多的普通群眾開始拿起手機記錄生活,以微紀錄片的形式發布在新媒體平臺上,后期專業媒體對一些群眾記錄的素材進行編輯整理形成系列微紀錄片,在各媒體平臺投放,公眾可以通過這些微影片直接了解疫情期間人們的生活狀態,微紀錄片帶來了傳統媒體所達不到的細致入微的全息紀實。
《武漢:我的戰“疫”日記》《武漢戰疫紀》展現了武漢市民、醫護人員、志愿者等人的溫暖故事,通過不同視角塑造了人民眾志成城、國家團結一心、共同抗擊疫情的形象,傳遞著民族精神和正能量。同時也有很多自媒體人通過客觀的記錄,既展現溫暖的故事也不避諱疫情帶來的消極影響,來回應群眾對真相的疑問。抗疫微紀錄片《在武漢》用最質樸的畫面講述了在特殊時期武漢的人和事,堅持為醫護人員出車的出租車司機、配送蔬菜和藥品的外賣員、為遠在他鄉的武漢人喂寵物的鎖匠還有為醫護人員剪發的理發師等。武漢微博博主“蜘蛛猴面包”在他的博客上投放了微紀錄片《封城日記》,真實呈現了當時的武漢現狀和市民的志愿活動,片中展現了疫情中武漢排起長隊的超市、無人看管的寵物、徒步前往醫院的老人等,捕捉了很多主流紀錄片無法觸及的真事實,為新聞等主流輿論做了更加鮮活、更加貼近生活的補充。
(三)多元傳播,凝聚人心
媒介融合的時代背景下,微紀錄片的傳播方式有了更多的選擇,不僅可以投放在電視上,其短小精悍的優勢更適用于網絡傳播,各大視頻平臺紛紛設置紀錄片板塊,為微紀錄片的創作和傳播提供了便利,也使得原本受眾較少的紀錄片被更多人接受。觀眾可以隨時隨地觀看,一鍵轉發進行再次傳播,直接評論發表自己看法,充分調動了年輕人看紀錄片的積極性。
疫情期間人們密切注視著資訊信息,微紀錄片作為公信度較高的媒體形式,受到了群眾關注。愛奇藝、騰訊、Bilibili等視頻平臺在首頁設置疫情專區,戰“疫”微紀錄片以其內容真實、時長適中等優勢頻登頭條。疫情病毒同時也在國際輿論場上蔓延,全球受眾關注著疫情的實時發展情況和防控進程,各種負面謠言、不實信息嚴重影響國家形象,微紀錄片則擔起“喉舌”的責任,以其感召力傳播中國聲音。中國國際電視臺推出微紀錄片《武漢戰疫紀》是首部英文戰“疫”紀錄片,一經播出觀看破億,多方海外平臺轉載,在世界上引起極大反響。
新媒體的交互性具有凝聚人心的作用,新媒體互動性強,觀眾參與度高,微博、微信等互聯網傳播媒介成為大眾信息傳播的主要陣地,微紀錄片在互聯網的傳播圈上無限擴展式轉載傳播,同時微紀錄片所傳遞的信息第一時間在彈幕、評論中得到反饋,與拍攝者分享他們的看法,表達自己的意見。
三、結語
在媒介融合語境下誕生的微紀錄片具有著微拍攝、微制作和微敘事等特點,講身邊人身邊事,受到了群眾的普遍認同。同時微紀錄片源于生活的特點使其具有了極強的公信力,對彰顯社會主義人文精神、傳播正能量、增加國家認同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未來微紀錄片創作應充分利用媒介融合給予它的優勢,保持內容質量的同時豐富畫面效果,以人為本,迎合時代熱點弘揚民族精神、增進國家認同。5G 時代到來,新媒體傳播速度更快,傳播方式更加多元,面對不斷更新的傳播生態,微紀錄片要充分利用互聯網帶來的便利,發揮更大的價值。
注釋
①王杰.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2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