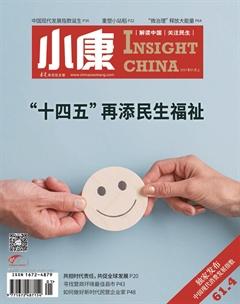南通城初具規模
東升

好讀書,不求甚解;喜說文,不激不隨。
上回介紹了中國近代史上最成功的華商紗廠——大生紗廠的誕生地——看似極為普通的江北工業小鎮唐閘鎮。在發展唐閘工業區鎮的同時,中國近代著名的愛國實業家、政治家、教育家和思想家張謇選定位于南通城西南長江邊的天生港作為港口區,于1904年建造碼頭,成立大達輪步公司,其后又創辦了通燧火柴廠等企業,形成了天生港港口鎮的雛形。
狼山鎮位于南通城南長江邊,距城也是9公里左右, 軍山、 劍山、 狼山、馬鞍山、黃泥山等五山沿江而立。張謇結合狼山鎮自然風光,在狼山、軍山、黃泥山等處建筑了林溪精舍、趙繪沈繡之樓、東奧山莊、西山村廬、望虞樓等別業和景觀,與這里原有的古剎寺廟融為一體,遂使狼山鎮成為宗教區和游覽風景區。
張謇在南通舊城的南部開辟了新市區,把學校、文化機構集中于東側。于20世紀初創辦了中國第一所師范學校——南通師范學校,建立了中國第一座博物苑——南通博物苑,還創辦了圖書館、醫院等設施。在南通舊城西側以桃塢路為中心,開辟了商業街、戲劇場,建成了一些大型建筑,如總商會、更俗劇場等。在舊城的南濠河,修建了東、南、西、北、中5個公園,大大美化了城市環境,成為人們游覽與休閑的好去處。
南通城和唐閘鎮、天生鎮、狼山鎮之間酷似三鼎護香爐狀,香爐(南通城)居中,三鼎均布在外,彼此之間自然分布著綠色的田園,城鄉相間,各自可以合理發展,但又相距不遠,中間有河道及公路連接,在城市功能上渾然一體,形成了一城三鎮獨特的城鎮空間布局。到1920年,南通的城市建設已初具規模。
初夏時節,通揚運河上偶見一兩只載著沙子的鐵皮貨船往來穿行。過往的繁忙景象已經依稀難辨,只是在發黃的史料記載里,當年以洋紗、洋布為代表的洋貨橫行,就是沿著這條波光粼粼的運河大道直抵江北,就連偏僻地區的手工業也遭到嚴重破壞。
回望19世紀末,列強以堅船利炮轟開封建中國門戶的同時,也加緊了經濟侵略。《馬關條約》的簽訂,更使外國資本長驅直入,紛紛在沿海投資設廠,傾銷商品,1867年進口機紗為35507擔,到1899年猛增為2748644擔,30多年增長了80倍。照此下去,中國民族工業發展的一線生機將被活活地扼殺在襁褓之中。
“四萬萬人齊下淚,天涯何處是神州”,中國大地上進行著一場事關民族圖存的商戰。不少懷抱先進思想的官僚知識分子仿效西方,買機器、辦工廠,冀望以“商戰”之勝來補“海戰”之敗。
《馬關條約》簽訂后的第一個蕭瑟深秋,在家服喪的晚清恩科狀元張謇心急如焚,他憤然在日記中寫道:“幾磬中國之膏血,國體之得失無論矣。”
腳下的故鄉南通盛產棉花,“力韌絲長,冠絕亞洲”,而那段時間卻隨著洋紡織機器的盛行而大量運往日本,成為日產棉紗的必需原料。花往紗來,南通一帶洋紗洋布的銷售日盛一日,多時達到每天20大包,本紗本布卻銷路日減……眼見民生凋敝、國富外流,張謇慨然長嘆:“這與割肉喂虎有什么區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