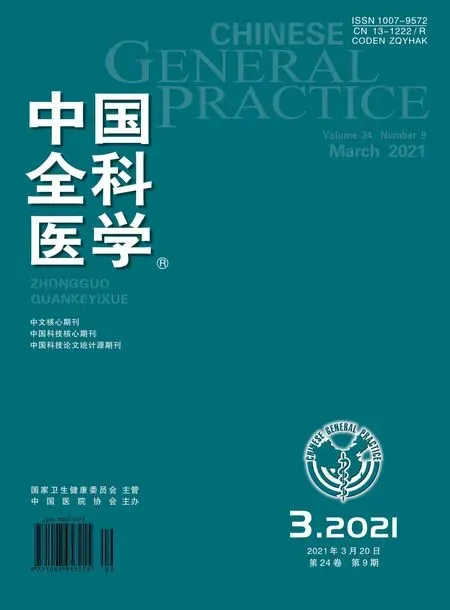睡眠質量與抑郁癥狀及其交互作用與老年人認知衰弱的關聯研究
崔光輝,李少杰,孔慶悅,尹永田,陳莉軍,陳磊,劉馨謠
認知衰弱是指在排除癡呆的情況下個體同時存在身體衰弱和認知功能下降的狀態[1]。與單獨的衰弱或輕度認知功能損害相比,認知衰弱發展為癡呆[2]甚至死亡[3]等不良健康結局的風險顯著增加。既往研究認為,作為神經病變的前驅期,認知衰弱具有一定的可逆性[4]。因此積極探討認知衰弱的危險因素并進行早期識別和干預有助于提升老年人生活質量,減少醫療和照護負擔。然而目前國內相關研究尚處于起步階段,主要為文獻綜述或僅關注認知功能損害與衰弱中的一者,缺乏針對大陸社區老年人群的橫斷面調查和因素之間交互作用的探討。MA等[5]認為抑郁癥狀是認知衰弱的獨立影響因素。此外,通過文獻梳理發現睡眠質量與衰弱和認知功能障礙之間存在關聯[1],但能否將其推論為認知衰弱的預測變量尚未可知。故本研究旨在系統探討睡眠質量、抑郁癥狀與老年人認知衰弱的關聯,并進一步驗證二者是否存在交互作用,為今后開展社區篩查和多學科管理提供一定的借鑒。
1 對象與方法
1.1 研究對象 采用分層整群抽樣法,于2019年12月從濟南市隨機選取3個區、1個縣,每個區縣抽取2個街道或鄉鎮,每個街道抽取2個社區或行政村,對該社區或行政村中所有符合納入標準的老年人進行調查。納入標準:(1)年齡≥60歲,有居住地常住戶口;(2)無聽力、精神及認知障礙;(3)無重大疾病。共抽取6個社區、10個行政村1 130例老年人進行調查。
1.2 研究方法
本研究價值及局限性:
國內關于認知衰弱的研究主要為文獻綜述或僅關注認知功能損害與衰弱中的一者,且缺乏其影響因素間交互作用的探討。本研究通過橫斷面調查探討了老年人睡眠質量與抑郁癥狀及其交互作用與認知衰弱的關聯,為后續干預提供了一定的參考依據;但同時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一是無法證實三者之間的因果關系,期待進一步的縱向研究加以證實;二是關于此交互作用背后具體的生物學機制尚有待深入研究。
1.2.1 一般資料調查表 采用自制一般資料調查表對受試者性別、年齡、家庭經濟水平、受教育程度、每日久坐時間、是否患有慢性病等資料進行調查。慢性病標準根據國際疾病分類(ICD-10)標準,將9種常見慢性病:高血壓、心臟病(冠心病、心律不齊)、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慢性胃/十二指腸潰瘍、慢性頸/腰椎病、2 型糖尿病、腦卒中、抑郁癥、癌癥列入此次調查。
1.2.2 匹茲堡睡眠質量指數量表(Pittsburgh Sleep Quality Index,PSQI) 采用PSQI對老年人睡眠情況進行評定。PSQI由BUYSSE等編制,在中國人群中的Cronbach's α 系數為 0.842[6]。PSQI包括主觀睡眠質量、入睡時間、睡眠總時間、睡眠效率、睡眠障礙、使用催眠藥物、日間功能7個維度,共18個條目;每條目均采用Likert 4級評分法(0~3分),總分為0~21分。PSQI總分≥8分提示受試者存在睡眠障礙。
1.2.3 簡版老年抑郁量表(Geriatric Depression Scale,GDS-15) 采用GDS-15對老年人抑郁癥狀進行評定。GDS-15由YESAVAGE等編制,在中國老年人群中的Cronbach's α系數為0.793[7]。GDS-15共15個條目,每個條目依據答“是”或“否”分別計1、0分,總分0~15分,>8分為存在抑郁癥狀,總分越高表示受試者抑郁癥狀越重。
1.2.4 認知衰弱評估 首先,采用簡易精神狀態量表(Mini-mental State Examination,MMSE)對老年人認知功能進行評定。MMSE由FOLSTEIN等[8]編制,在中國人群中的評價者間一致性和間隔2~6 d重測信度分別為0.97和0.90[9]。MMSE包括時間和地點定向力、記憶力、注意力與計算力、回憶力、語言能力5部分,共30條目;每答對1題計1分,總分為30分。以中學及以上受教育程度MMSE≤27分、小學文化程度MMSE≤24分、文盲MMSE≤21分為標準判定受試者存在認知功能障礙[10]。其次,采用中文版Tilburg衰弱量表對老年人衰弱情況進行評定。Tilburg衰弱量表由GOBBENS等研發,奚興等[11]翻譯漢化,在中國老年人群中的Cronbach's α系數為0.686。中文版Tilburg衰弱量表包括軀體衰弱、心理衰弱、社會衰弱3個維度,共由15個條目構成;每個條目答是計0分、否計1分,總分為0~15分,≥5分為衰弱,分數越高表明受試者衰弱癥狀越嚴重。若受試者同時存在認知障礙和衰弱,則將其判定為認知衰弱。
1.3 統計學方法 采用SPSS 25.0統計學軟件進行數據分析。計數資料以相對數表示,組間比較采用χ2檢驗。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歸分析探究社區老年人睡眠質量、抑郁癥狀及其交互作用對認知衰弱的影響,其中相乘模型采用ROTHMAN[12]提出的評價方法,將睡眠質量、抑郁癥狀與二者的乘積項同時納入多因素Logistic回歸模型加以驗證;相加模型采用Delta 法,并引入ANDERSSON等[13]編制的Excel表以計算評價指標超額危險度(RERI)、歸因比(AP)、交互作用指數(S)。雙側檢驗水準α=0.05。
2 結果
2.1 問卷回收情況 共發放問卷1 130份,回收有效問卷1 091份,有效回收率為96.6%。
2.2 老年人睡眠障礙、抑郁癥狀、認知衰弱情況 1 091例老年人存在睡眠障礙186例(17.0%),無睡眠障礙905例(83.0%);抑郁癥狀180例(16.5%),無抑郁癥狀911例(83.5%);認知衰弱89例(8.2%),非認知衰弱1 002例(91.8%)。存在睡眠障礙和抑郁癥狀的老年人共58例,其認知衰弱發生率為37.9%(22/58);存在睡眠障礙但無抑郁癥狀的老年人共128例,其認知衰弱發生率為14.1%(18/128);不存在睡眠障礙但存在抑郁癥狀的老年人共122例,其認知衰弱發生率為10.7%(13/122);不存在睡眠障礙也不存在抑郁癥狀的老年人共738例,其認知衰弱發生率為4.6%(36/783)。
2.3 不同一般資料老年人認知衰弱發生率比較 不同年齡、受教育程度、每日久坐時間>5 h情況、慢性病患病情況老年人認知衰弱發生率比較,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不同性別、家庭經濟水平老年人認知衰弱發生率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1)。
2.4 睡眠質量、抑郁癥狀與老年人發生認知衰弱的相關性 以老年人是否發生認知衰弱為因變量,以睡眠障礙、抑郁癥狀為自變量,控制混雜因素年齡、受教育程度、久坐時間、慢性病患病情況(賦值見表2),進行多因素Logistic回歸分析,結果顯示,睡眠障礙、抑郁癥狀是老年人發生認知衰弱的影響因素(P<0.05,見表3)。
2.5 基于多因素Logistic回歸分析的睡眠質量與抑郁癥狀對老年人發生認知衰弱的乘積交互作用分析 以老年人是否發生認知衰弱為因變量,以睡眠障礙、抑郁癥狀及二者乘積為自變量,控制混雜因素年齡、受教育程度、久坐時間、慢性病患病情況(賦值見表2),進行多因素Logistic回歸分析,結果顯示,睡眠障礙×抑郁癥狀對老年人發生認知衰弱不存在乘積交互作用(P>0.05,見表4)。

表1 不同一般資料老年人認知衰弱發生率比較〔n(%)〕Table 1 Comparison of cognitive frailty prevalence in elderly people by demographic factors

表2 老年人發生認知衰弱影響因素分析的多因素Logistic回歸分析賦值表Table 2 Assignment of the factors influencing cognitive frailty in elderly people included in the multivariate Logistic regression model

表3 老年人發生認知衰弱影響因素的多因素Logistic回歸分析Table 3 Multivariate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of the factors influencing cognitive frailty in elderly people

表4 基于多因素Logistic回歸分析的睡眠質量與抑郁癥狀對老年人發生認知衰弱的乘積交互作用Table 4 Multiplicative interactive effect of sleep quality and depressive symptoms on cognitive frailty in elderly people based on multivariate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2.6 基于多因素Logistic回歸分析的睡眠質量與抑郁癥狀對老年人發生認知衰弱的相加交互作用分析 以老年人是否發生認知衰弱為因變量,以睡眠障礙、抑郁癥狀為自變量,控制混雜因素年齡、受教育程度、久坐時間、慢性病患病情況(賦值見表2),進行多因素Logistic回歸分析,結果顯示,存在睡眠障礙和抑郁癥狀老年人發生認知衰弱的風險為不存在睡眠障礙且不存在抑郁癥狀老年人的10.536倍(見表5),RERI=6.998〔95%CI(0.384,13.612)〕,AP=0.664〔95%CI(0.405,0.924)〕,S=3.758〔95%CI(1.407,10.038)〕,即睡眠質量與抑郁癥狀對老年人發生認知衰弱具有相加交互作用。
3 討論
本研究中老年人認知衰弱檢出率為8.2%,略低于潘利妞等[14]的研究結果,明顯高于MA等[5]的研究結果,可能與所采用的測量工具和評估標準不同有關。目前國內針對認知衰弱流行病學特征的研究較少,今后可在住院或門診患者、社區及養老機構老年人等不同群體中開展大規模調查,并進行文獻的系統評價,進而為科學防控提供明確的依據。
本研究單因素分析結果顯示,不同年齡老年人認知衰弱發生率存在差異,可能與老年人中樞神經系統發生包括腦萎縮等在內的退行性改變、罹患其他疾病風險增高等因素有關[15]。需要注意的是本研究中受教育程度為大專/大學者的認知衰弱發生率較高(24.1%),與以往研究[4]中受教育程度越高則認知衰弱發生率越低的結論不一致。楊帆等[16]指出,由于MMSE所采用的截斷值與文化程度有關,高中以上學歷的截斷值高于初中及以下程度,被篩選為輕度認知功能損害的可能性更大,因而認知衰弱的檢出人數并未呈現理論上的隨教育程度升高而減少。本研究結果顯示,每日久坐時間>5 h的老年人認知衰弱檢出率明顯高于<5 h者,筆者檢索文獻發現目前尚無相關文獻報道,既往研究僅關注體育鍛煉與認知衰弱的關聯[4],在一定程度上忽視了久坐行為的影響。OLANREWAJU等[17]認為,久坐時間越長,機體可能會呈現內側顳葉厚度變薄、腦血流量異常、白質高信號(WMHV)增加、腦源性神經營養因子(BDNF)水平降低等變化,而上述變化與軀體衰弱、認知功能下降、平衡障礙等有關[15,18]。本研究結果還顯示,患慢性病的老年人認知衰弱發生率高于無慢性病者,提示今后應對該部分老年人進行重點篩查和及早干預。

表5 基于多因素Logistic回歸分析的睡眠質量與抑郁癥狀對老年人發生認知衰弱的相加交互作用分析Table 5 Additive interactive effect of sleep quality and depressive symptoms on cognitive frailty in elderly people based on multivariate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控制混雜因素年齡、受教育程度、久坐時間、慢性病患病情況后,多因素Logistic回歸分析結果顯示,睡眠障礙、抑郁癥狀是老年人發生認知衰弱的影響因素。孔令磷等[19]通過對社區老年2型糖尿病患者進行橫斷面調查發現,夜間睡眠時間不足者罹患認知衰弱的風險更高。既往研究表明睡眠障礙是衰弱和輕度認知功能損害的共同危險因素[1],而本研究結果提示可以將其推論為認知衰弱的預測變量。關于其具體機制可能與以下因素有關:首先,長期睡眠障礙可能誘發老年人心腦血管、軀體疾病及精神功能障礙等,進而損害機體的生理儲備,導致老年人脆弱性增加,出現肌肉減少等衰弱的諸多癥狀。同時,下丘腦-垂體-腎上腺軸(the hypothalamic-pituitary-adrenal axis,HPA軸)的過度激活以及睪酮、類胰島素生長因子-1(IGF-1)和生長激素等作為一種內分泌機制可能在睡眠質量與衰弱的關聯中起中間調節作用[20]。除此之外,睡眠障礙還可能通過炎性反應、血管改變、β-淀粉樣蛋白的清除障礙及Tau蛋白水平升高等途徑損害認知功能[21]。本研究中抑郁癥狀是老年人發生認知衰弱的危險因素的結果與KWAN等[22]研究結果相一致。RUAN等[23]認為抑郁情緒能夠導致機體白介素(IL)-6、腫瘤壞死因子α(TNF-α)、C反應蛋白(CRP)等細胞因子水平升高,而其介導的慢性炎性反應一方面作用于骨骼肌引起肌肉密度和質量下降,另一方面還可以通過血-腦脊液屏障造成腦內淀粉樣多肽前體蛋白增多,最終導致認知衰弱的發生[4]。
本研究交互作用分析結果顯示,睡眠質量與抑郁癥狀對老年人發生認知衰弱存在相加交互作用,筆者檢索文獻發現目前尚無相關報道。本研究從統計學角度系統闡述了睡眠質量、抑郁癥狀與認知衰弱三者間的關系,即同時存在睡眠障礙和抑郁癥狀的社區老年人患認知衰弱的風險遠高于睡眠障礙與抑郁癥狀二者單獨作用,提示對重點人群及時提供心理疏導和睡眠干預措施有助于降低其發生認知衰弱的可能性。
綜上所述,睡眠障礙、抑郁癥狀是老年人發生認知衰弱的影響因素,且睡眠質量與抑郁癥狀對老年人發生認知衰弱具有相加交互作用,值得社區篩查時注意。
作者貢獻:崔光輝、李少杰、尹永田負責文章的構思與研究設計,撰寫論文;崔光輝、李少杰、孔慶悅、陳莉軍開展問卷調查;崔光輝、李少杰、陳磊、劉馨謠進行數據錄入;崔光輝、李少杰負責數據處理,并分析解讀結果;孔慶悅、尹永田負責文章的質量控制與審核,監督管理。
本文無利益沖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