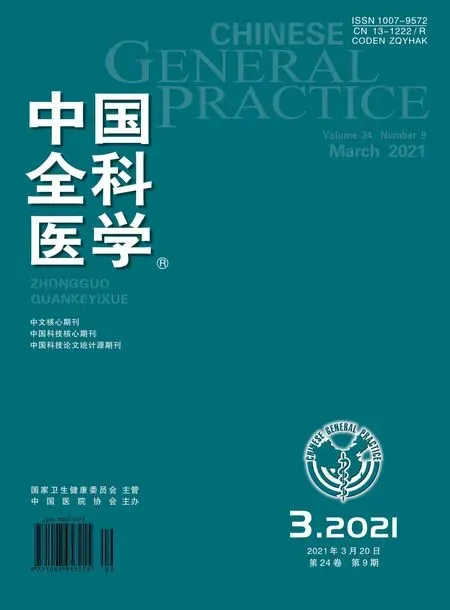兒童原發性1型高草酸尿癥一例報道并文獻復習
周旭東,趙興華,許長寶,李武學,趙永立
原發性1型高草酸尿癥(PH1)是一種常染色體隱性遺傳病。因AGXT基因發生突變,導致其編碼的肝臟特異性丙氨酸乙醛酸轉化酶(AGT)表達缺陷,乙醛酸轉氨生成甘氨酸減少,氧化生成草酸增加,草酸鹽沉積于腎臟及多個腎外器官,最終引發多發性和復發性草酸鈣結石、腎鈣質沉著癥[1]。由于臨床對PH1認識不足,常導致誤診、漏診,患者就診時常已進展為終末期腎病(ESRD)。本文報道了1例PH1患兒,其于鄭州大學第二附屬醫院初次就診時進行代謝評估,尿草酸水平>100 mg/24 h,排除其他疾病后考慮PH的診斷,并進一步通過AGXT基因測序明確診斷為PH1,目前正在進行為期6個月的干預治療及密切隨訪,現報道如下。
專家點評:
由于臨床對原發性1型高草酸尿癥(PH1)的認識不足而常導致誤診和漏診,不能及時或恰當治療,患兒常早期進展為終末期腎病。本文通過對1例6歲尿結石患兒的診治過程進行總結分析,提示針對兒童腎結石需要進行全面的代謝評估,以幫助查找遺傳病因,做到精準診斷及進一步的臨床治療和遺傳咨詢服務,對臨床相關病例有提示作用。
(首都醫科大學附屬北京婦產醫院 孔元原)
1 病例簡介
患兒,男,6歲,漢族,首發癥狀為排尿時突發尿痛,可見結石排出,2019-02-12至河南省平頂山市寶豐縣人民醫院行彩超檢查示:雙腎結石、右側輸尿管結石、右腎積水、膀胱結石。后為進一步治療于2019-02-22入住鄭州大學第二附屬醫院泌尿外科,期間未行特殊治療。患兒既往可見排尿突然中斷癥狀,生長發育正常。家族史:患兒父母非近親結婚,父系及母系三代無相同病史。
入院查體及輔助檢查:發育正常,營養中等,智力正常,身高130 cm,體質量24 kg;血壓105/77 mm Hg(1 mm Hg=0.133 kPa);右腎區壓痛、叩擊痛,未發現其他陽性體征。CT檢查結果:雙腎結石,右側輸尿管末端結石并右腎積水,膀胱結石(見圖1)。

圖1 患兒影像學檢查結果Figure 1 Imaging findings of the male child with primary hyperoxaluria type 1
實驗室檢查:血常規示白細胞計數5.9×109/L,血紅蛋白133 g/L,血小板403×109/L;尿常規示pH值6.0,紅細胞沉降率(+),尿蛋白陰性;血生化檢查示血尿酸385 μmol/L,血尿素氮4.56 mmol/L,血肌酐40 μmol/L,甲狀旁腺素35.6 ng/L。患兒共行6次24 h尿液成分分析,結果見圖2。結石成分分析為一水草酸鈣>95%。
基因測序分析:對患兒及其父母進行基因測序,患兒基因測序在AGXT基因第9外顯子上發現突變(c.864G>A:p.Trp288X),第2外顯子上亦發現突變(c.346G>A:p.Gly116Arg)。患兒母親基因測序檢測到AGXT基因第9外顯子突變(c.864G>A:p.Trp288X),患兒父親基因測序檢測到AGXT基因第2外顯子突變(c.346G>A:p.Gly116Arg)。根據美國醫學遺傳學與基因組學會(ACMG)的序列變異解釋標準和準則[2],突變(c.864G>A:p.Trp288X)為無義突變,可能為AGXT的致病變異;突變(c.346G>A:p.Gly116Arg)是來自患兒父親的錯義突變,其存在于轉氨酶的一個結構域,對AGT蛋白的功能很重要(見圖3)。本研究發現的兩個AGXT基因突變均為雜合突變,在氨基酸水平上,無義突變導致停止擴增而不是色氨酸形成(W288X),而錯義突變導致精氨酸形成而不是甘氨酸(G116R)。
診斷及治療:患兒的臨床表現符合PH1的臨床特點,結石成分分析為一水草酸鈣>95%,AGXT基因測序為復合雜合突變,臨床最終診斷為PH1。患兒在本院的治療分為3個階段:第1階段,囑患兒出院后大量飲水〔3 L·(m2)-1·d-1〕,口服維生素B6(5 mg·kg-1·d-1)以抑制草酸形成,并口服枸櫞酸鉀(0.1 mg·kg-1·d-1,早、中、晚3次服用)以堿化尿液并減少尿鈣排泄,抑制尿結石的形成;第2階段,在第1階段治療基礎上加用草酸降解酶30 g/d(早、中、晚3次溫水沖服),以降解草酸;第三階段,大量飲水〔3 L·(m2)-1·d-1〕,增加口服維生素B6劑量(10 mg·kg-1·d-1)以抑制草酸形成,并繼續口服枸櫞酸鉀(0.1 mg·kg-1·d-1,早、中、晚服用)以堿化尿液并減少尿鈣排泄,抑制尿結石的形成。
隨訪:由于患兒屬于早期發現的PH1,并積極配合治療,因此本院擬定的隨訪計劃如下:復查血常規、尿常規、肝功能、腎功能、電解質,4周/次,以防止發生泌尿系感染,同時監測肝、腎功能;復查低劑量泌尿系CT(平掃),4周/次,觀察患兒有無新發結石、腎鈣質沉積等;復查24 h尿液成分,4周/次,觀察患兒草酸、枸櫞酸、電解質水平,并根據患兒24 h尿液成分分析結果調整用藥。隨訪期間患兒血常規、尿常規、肝功能、腎功能、電解質水平均在參考范圍內。

圖2 患兒6次24 h尿液成分分析結果Figure 2 Results of 6 times of 24-hour urine composition analysis of this male child with primary hyperoxaluria type 1

圖3 患兒及其父母Sanger測序顯示AGXT基因突變Figure 3 Sanger sequencing of this male child patient and his parents revealed AGXT gene mutation
2 討論
原發性高草酸尿癥(PH)是一種常染色體隱性遺傳病。根據不同的基因突變位點可將PH分為3種亞型,其中PH1是由AGXT基因突變引起的,可導致維生素B6依賴的AGT表達缺陷[3];PH2是由GRHPR基因突變所導致的乙醛酸/羥基丙酮酸還原酶功能障礙[4];PH3是由HOGA1基因突變引起的,該基因編碼線粒體4-羥基-2-酮戊二酸醛縮酶[5]。PH1是發病率最高的一種亞型,約占PH的80%[6]。
在中歐地區,活產嬰兒中PH1的發病率為1/12萬[7];在北非和加里亞群島,PH1的發病率更高,這可能是由于近親結婚造成的[8];在歐洲和美國,PH1占兒童和青少年ESRD的比例不到1%[9]。PH1真正的發病原因不清楚,并且是否存在地域性差異仍不確定,但早期的觀察研究還是很有意義的[10]。
人體內草酸不能被代謝吸收,只能作為代謝終產物從腎臟排出。草酸鹽可以在腎小球內自由濾過,也可以由腎小管分泌。在PH1患者中,由于內源性草酸產生過多,草酸鹽在尿液中過飽和,導致腎小管管腔內形成晶體和復合物,而一些晶體會聚集于腎小管細胞表面,最終形成腎結石;另一些晶體會被吸收進腎小管細胞中,并逐漸遷移到腎間質,最終形成腎鈣質沉著癥。不斷進展的腎鈣質沉著癥和反復發作的泌尿系結石會引起泌尿系感染和梗阻性腎病等并發癥。當腎功能進一步損害、估算腎小球濾過率(eGFR)下降至30~40 ml·min-1·(1.73 m2)-1時,草酸鹽不能通過腎臟完全排出體外,血漿草酸鹽濃度逐漸升高,并迅速達到30 μmol/L。草酸會沉積于各種腎外組織器官,包括心肌、骨、皮膚、血管壁、視網膜、中樞神經系統等,長期影響包括心肌病、骨痛、骨鈣化、抗藥性貧血、皮膚潰瘍、血管病變、視網膜病變、周圍神經病變等在內的疾病[11]。
臨床早期診斷PH1至關重要,便于早期開始干預治療。對于泌尿系結石患者,任何年齡段均應行24 h尿液成分分析。PH1患者的代謝指標是在無高草酸尿其他病因情況下,尿草酸水平>50 mg/24 h。目前原發性與繼發性高草酸尿癥沒有明確的界限,尿草酸水平>70 mg/24 h通常認為是代謝因素所致,但也有一些繼發性疾病,如克羅恩病、短腸綜合征、胰腺功能不全等疾病患者尿草酸水平可以>100 mg/24 h[12]。尿草酸水平在50~70 mg/24 h也不能排除PH,如果患者年齡較小、有復發性腎結石、腎鈣質沉著癥則應行進一步檢查。如果腎功能正常,血漿草酸水平對診斷沒有幫助,但隨著eGFR的下降,血漿草酸水平會上升。血漿草酸水平>100 μmol/L可能來源于PH1,但目前沒有明確的方法來區分是PH1造成還是腎衰竭造成。結石成分中一水草酸鈣>95%是PH1患者的另一重要特征[13]。肝穿刺活檢是診斷PH1的傳統方法,也是診斷PH1的金標準[14],但肝穿刺活檢為有創性檢查,大多數患者不能接受。分子基因檢測已經逐漸取代肝穿刺活檢成為首選的PH1診斷方法,目前已經發現PH1患者的AGXT基因至少有178個突變位點[15],其中錯義突變最為常見;AGXT外顯子及其剪切區直接測序是診斷PH1的重要和有效手段[13],存在致病純合或者雜合突變可以確診[16]。隨著分子生物學和基因檢測技術的發展,PH1雖可以明確診斷,但是PH1的早期篩查仍至關重要。
本例患兒6歲發病,以發現泌尿系結石就診于本院,尿液成分分析提示尿草酸水平>100 mg/24 h,結石成分分析為一水草酸鈣>95%,考慮患兒處于PH1高發病年齡段,且各項檢查結果均比較典型,因此高度懷疑患兒為PH1,遂進一步行基因測序,結果提示患兒存在引起PH1的兩個AGXT基因突變(c.346G>A:p.Gly116Arg;c.864G>A:p.Trp288X),其中一個突變為新的無義突變(c.864G>A:p.Trp288X),而另一個突變(c.864G>A:p.Trp288X)為錯義突變。本次對患兒進行基因測序檢測到的這種新的無義突變可能對中國PH1患兒的治療有重要意義。結合患兒的臨床表現和基因測序結果,PH1診斷明確,無須再行肝穿刺檢查。
關于PH1的治療,目前主要是根據PH1患者疾病發展階段執行個體化治療。在PH1發現早期以保守治療為主,包括大量飲水〔2~3 L·(m2)-1·d-1〕以防止草酸過飽和[17];口服維生素B6以減少草酸生物合成,推薦劑量為初始5 mg·kg-1·d-1,逐漸增加劑量但不超過20 mg·kg-1·d-1,且至少使用3 個月[17];口服枸櫞酸鹽(100~150 mg·kg-1·d-1,早、中、晚服用)以堿化尿液并減少尿鈣排泄[18]。當患者出現透析指征但又不能行肝腎聯合移植時,推薦高效透析,血液透析、腹膜透析或者兩者聯合以及高通量透析均可[19]。隨著PH1病情進展,腎功能進一步惡化,到慢性腎臟病4、5期時,現有的透析方案已經不能快速清除患者體內產生的過量草酸,因此,器官移植成為治療該疾病的另一種選擇,目前肝腎聯合移植的療效最好[19],不推薦單獨的腎移植,因為單獨的腎移植具有較高的復發風險[20]。近年來,隨著分子生物學技術以及基因技術的發展,關于PH1的治療方案也層出不窮。利用肝細胞移植可以恢復AGT活性[21];由于PH1是單基因致病,重組基因療法尋找替代酶也可用于該病的治療[22]。未來可以通過聯合各種治療方案、早期干預以減少PH1患者肝臟草酸的產生、草酸在腎臟以及腎外器官的沉積,減輕患者痛苦,避免行器官移植術[23]。本例患兒屬于PH1早期,給予排石治療后開始進行針對PH1的個體化治療方案,包括大量飲水、口服枸櫞酸鉀以堿化尿液并減少尿鈣排泄、逐漸增加維生素B6劑量以減少草酸生物合成,并且在治療過程中嘗試使用草酸降解酶以降解草酸,后發現草酸降解酶對該患兒降解草酸無明顯作用,遂暫停應用草酸降解酶。在患兒治療及隨訪過程中,其腎功能指標均在參考范圍內,由于患兒的依從性較差,枸櫞酸鹽未按照要求服用,復查24 h尿液成分中枸櫞酸水平波動較大,但隨訪期間24 h尿液成分中草酸水平波動在30%以內。
綜上所述,對于兒童時期發現的泌尿系結石,均應行全面的代謝評估,當24 h尿草酸水平高于參考范圍上限(即>50 mg/24 h),排除腸源性疾病后均應考慮到PH[19]。AGXT基因測序目前已經取代肝穿刺活檢成為診斷PH1的首選方法,應注意對已經確診的患者家屬進行基因測序[20]。一旦基因測序診斷確診為PH1,應該積極制定個性化的治療方案,并密切隨訪;如果患者的腎功能已經下降,則應該考慮合適的器官移植方案[6]。
作者貢獻:周旭東進行文章的構思與設計、可行性分析,并負責論文撰寫;周旭東、李武學、趙永立負責資料的收集與整理;趙興華負責論文質量控制及校審,對文章整體負責、監督管理;許長寶負責論文的修訂和質量控制。
本文無利益沖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