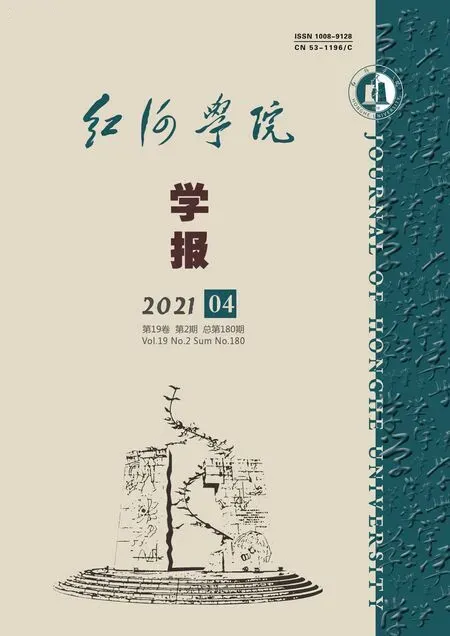基于文化差異理論探究《霧都孤兒》翻譯的共情困境
劉本英
(遼寧對外經貿學院,遼寧大連 116052)
1972年,霍夫斯泰德教授以來自不同國家的十一萬六千人作為研究樣本,探究造成出文化差異理論的五個重要元素,即權力距離;長期、短期取向差異;男性、女性選擇差異;個人主義、集體主義差異及不確定性規避。霍夫斯泰德的文化差異理論為跨文化交流研究、翻譯研究提供了理論依據。全球化背景下,我國民眾閱讀英美文學成為常態,學界對現行英美文學譯本的翻譯研究也逐步深化。《霧都孤兒》作為優秀的英美文學作品,并在我國傳播度較廣,甚至被列入教育部新課標的必讀書目。由此,以《霧都孤兒》為例進行翻譯研究具有代表性,在文化差異理論下探究《霧都孤兒》的共情翻譯,為英美文學作品的共情意譯發展提供良好范例。
一 文獻綜述
《霧都孤兒》在我國譯文版本有數十余種,其中林紓、榮如德、黃雨石的譯本流傳度較高。在《霧都孤兒》漢化流傳較廣的背景下,眾多學者開始對《霧都孤兒》的漢化翻譯內容進行探究,旨在通過分析《霧都孤兒》譯文的優缺點,提出完善英美文學作品翻譯的有機路徑,從而推進英美文學在我國各個階層的有效傳播。陽英以翻譯目的論為切入點,對比分析了榮如德和祈熾版本《霧都孤兒》中的情感描寫,并提出了譯者需在一定程度上遏制自身“譯者主體性”的觀點。有學者指出,基于翻譯目的論中“受眾是影響翻譯的重要因素”的觀點,譯者需具備“讀者意識”、以讀者的眼光看待自己的翻譯作品。陽英的研究促進譯者深入群眾、以群眾的眼光翻譯出接地氣的語篇,推進英美文學在我國的異化翻譯及本土化傳播。[1]王丹丹以語用翻譯視角為切入點,從詞語和句子等不同層面比較分析了榮如德及何文安版本的《霧都孤兒》,得出了不同譯本所反映的譯者思維不同、譯者主觀思想會影響文本翻譯的結論。基于此,王丹丹提出翻譯文學作品時,譯者需在摸清作品文化背景的基礎上,把握現階段時代特征的優化翻譯路徑。[2]狄麗卿以翻譯銜接手段為切入點,指出《霧都孤兒》譯文中銜接語重復或銜接不當等問題,進而提出整合語篇銜接詞以提高文本通順度的優化翻譯路徑。[3]陳超鵬及高存以圖里翻譯規范理論為切入點,從預前規范、操作規范等方面整合《霧都孤兒》譯文語言文化范式,為英美文化作品的翻譯提供了創新視角。[4]
綜上,學者們在探討《霧都孤兒》的翻譯路徑時,很少有人以霍夫斯泰德文化維度理論為切入點分析《霧都孤兒》的共情翻譯路徑。因此,基于文化差異理論探析《霧都孤兒》的共情困境具有創新性及重要意義。
二 文化差異理論下《霧都孤兒》翻譯的共情困境
(一)集體主義維度下讀者共情點激發困境
“個人主義與集體主義的差異性”是構成文化差異理論的重要因素之一。霍夫斯泰德認為,相較于崇尚個人主義、個人自由權的美國,日本、中國等亞洲國家的人,更崇尚能夠參與社會活動、建立群體關系的集體主義。《霧都孤兒》通過描寫奧利弗·崔斯特的苦難與挫折,諷刺了英國工業革命背景下英國資產階級的丑惡,奧利弗·崔斯特便是“個人主義維度”下的“個人英雄”;而刻畫奧利弗的狄更斯,更是抨擊英國腐敗社會的“時代英雄”。
1918年林紓在《霧都孤兒》譯本序章中寫到“希望中國也能有狄更斯一樣的人”,直接說明了譯者的主觀思想。由此,林紓的譯文多側重于突出歐美國家“個人英雄主義”,旨在以此激發國民共情,改變當時中國的風貌。然而,林紓譯本的部分譯文過于夸張,甚至將原文意思進行增譯或改譯,效果適得其反,本身就作為集體主義者的國內受眾的共情點難以被激發。如林紓將“he ought to laugh or cry”譯為“他驚如木偶”,其本意是想描寫奧列佛看到理事會高層階級的人時,內心的“不知該哭還是該笑”的激動和矛盾,但“驚如木偶”卻將主人公的情緒進行了改變,從復雜的矛盾心理譯轉為單一的驚訝情緒,無法通過階級矛盾來激發當時也處于階級斗爭卻崇尚集體主義的國內受眾。此后,黃雨石、榮如德等在翻譯時采取了序章交代作品文化背景、正文中增加注釋等翻譯手法,旨在讓讀者盡可能了解作品背景以提高共情感受,然而收效甚微。閆文珍認為,在集體主義思想下,我國讀者對于英美文學中的“個人主義”無法產生共情同感,甚至無法理解作品中人物的做法。[5]歸根結底,是受眾在自身的集體主義思想框架視域下解讀外國文學思想。由此可見,個人主義與集體主義的文化差異性導致國內讀者共情失調,國內讀者共情點難以被激發。
(二)權力距離維度下受眾階層共情差異
“權力距離”指不同社會的權力劃分程度,以及社會群體對社會中權力劃分情況的接受程度。一方面,權力距離有高低之分,《霧都孤兒》所描繪的英國社會便是“高權力距離”的典型,權力分級十分嚴重,貴族享有特權,人民權力則被壓榨。我國作為人民當家作主的社會主義國家,權力直接由人民行使,人人平等,是“低權力距離”的代表。由此,在不同權力距離維度下,我國受眾對《霧都孤兒》書中的共情感受度較低,即有部分共情感受,但因文化差異無法達到國外受眾更為深度的“感同身受”。如譯者何文安將原作中的“touching his fur cap”直接翻譯為“他碰了碰自己的皮帽子”,“碰帽子”這一舉動在禮儀繁瑣、階級劃分明顯的上世紀英國,是低權力人群向高權力人群行禮的表現。我國讀者在讀譯文時,因不了解英國上世紀資產階級社會的劃分狀況以及各類禮儀,對于原作中的動作描寫、心理描寫了解不到位,導致無法產生共情感受。另一方面,文化差異理論中的權力距離維度闡明,社會形態無論是民主還是專制制度,管理者和決策者與員工(即被管理人群)的思維形態都具有差異性。國內受眾無階級劃分但有階層劃分,從事不同行業、薪資待遇不同的群體,在閱讀《霧都孤兒》時所別觸發的共情點都各不相同。對于管理階層的讀者來說,其對底層人物奧列弗的境遇及其選擇犯罪的行為難以產生共情心理。
(三)不確定性規避下譯文還原度困境
不確定性規避指的是人們在社會生活中,所能感受到的不確定性事物的威脅程度。霍夫斯泰德專門指出中國屬于不確定性規避程度較低的國家。《霧都孤兒》所描繪的上世紀英國犯罪率較高、階級矛盾明顯,屬于具有“高度不確定性”的社會。在此背景下,以狄更斯為首的文化精英們通過文學作品建構意識、提高民族認同。狄更斯在構建故事時所用的語言描寫、心理描寫較為大膽和直白。[6]《霧都孤兒》包含犯罪、童工、幫派、黑色交易等內容,我國譯者在對作品進行文化尺度上的禁忌處理時,以大幅度減譯、換譯等方式處理原文,譯文的還原度較低。譯文作為原文的“二次創作”,本身就無法完全還原原文語境,大幅度減譯、換譯等方式更無法激發讀者的共情感受。如青少版本的《霧都孤兒》譯本,以概括性的粗略描寫代替原作中對犯罪行為的細節描寫。在部分成人譯本中,譯者也以異化翻譯法,規避尺度,削弱了原文的諷刺意味。如在原作二十二章《破門盜竊》中,譯者榮如德將形容奧列弗的“hopeful pupils”一詞翻譯為“高足”,譯者何文安將其翻譯為“高徒”,譯者黃雨石將其翻譯為“有希望的學生”,相較于前兩者,黃雨石“有希望的學生”更加將竊賊對培養出小竊賊而沾沾自喜、得意洋洋的諷刺意味體現出來。進行犯罪卻說“有希望”,體現狄更斯對英國黑暗腐朽社會下資產階級掌權,人民只能通過盜竊來果腹的批判。榮如德和何文安譯本的“高足”“高徒”缺少“希望”一詞,削弱了諷刺意味,對原作還原度較低,讀者共情體驗受阻。
三 《霧都孤兒》共情翻譯的完善路徑
(一)合理使用銜接術語
鑒于集體主義維度下讀者共情點激發的困境,通過合理使用翻譯銜接術語的翻譯方法,完善翻譯中的情感表達,弱化個體主義和集體主義的文化差異,促進讀者在閱讀時的自我情緒代入,可以提高讀者共情體驗。第一,適當增加結構銜接術語以完善中心思想。在翻譯中增加所以、因此、然而、但是、由于等結構銜接詞,增加上下文語篇的連貫性,讓讀者對于事件的前因后果更加明晰。第二,多元變換作品中的指稱銜接術語,促進讀者的情緒代入,甚至能夠讓讀者自我代入書中人物,以提高共情體驗。[7]以榮如德和何文安譯本為例,榮如德譯本中將“Oliver”通篇均直接譯為奧列佛,而何文安譯本以“小伙子”“小家伙”“這個小賊”等指代奧列佛,更契合原作中奧列佛所處的情境,增加讀者的心理代入感。第三,使用主被動變換銜接方法,進一步完善譯文的準確性,推進讀者以譯者甚至作者視域去理解作品,感受人物情緒。
(二)注重多元人物翻譯
《霧都孤兒》原著的書名《Oliver Twist》就直接說明了主人公的重要地位。緣于此,許多譯者在進行“二次創作”時,往往多注重主人公的情緒心理描寫,忽略了其他人物的情感翻譯表達。如許多青少年譯本直接將費金這一人物刻畫成完全負面的惡人,沒有確切表達出費金這一反派人物的人格特色。基于權力距離下受眾階層不同、共情差異也不同的情況,從注重奧列佛一人的塑造,轉為注重《霧都孤兒》中正派、反面等多元人物翻譯的“二次創作”,以激發不同階層讀者對《霧都孤兒》中不同人物的情感共鳴,將以往讀者在閱讀時自動代入“主人公”的意識形態,轉變為讀者能夠代入其他人物甚至反派人物的意識形態,以提高讀者與原著人物的共鳴感。[8]在注重其他人物翻譯時,可采用增譯的形式刻畫人物,如原文“the short man seems to have made sure that he has not for gotten ”中的“ he has not for gotten”,榮如德將其譯為“他沒有忘記他的處境”,在原著基礎上加了“他的處境”四個字,既沒有改變原文所指意思,又以增譯的形式完善了譯文對配角人物的刻畫。
(三)適當減譯或模糊翻譯
文化差異理論下,我國與《霧都孤兒》刻畫的上世紀英國屬于“不確定性規避因素”截然相反的國家。李亞蕾認為在翻譯中“創設場景”來將讀者代入作品,可提升原文準確度的翻譯方法。[9]基于此,在我國文化創作規范和翻譯規范下,譯者可通過適當減譯或模糊翻譯的形式提高譯文準確性,從而提高原著的還原度,以增強低度不確定性受眾(國內讀者)對高度不確定性場所(原著場景)的理解度。一方面,契合我國創作規范詞庫,針對青少年版本的《霧都孤兒》進行適當減譯而非大幅度減譯。另一方面,對于部分原著較為模糊的語篇,譯者多以自身主觀思維進行理解性翻譯,不利于對原著“高度不確定性”場景的構建。基于此,在遵循原文的基礎上以模糊翻譯的方法設置不確定性場景,推進讀者對原著的理解。除此之外,“一千個讀者有一千個哈姆雷特”,模糊翻譯中的“不確定性”,能夠促使讀者對原著形成自己的感悟和理解,提高自身的文學素養,從而深化我國受眾在閱讀《霧都孤兒》時的共情體驗。
四 結語
翻譯作為原著的“二次創作”,是讀者閱讀作品是否能夠提高共情觀感、理解原著的關鍵。通過合理使用銜接術語、多元完善作品中小人物的形象刻畫等翻譯方法,以更為貼合原著的“作者/譯者思維”去理解把握作品,增加讀者在閱讀時的共情體驗,提升學素養,使《霧都孤兒》的文學價值得以充分體現。對《霧都孤兒》的共情翻譯路徑探討也為英美文學作品在我國的翻譯實踐提供良好借鑒,推進了英美文化研究及跨文化交流的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