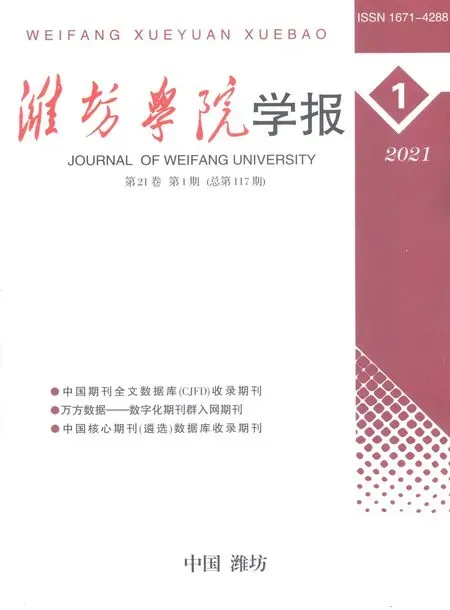莫言傳記研究
孫曉晴
(山東大學(xué),濟(jì)南 250100)
2012 年莫言問(wèn)鼎諾貝爾文學(xué)獎(jiǎng)引起國(guó)內(nèi)外關(guān)注,國(guó)內(nèi)學(xué)界更是掀起了一場(chǎng)“莫言熱”,莫言研究進(jìn)入一個(gè)新的高度,與此同時(shí)關(guān)注作家生平與創(chuàng)作的傳記寫(xiě)作也提上日程。簡(jiǎn)而言之,“傳記是某一個(gè)人物的生平的經(jīng)歷”[1],按照作者與傳主的關(guān)系,傳記可分為自傳和他傳,進(jìn)行傳記考察應(yīng)秉承“自傳優(yōu)先,他傳靠后”[2]的原則,但目前莫言沒(méi)有嚴(yán)格意義上的自傳、回憶錄,只有《莫言自述》[3]《我的中學(xué)時(shí)代》[4]等具有自傳性質(zhì)的訪談、散文作品。現(xiàn)有的莫言傳記基本可歸之于他傳:早在2008 年便已有葉開(kāi)的《莫言評(píng)傳》,莫言獲諾貝爾文學(xué)獎(jiǎng)后,更多傳記類(lèi)性質(zhì)的文字、著作相繼面世,其中包括王玉的《莫言評(píng)傳》,陶林、許海峰的《莫言的故事》,項(xiàng)星主編的《從紅高粱地走出的文壇巨匠——莫言的故事》以及程光煒的《莫言家世考證》系列等。
陶林、許海峰所著的《莫言的故事》以及項(xiàng)星主編的《從紅高粱地走出的文壇巨匠——莫言的故事》屬于面向青少年的通俗化傳記,內(nèi)容相對(duì)單薄;《莫言家世考證》系列是程光煒于2014-2016年間發(fā)表的十篇論文,文字雖然具備了傳記的基礎(chǔ)內(nèi)容要素,但作者并非追求整全傳記的書(shū)寫(xiě),僅就莫言的家庭、教育等十個(gè)專(zhuān)題進(jìn)行梳理考證,因此它更多是一份具有史料意義的考證資料。目前相對(duì)系統(tǒng)的莫言傳記有葉開(kāi)的《莫言評(píng)傳》和王玉的《莫言評(píng)傳》。莫言傳記在數(shù)量上并不取得優(yōu)勢(shì),但在傳記內(nèi)容、傳記性質(zhì)等方面已經(jīng)具備一定的代表性。目前學(xué)界對(duì)莫言傳記的關(guān)注甚少:或通過(guò)序言、后記對(duì)傳記作品做簡(jiǎn)單介紹[5],或是讀后感性質(zhì)的評(píng)論[6],沒(méi)有形成系統(tǒng)性的專(zhuān)論,也沒(méi)有涉及更為深入的傳記文學(xué)理論的探討。本文以兩部《莫言評(píng)傳》為研究對(duì)象,分析傳記特點(diǎn)的同時(shí),對(duì)比互現(xiàn),明晰得失,關(guān)照傳記寫(xiě)作的理論原則問(wèn)題,為未來(lái)莫言傳記寫(xiě)作甚至整體傳記寫(xiě)作生態(tài)提供可能的借鑒,同時(shí)也為中國(guó)傳記理論建設(shè)提供部分個(gè)案。
一、真實(shí)、客觀與文學(xué)性——豐贍傳材、考辨與虛構(gòu)
對(duì)傳主生平的敘述和對(duì)傳主個(gè)性的刻畫(huà)是學(xué)術(shù)界公認(rèn)的現(xiàn)代傳記的基本要素和核心要素,而對(duì)二者的展示首先應(yīng)最大限度保證真實(shí)性與客觀性。傳記寫(xiě)作的基礎(chǔ)是歷史,歷史書(shū)寫(xiě)最重要的原則是“真實(shí)”,而“真實(shí)”也正是傳記的生命。歷史是無(wú)法重現(xiàn)、不可盡述的,傳記的真實(shí)性也是相對(duì)的,傳記的真實(shí)性要求最大限度展現(xiàn)傳主的真實(shí)生平、刻畫(huà)傳主真實(shí)性格。兩部《莫言評(píng)傳》以內(nèi)容劃分都屬于學(xué)術(shù)傳記,學(xué)術(shù)傳記是傳記同學(xué)術(shù)的結(jié)合,也是人文同科學(xué)的結(jié)合,對(duì)傳記書(shū)寫(xiě)的真實(shí)性、客觀性都有更高的要求。最大限度書(shū)寫(xiě)傳記真實(shí),傳記作者要追求一手傳材的豐瞻全面,并運(yùn)用科學(xué)的方法對(duì)傳材考證辨?zhèn)危未嬲妫瑫r(shí)作者應(yīng)秉持公正客觀的態(tài)度,不虛美,不隱惡,構(gòu)建傳記真相。此外,任何文學(xué)性的虛構(gòu)都需要有所依據(jù),不違背真實(shí)性原則。
(一)豐瞻全面的一手傳材
傳記真實(shí)性的基礎(chǔ)保障是傳材的豐富完整。傳記作者應(yīng)全面關(guān)注傳主生命中的初學(xué)期、學(xué)習(xí)期、活躍期和隱退期[7],注重影響傳主發(fā)展方向、帶來(lái)傳主生活道路和心理世界轉(zhuǎn)變的傳記節(jié)點(diǎn)①傳記節(jié)點(diǎn)指?jìng)髦饕簧杏绊懙剿拿\(yùn),或是能夠說(shuō)明他的命運(yùn)的那些重要事件。楊正潤(rùn):《現(xiàn)代傳記學(xué)》,南京.南京大學(xué)出版社,2009 年版,第 525 頁(yè)。。同時(shí),傳主并非孤立存在,而是與周?chē)氖澜缑芮新?lián)系,因此,傳記敘述也應(yīng)當(dāng)關(guān)注傳主物質(zhì)和精神的生存環(huán)境,在社會(huì)生活、歷史情境和文化結(jié)構(gòu)中敘寫(xiě)傳主的人生和個(gè)性發(fā)展。如此才能更好地展示傳主生平,塑造全面真實(shí)的傳主形象,而對(duì)歷史情境、時(shí)代風(fēng)潮的關(guān)照,亦可進(jìn)一步透視時(shí)代變遷,賦予傳記書(shū)寫(xiě)以更加廣闊的視野。
作為首部莫言傳記,葉開(kāi)的《莫言評(píng)傳》在傳材搜集上的奠基性意義是不容置疑的。葉著2008年由河南文藝出版社出版,共計(jì)30.1 萬(wàn)字。全書(shū)分為五章,按時(shí)域階段對(duì)莫言的生平及創(chuàng)作進(jìn)行介紹與述評(píng)。第一章“饑餓年代”,從莫言的出生寫(xiě)起,主要敘述莫言家族、生活環(huán)境以及莫言童年的饑餓經(jīng)驗(yàn)和曖昧身份。第二章“求知年代”,圍繞莫言小學(xué)生涯的人和事展開(kāi),并敘莫言的閱讀經(jīng)歷。第三章“出走年代”,從莫言輟學(xué)開(kāi)始打工歲月一直敘述到莫言從軍入伍成為“古董級(jí)”戰(zhàn)士。第四章“激情年代”,從莫言“艱難的提干”寫(xiě)至其考入解放軍藝術(shù)學(xué)院發(fā)表《透明的紅蘿卜》《枯河》。第五章“收獲年代”,集中敘述了莫言從《紅高粱》到《豐乳肥臀》的創(chuàng)作歷程。葉著較為全面地關(guān)注到了莫言的初學(xué)期、學(xué)習(xí)期和活躍期,對(duì)莫言人生中的重要節(jié)點(diǎn)如輟學(xué)、入伍、文壇嶄露頭角等都有細(xì)致生動(dòng)的呈現(xiàn)。在展示傳主生存環(huán)境方面,葉開(kāi)描繪莫言家鄉(xiāng)“高密東北鄉(xiāng)”特殊的自然地理環(huán)境,同時(shí)也對(duì)莫言所處的時(shí)代語(yǔ)境投以關(guān)懷,并將個(gè)人浮沉與時(shí)代“大事”有機(jī)串聯(lián),如談及莫言的《酒國(guó)》之“生不逢時(shí)”時(shí),作者便分析了20 世紀(jì)90 年代初期文學(xué)領(lǐng)域的“陜軍東征”[8]。此外,葉著收錄50 余幅莫言本人提供的不同時(shí)期的照片,“圖像比任何人所能想象的都要真實(shí)”[9],這些直觀、真切的照片圖像為讀者走近莫言提供了豐富的視覺(jué)資料。然而,葉著在傳材搜集方面也非盡善盡美。葉開(kāi)在章節(jié)注釋中寫(xiě)到:“本書(shū)寫(xiě)到的就是三分之一個(gè)莫言,其他三分之一是他的家庭和愛(ài)情,還有三分之一大概就是詩(shī)人莫言。”[10]如作者所言,葉著中傳主的家庭、愛(ài)情和詩(shī)文都是空缺的。家庭、愛(ài)情是莫言人生的重要切面,詩(shī)文則蘊(yùn)含了莫言的思想感情,此三者的欠缺不利于立體傳主的塑造;再者,由于創(chuàng)作時(shí)間限制,葉開(kāi)對(duì)莫言后期的創(chuàng)作如《生死疲勞》《檀香刑》等皆一筆帶過(guò),莫言2008 年后的生活、創(chuàng)作更未納入討論范圍之內(nèi),這種缺失是為當(dāng)代具有“生長(zhǎng)性”的作家作傳所面臨的無(wú)法避免的困境,無(wú)可厚非,卻不能不謂一憾事。總體而言,在傳材搜集上,葉開(kāi)《莫言評(píng)傳》具有基礎(chǔ)性意義,卻仍有空白需要填補(bǔ)。
王玉的《莫言評(píng)傳》在史料方面更為全面、翔實(shí)。王著2014 年由清華大學(xué)出版社出版,共計(jì)60.7 萬(wàn)字,呈現(xiàn)出十分厚重的面貌。全書(shū)分五章,系統(tǒng)地介紹了莫言的生平及創(chuàng)作。第一章“一捧拷問(wèn)時(shí)間的鄉(xiāng)土——莫言的意義”,主要考證莫言與“尋根”“魔幻現(xiàn)實(shí)主義”等文學(xué)流派的關(guān)系。第二章“一種屬于土地的歸去來(lái)——莫言的生平”,分三小節(jié)講述了圍繞在莫言身邊的人,莫言的讀書(shū)之路、軍隊(duì)生活、求學(xué)歷程以及莫言人生中的幾個(gè)重要節(jié)點(diǎn)。第三章“一個(gè)高密東北鄉(xiāng)農(nóng)民的叛逆——莫言的作品”,全面解讀了莫言的小說(shuō)、散文、影視劇本。第四章“一場(chǎng)關(guān)于‘饑餓、孤獨(dú)、情愫’的盛宴——莫言的小說(shuō)評(píng)析”,在關(guān)照莫言生平的基礎(chǔ)上再分析莫言的作品。第五章“一篇‘諾貝爾文學(xué)獎(jiǎng)’的十年寓言——莫言的藝術(shù)成就”,探究了莫言作品中的“陌生化”“審丑意識(shí)”“女性書(shū)寫(xiě)”等諸多課題。在葉著中出現(xiàn)的人物、事件、時(shí)代背景、文壇氣象等經(jīng)過(guò)王玉補(bǔ)充拓展后變得更加豐滿、立體。在作品評(píng)介范圍上,王玉對(duì)莫言的十一部長(zhǎng)篇小說(shuō)都有獨(dú)到細(xì)致的解讀,也關(guān)照到了莫言《島上的風(fēng)》《丑兵》等相對(duì)冷門(mén)的小說(shuō)以及小說(shuō)之外的散文、演講、話劇影視作品等,作者還對(duì)莫言作品的譯介情況進(jìn)行了詳細(xì)梳理,在史料搜集方面頗見(jiàn)功力。但在王著中,部分?jǐn)⑹鲇捎谌狈σ皇植牧希捎脗饔浥c作品互補(bǔ)對(duì)參的方式,莫言的小說(shuō)、散文成為作者的素材庫(kù)。②如以莫言小說(shuō)《丑兵》為參照描寫(xiě)莫言外貌。莫言是習(xí)慣拿記憶說(shuō)話的人,他的散文及部分小說(shuō)一定程度上映照出他的人生,流露著他真實(shí)的感情,因此這種互補(bǔ)對(duì)參的方式有其合理性。盡管如此,作為傳記作者,將傳主作品作為一手史料入傳時(shí),事實(shí)的考證與核定環(huán)節(jié)不能省略,唯有如此方能“去偽存真”,這一點(diǎn)是王著所忽略的。
整體而言,兩部《莫言評(píng)傳》在傳材搜集方面皆有建樹(shù),但由于時(shí)間以及作者本身的限制,莫言傳記書(shū)寫(xiě)仍有拓展空間:其一,盡管葉著和王著對(duì)莫言“大學(xué)生活”都有涉及,但都未做深入展開(kāi),無(wú)論是解放軍藝術(shù)學(xué)院文學(xué)系的學(xué)習(xí),還是北京師范大學(xué)魯迅文學(xué)院創(chuàng)作研究生班的進(jìn)修,對(duì)莫言創(chuàng)作的影響都是非常關(guān)鍵的,傳記作者應(yīng)當(dāng)給予更多的關(guān)照。其二,兩部傳記寫(xiě)至莫言中年階段后,便呈現(xiàn)很明顯的“作品評(píng)析”壓倒“傳主生活”的傾向,他們更多關(guān)注的是“作為作家”的莫言,而非“作為人”的莫言,莫言“作家”身份之外的生活傳記作者鮮有涉及。這固然有道德上的考慮,但道德限制內(nèi)的傳材發(fā)掘卻不應(yīng)忽視。莫言作為山東大學(xué)教授與弟子間的交往,莫言與舊友、同學(xué)的往來(lái),莫言與讀者的互動(dòng)都是傳主生活中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體現(xiàn)傳主性格不可或缺的部分,傳記作者應(yīng)當(dāng)給予關(guān)注。其三,兩位傳記作者對(duì)傳主背后的文化結(jié)構(gòu)的關(guān)注有所欠缺。文化結(jié)構(gòu)是處于社會(huì)內(nèi)部的傳統(tǒng)和時(shí)代精神的結(jié)合,相比于外在的政治經(jīng)濟(jì)因素,它對(duì)傳主的影響是隱形的,但它決定了人的內(nèi)在氣質(zhì),莫言出生于山東高密——齊文化與魯文化的交匯地,齊魯文化作為一種文化結(jié)構(gòu),對(duì)莫言的生活做派、作品創(chuàng)作的影響是不可忽視的。這些或可作為莫言傳記寫(xiě)作的生長(zhǎng)點(diǎn)。
(二)傳材考證和校訂辨?zhèn)?/h3>
傳材搜集之后,考證辨?zhèn)问莻饔涀髡叩诙?xiàng)必要工作。在大量的傳材中,除了時(shí)間、地點(diǎn)、地理環(huán)境等客觀的事實(shí),很多記載都帶有一定主觀性,即使是傳主個(gè)人的回憶、敘述也可能因?yàn)檫z忘等原因存在某些偏差或錯(cuò)誤,細(xì)致的考證體現(xiàn)了傳記作者的嚴(yán)謹(jǐn)態(tài)度,也是構(gòu)建傳記真實(shí)的基礎(chǔ)性工作。
盡管葉開(kāi)一再表示“我虛構(gòu)了莫言”,但這并不違背他對(duì)傳材校訂辨?zhèn)蔚膶徤鲬B(tài)度。傳記第一章作者便考證了莫言的出生日期①葉開(kāi)考證莫言出生于1955 年2 月17 日,農(nóng)歷乙未,正月二十五。他的另外一個(gè)生日是1956 年3 月25 日,這實(shí)際是莫言為了提干修改年齡編造的“假生日”。這一事實(shí)在莫言獲得諾貝爾文學(xué)獎(jiǎng)后被學(xué)者們注意到,但在2008 年,在眾多文學(xué)史敘事都以后者作為莫言的出生日期之際,葉開(kāi)的考證無(wú)疑是有價(jià)值的。;此后,在對(duì)莫言閱讀史的考察中,他又發(fā)現(xiàn)了莫言自述閱讀經(jīng)歷時(shí)的抵牾現(xiàn)象:莫言在演講中談到自己讀的第一本書(shū)《封神演義》是在石匠的女兒那里拉磨工作換來(lái)的[11],但在另一篇散文中,莫言又說(shuō)該書(shū)是從班里一個(gè)男同學(xué)那邊借過(guò)來(lái)的。[12]葉開(kāi)指出,借書(shū)的人由“無(wú)趣的男同學(xué)”置換成“美貌的石匠女兒”,莫言有意識(shí)地在講話中把歷史傳奇化,“在這樣一個(gè)本來(lái)應(yīng)該是充滿斗爭(zhēng)的關(guān)系里,因?yàn)槲覍?duì)石匠的女兒有愛(ài)慕之心,故事的目標(biāo)轉(zhuǎn)換了,價(jià)值產(chǎn)生了變化,石匠女兒的價(jià)值后來(lái)居上,凌駕于《封神演義》之上。作為故事講述能手的莫言,在這樣一個(gè)簡(jiǎn)單的演講中,巧妙地套用了一個(gè)經(jīng)典故事的結(jié)構(gòu),來(lái)消解自己少年時(shí)代的艱難閱讀歷程。”[13]而莫言“石匠女兒”的虛構(gòu)很有可能是源于莫言少年時(shí)代男女之間對(duì)抗性的缺失而形成的補(bǔ)償心理[14],這種考證和探究無(wú)疑是有啟發(fā)價(jià)值的。而嚴(yán)謹(jǐn)考證也使這部評(píng)傳更加真實(shí)可靠。王玉《莫言評(píng)傳》的寫(xiě)作態(tài)度也是相當(dāng)嚴(yán)謹(jǐn)?shù)模@種嚴(yán)謹(jǐn)性體現(xiàn)在她對(duì)莫言童年閱讀敘事中的差異的關(guān)注、對(duì)魔幻現(xiàn)實(shí)主義與莫言的淵源的辨析,也體現(xiàn)在她敘述的準(zhǔn)確性上。在葉著中,葉開(kāi)提到了莫言的小學(xué)老師張召聰[15]對(duì)莫言的影響以及莫言在棉花加工廠[16]的工作經(jīng)歷。“張召聰”和“棉花加工廠”等稱(chēng)呼源于莫言《我的老師》等回憶性散文,作家的回憶有時(shí)是有偏差的,王玉在考證諸多材料后便得出:“張召聰”應(yīng)寫(xiě)作“張兆聰”,“老師的名字,莫言根據(jù)音來(lái)判斷,所以孟憲慧、張召聰在莫言的文字里。”[17]莫言所謂的“棉花加工廠”,全稱(chēng)是“高密縣第五棉油加工廠”。[18]
關(guān)于傳記史料的考辨,中國(guó)現(xiàn)代傳記寫(xiě)作的開(kāi)路人胡適指出:“對(duì)于任何證據(jù)材料都得問(wèn):(1)這種證據(jù)是在什么地方尋出的?(2)什么時(shí)候?qū)こ龅模浚?)什么人尋出的?(4)地方和時(shí)候上看起來(lái),這個(gè)人有作證的資格嗎?(5)這個(gè)人雖有證人資格,而他說(shuō)這句話時(shí)有作偽無(wú)心的或有心的可能嗎?”[19]這種反思對(duì)當(dāng)下傳記書(shū)寫(xiě)仍具有警示意義。
(三)客觀性原則與“文過(guò)溢美”
傳記作者公正客觀的態(tài)度是真實(shí)的保障,作者唯有做到“善惡必書(shū)”才能呈現(xiàn)出一個(gè)完整、真實(shí)的傳主形象。兩部評(píng)傳對(duì)作家、作品的評(píng)價(jià)整體較為客觀公允。在對(duì)莫言生平書(shū)寫(xiě)的過(guò)程中,他們既關(guān)注到莫言為讀書(shū)、為入伍所做的努力,也不諱言他在文革中“批斗”對(duì)自己多有照顧的女老師、為提干而改掉生日等事件,給予讀者一個(gè)較為真實(shí)的莫言。
在對(duì)莫言作品的評(píng)析方面,葉著不惜筆墨點(diǎn)評(píng)莫言創(chuàng)作的成功之處,但他也指出莫言早期創(chuàng)作的模式化色彩:《黑沙灘》是臣服于大眾邏輯和政治邏輯的主旋律文學(xué)[20],《透明的紅蘿卜》中也仍然包含著一種刻板的聲音。然而此類(lèi)批評(píng)限于莫言早期創(chuàng)作,作者對(duì)莫言創(chuàng)作中“自我重復(fù)”“泥沙俱下”等“硬傷”并未提及。葉著中還數(shù)次出現(xiàn)帶有明顯褒揚(yáng)色彩的語(yǔ)辭,如贊譽(yù)莫言是“文曲星下凡”[21]等,這暗含了作者的“崇敬型”創(chuàng)作傾向①趙白生將傳記創(chuàng)作分為“紀(jì)念性傳記”“認(rèn)同性傳記”“排異性傳記”三類(lèi),其中“認(rèn)同性傳記”中又細(xì)分為“移情型”創(chuàng)作、“崇敬型”創(chuàng)作和“體驗(yàn)型”創(chuàng)作。“崇敬型”創(chuàng)作即出于對(duì)莫言的尊敬和敬仰,以仰視的視角描摹莫言的生活、思想和文學(xué)創(chuàng)作。趙白生:《一沙一世界——論傳記主人公的選擇與整體性》,《北京大學(xué)學(xué)報(bào)》(哲學(xué)社會(huì)科學(xué)版),1998 年第5 期。,一定程度上妨礙了傳記的客觀性。相比之下,王玉并未因?qū)髦鞯淖鹁炊M言其不足。除了對(duì)莫言早期作品不足的批評(píng),她也犀利地指出莫言作品中的自我重復(fù)問(wèn)題:“情節(jié)無(wú)非是好地主,壞支書(shū),好母親,壞婆婆,大膽的姑娘……”[22]對(duì)于這種重復(fù),王玉表示理解,但同時(shí)也指出“僅僅拿記憶說(shuō)話,卻又在寫(xiě)作中習(xí)慣遺忘是多么危險(xiǎn)的事情”[23]。這都體現(xiàn)了作者辯證、客觀的學(xué)術(shù)立場(chǎng)。
傳記作者選定傳主為之作傳,其本身便可能對(duì)傳主存在尊崇心理,而在作傳過(guò)程中,隨著對(duì)傳主了解的深入,作者難免會(huì)因?yàn)楣睬槎鴮?duì)傳主產(chǎn)生親近感與護(hù)佑之情,極有可能超越“同情性理解”的限度,有意無(wú)意隱惡揚(yáng)善;除了個(gè)人感情,傳記作者更有現(xiàn)實(shí)利益、道德親情等諸多因素考量,這都可能妨礙傳記的真實(shí)、客觀。針對(duì)傳記“文過(guò)溢美”的傾向,英國(guó)文學(xué)批評(píng)家德斯蒙特·麥卡錫提出了“傳記家誓言”,即傳記作者必須遵守職業(yè)道德,在傳記中不允許有意歪曲和隱瞞事實(shí)。傳記作者遵守“傳記家誓言”,注重主觀感情介入的程度,不虛美,不隱惡,警惕過(guò)度表達(dá),主動(dòng)由“崇敬型”創(chuàng)作走向“體驗(yàn)型”創(chuàng)作,以平視的視角看待傳主,走進(jìn)傳主的世界,與傳主進(jìn)行心靈、精神上的平等對(duì)話,如此方能構(gòu)建傳記的真相。
(四)文學(xué)性虛構(gòu)
傳記的屬性問(wèn)題至今仍是傳記實(shí)踐的核心問(wèn)題之一,但傳記同時(shí)具有文學(xué)和歷史學(xué)雙重屬性,傳記書(shū)寫(xiě)應(yīng)當(dāng)在歷史與文學(xué)之間求得平衡,這已是學(xué)界的一種普遍共識(shí)。成熟的傳記往往能夠“基于史而臻于文”,達(dá)到客觀、真實(shí)的歷史性與生動(dòng)、形象的藝術(shù)性的統(tǒng)一。因此傳記作者不僅要塑造一個(gè)真實(shí)的傳主,更要讓傳主鮮活起來(lái),在故紙中“復(fù)活”傳主。這就涉及到想象與虛構(gòu)。
傳記想象的方式和指向各不相同,因此虛構(gòu)也有不同偏向。楊正潤(rùn)按照虛構(gòu)的指向?qū)⒅畡澐譃樗念?lèi):填補(bǔ)型、擴(kuò)張型、轉(zhuǎn)移型和明示型。②填補(bǔ)型虛構(gòu)即通過(guò)合理推想,用故事、細(xì)節(jié)等把空白的歷史片段填補(bǔ)完整;擴(kuò)張型虛構(gòu)指在事實(shí)的基礎(chǔ)上,渲染鋪墊,乃至一定的夸張,調(diào)節(jié)事件敘述,豐滿人物的形象;轉(zhuǎn)移型虛構(gòu)指?jìng)饔浖覍?duì)歷史材料進(jìn)行時(shí)間、地點(diǎn)或形式上的轉(zhuǎn)移;而在明示型虛構(gòu)中,傳記家不企圖掩蓋敘述的虛擬性,他公開(kāi)承認(rèn)某些敘述的虛構(gòu)性。楊正潤(rùn):《現(xiàn)代傳記學(xué)》,南京·南京大學(xué)出版社,2009 年版,第542- 549 頁(yè)。葉開(kāi)《莫言評(píng)傳》中不乏虛構(gòu)成分,他多采用轉(zhuǎn)移型虛構(gòu)與直接引用相結(jié)合的呈現(xiàn)方式。如作者曾寫(xiě)到少年莫言草垛偷讀《青春之歌》的片段:
從草垛后暈頭漲腦地鉆出來(lái),已是紅日西沉。
少年莫言聽(tīng)到羊在圈里餓得狂叫。
他心里忐忑不安,等待著一頓痛罵或痛打。莫言母親看他那副魂不守舍的樣子,寬容地嘆息一聲,沒(méi)罵也沒(méi)打,只是讓他趕快出去弄點(diǎn)草喂羊。
少年莫言如釋重負(fù):
“我飛快地躥出家院,心情好得要命,那時(shí)我真感到了幸福。”[24]
葉開(kāi)此處的敘述是根據(jù)莫言的回憶性散文《童年讀書(shū)》轉(zhuǎn)寫(xiě)的,基本事件與《童年讀書(shū)》的敘述一致,但筆觸更加細(xì)膩生動(dòng),在描寫(xiě)到莫言如釋重負(fù)的心情時(shí),作者采用了直接引用的方式。在葉著中,凡是與傳主關(guān)系密切且傳主有相關(guān)敘述的內(nèi)容,傳記多直接引用傳主在自述、演講中的文字。這種轉(zhuǎn)移型虛構(gòu)與直接引用相結(jié)合的方式既增強(qiáng)了傳記的文學(xué)性,又很好地保證了傳記的客觀性。葉著中也存在填補(bǔ)型虛構(gòu)和夸張型虛構(gòu),為嚴(yán)肅的學(xué)術(shù)傳記增添了生機(jī),此類(lèi)虛構(gòu)在著作中運(yùn)用不多,因此并不違背學(xué)術(shù)傳記的客觀性要求。王玉的《莫言評(píng)傳》在虛構(gòu)方面與葉開(kāi)類(lèi)似,基本采用轉(zhuǎn)移虛構(gòu)與直接引用相結(jié)合的方式,極少填補(bǔ)、夸張型虛構(gòu),顯示出較強(qiáng)的學(xué)術(shù)追求。虛構(gòu)增強(qiáng)了傳記的文學(xué)性和可讀性,但值得注意的是,“傳記家的想象是一種復(fù)原性的想象、一種推想,目的是通過(guò)虛構(gòu)的內(nèi)容更真實(shí)地再現(xiàn)歷史。”[25]虛構(gòu)是為了真實(shí),不能突破真實(shí)性底線。
二、清晰、連貫與深度——結(jié)構(gòu)體系與作品評(píng)介
在真實(shí)、客觀的基礎(chǔ)上,傳記作者要想更好地展示傳記核心,實(shí)現(xiàn)對(duì)傳主生平的條理敘述和對(duì)傳主個(gè)性的清晰展示,傳記的結(jié)構(gòu)體系構(gòu)建便不能忽視。書(shū)寫(xiě)作家傳記,作者除了對(duì)傳主人生和傳主個(gè)性的敘寫(xiě),更需要關(guān)注傳主的創(chuàng)作,傳記作者能否對(duì)傳主作品進(jìn)行獨(dú)到、精彩解讀,對(duì)傳主成就及地位做出恰如其分的評(píng)價(jià)是衡量作家傳記價(jià)值的一個(gè)重要尺度。
(一)結(jié)構(gòu)體系
傳記結(jié)構(gòu)體系的構(gòu)建在傳記書(shū)寫(xiě)中占有重要地位,圍繞傳主的人和事名目繁多,錯(cuò)綜復(fù)雜,單純按照時(shí)間順序謀篇布局有時(shí)很難滿足傳記書(shū)寫(xiě)的需要,傳記的結(jié)構(gòu)布局牽涉到傳材的安排及其相互關(guān)系,進(jìn)一步影響傳主形象、個(gè)性塑造和傳記呈現(xiàn)的整體效果。作家評(píng)傳基于作家“個(gè)人生活與個(gè)性歷史敘事”和“志向或職業(yè)敘事”的“雙螺旋架構(gòu)”[26]及傳主作品的評(píng)介需求,對(duì)傳記結(jié)構(gòu)體系有更高的要求。楊正潤(rùn)將傳記結(jié)構(gòu)劃分為四種模式:時(shí)序結(jié)構(gòu)、場(chǎng)面結(jié)構(gòu)、專(zhuān)題結(jié)構(gòu)、復(fù)合結(jié)構(gòu)。時(shí)序結(jié)構(gòu)是按時(shí)間順序敘述傳主生平;場(chǎng)面結(jié)構(gòu)是選擇其中若干主要的和重大的事件組織成相對(duì)獨(dú)立的故事構(gòu)建傳主生平;專(zhuān)題結(jié)構(gòu)則是把傳主的經(jīng)歷、個(gè)性或成就分解成幾個(gè)領(lǐng)域進(jìn)行專(zhuān)題敘述或評(píng)論;復(fù)合結(jié)構(gòu)是前三種專(zhuān)題取長(zhǎng)補(bǔ)短的綜合。復(fù)合結(jié)構(gòu)往往以時(shí)序?qū)髦饕簧?jīng)歷進(jìn)行梳理,場(chǎng)面化的敘述既有故事性,又突出傳主的個(gè)性,同時(shí)也插入了專(zhuān)題,集中介紹和評(píng)價(jià)傳主某方面的成就,對(duì)尋求歷史性和文學(xué)性平衡的長(zhǎng)篇傳記具有重要意義。[27]
在結(jié)構(gòu)布局方面,葉著采用了復(fù)合結(jié)構(gòu),從“饑餓年代”到“收獲年代”五個(gè)章節(jié)基本按時(shí)序敘述,在此基礎(chǔ)上葉開(kāi)在章節(jié)內(nèi)插入專(zhuān)題,圍繞某一核心集中探討,如第一章“饑餓年代”中“活水的記憶”一節(jié)便以專(zhuān)題的形式敘述莫言與“水”的淵源。復(fù)合結(jié)構(gòu)為作者安排傳材、評(píng)介作品提供了充足的空間。在處理傳主生平、文學(xué)創(chuàng)作、作品評(píng)介這三方面內(nèi)容上,作者采用了“夾敘夾議”的手法:敘述傳主生平的同時(shí)穿插敘述相應(yīng)的傳主的文學(xué)活動(dòng),并對(duì)傳主的作品進(jìn)行解讀。如第一章“塵土的記憶”一節(jié)中,作者描繪莫言“浮土”上的誕生,同時(shí)插敘《豐乳肥臀》中玉女金童誕生時(shí)相似的場(chǎng)景,并進(jìn)一步對(duì)《豐乳肥臀》中“離不開(kāi)乳房的孩子”上官金童以及莫言小說(shuō)中的前烏托邦心態(tài)做了簡(jiǎn)要論評(píng),作家文學(xué)創(chuàng)作與其人生經(jīng)歷的內(nèi)在聯(lián)系機(jī)制得以顯現(xiàn)。此種傳記結(jié)構(gòu),實(shí)現(xiàn)了介紹傳主生平、展示傳主個(gè)性、解釋傳主個(gè)性的有機(jī)統(tǒng)一,傳主的形象得以生動(dòng)顯現(xiàn)。葉著為研究者提供了一條較為清晰的史料線索,也為讀者提供了一條走近作家、進(jìn)入作品的有效途徑。
王玉的《莫言評(píng)傳》的結(jié)構(gòu)體系卻不盡如人意。王玉將傳記分為五個(gè)部分:莫言的意義、生平、作品、小說(shuō)評(píng)析和藝術(shù)成就,除了第二章是對(duì)莫言生平的集中描述,其余四章都是偏向評(píng)論性的文字,不難看出“評(píng)”壓倒“傳”的傾向,作為“作家”的莫言得到了很好的展示,但“作家”之外的莫言卻不那么豐滿。王著的結(jié)構(gòu)模式偏向?qū)n}結(jié)構(gòu),專(zhuān)題結(jié)構(gòu)適合經(jīng)歷復(fù)雜且有多方面成就的傳主,莫言的成就集中在文學(xué)領(lǐng)域,本質(zhì)上不是非常適合專(zhuān)題結(jié)構(gòu),且采用專(zhuān)題結(jié)構(gòu)行文布局,首先需要進(jìn)行合理、有效的專(zhuān)題劃分,遺憾的是,王著專(zhuān)題的劃分或割裂,或交疊,導(dǎo)致了內(nèi)容的混亂。在王著中,莫言的生平、作品、作品評(píng)析分屬不同章節(jié),傳主的生平經(jīng)歷與文學(xué)創(chuàng)作之間的有機(jī)互動(dòng)被切斷,“傳評(píng)分離”也造成了敘述與閱讀的雙重困難:進(jìn)行作品解讀時(shí),有時(shí)很難回避傳主的經(jīng)驗(yàn),如果僅是簡(jiǎn)單提及,無(wú)法保證敘述的完整性,帶給讀者疑惑,而詳細(xì)的回溯又勢(shì)必造成內(nèi)容重復(fù)與文不對(duì)題,敘述程度的調(diào)控難度較大。作者在處理“傳”“評(píng)”的敘述程度時(shí)顯然左支右絀。如第二章“一種屬于土地的歸去來(lái)——莫言的生平”,由章節(jié)題目及主體內(nèi)容不難看出作者此章想敘寫(xiě)莫言的生平,但在實(shí)際敘述中卻多次偏離主題,走向?qū)δ宰髌返脑u(píng)析。此章第三節(jié)“引來(lái)的目光”分為“蘿卜的成功與失敗”“和影視結(jié)緣的《紅高粱》”“國(guó)門(mén)內(nèi)外”三部分,“蘿卜的成功與失敗”描述了《透明的紅蘿卜》的創(chuàng)作始末,并多維解讀《透明的紅蘿卜》;“和影視結(jié)緣的《紅高粱》”主要敘述了《紅高粱》影片的攝制;“國(guó)門(mén)內(nèi)外”涵蓋了莫言作品的譯介情況、莫言走出國(guó)門(mén)的感受等多重內(nèi)容。在敘述中,作者并沒(méi)有突出這三處節(jié)點(diǎn)之于莫言人生的關(guān)鍵意義,反而將話題引向了對(duì)《透明的紅蘿卜》的學(xué)術(shù)討論和對(duì)《紅高粱》攝制的描述。王著的后三章“莫言的作品”“莫言的小說(shuō)評(píng)析”“莫言的藝術(shù)成就”在主題確立上已經(jīng)是交錯(cuò)重疊:解讀作品本就包含了小說(shuō)評(píng)析,藝術(shù)成就更是在作品中展現(xiàn)。在實(shí)際書(shū)寫(xiě)上也確實(shí)缺少邏輯條理,混亂冗雜,傳主的形象也變得晦暗不明。不同的傳記結(jié)構(gòu)有其不同的優(yōu)勢(shì),但就內(nèi)容復(fù)雜的作家傳記而言,復(fù)合結(jié)構(gòu)有時(shí)候更能實(shí)現(xiàn)傳記書(shū)寫(xiě)的目標(biāo);而在處理作家生平、作家創(chuàng)作與作品評(píng)介的關(guān)系上,“夾敘夾議”不失為一種好的方法。
(二)作品評(píng)介
莫言傳記按照傳主身份劃分屬于作家傳記,傳記作者需要關(guān)注傳主作為“人”的層面,也需要關(guān)注傳主作為“作家”的層面,而后者不可避免地涉及到對(duì)作家作品的評(píng)介。作品是作家個(gè)性、思想的集中反映,對(duì)作品的解讀探索也是深入發(fā)掘傳主個(gè)性、思想的有效途徑,傳記作者能否對(duì)傳主作品進(jìn)行獨(dú)到、精彩解讀,對(duì)傳主成就及地位做出恰如其分的評(píng)價(jià)是衡量作家傳記價(jià)值的一個(gè)重要尺度。
葉開(kāi)對(duì)傳主作品的評(píng)析不乏新意。如他解讀《紅蝗》是“莫言通過(guò)對(duì)高密東北鄉(xiāng)過(guò)去歷史的升華,來(lái)反襯現(xiàn)在世界的骯臟”,并進(jìn)一步提出應(yīng)該將《紅蝗》與直接展示現(xiàn)世骯臟的《歡樂(lè)》對(duì)比閱讀,認(rèn)為兩部作品是“一塊硬幣的正反面”。[28]在《酒國(guó)》與賈平凹《廢都》的對(duì)比中,葉開(kāi)指出:“《酒國(guó)》試圖通過(guò)普遍性達(dá)到普遍性,而《廢都》則是通過(guò)個(gè)人性達(dá)到普遍性。”[29]此外,如前所述,作者采用“評(píng)傳結(jié)合”“夾敘夾議”的評(píng)述方式,注重發(fā)現(xiàn)作家的文學(xué)創(chuàng)作與其人生經(jīng)歷的內(nèi)在聯(lián)系機(jī)制,實(shí)現(xiàn)了基于傳主經(jīng)驗(yàn)的作品評(píng)析。
王玉的《莫言評(píng)傳》在作品評(píng)介方面更見(jiàn)優(yōu)勢(shì)。如前所述,王著除了第二章是對(duì)莫言生平的集中描述,其余四章都是偏向評(píng)論性的文字,整體評(píng)價(jià)更加多維、全面。在評(píng)介程度上,王著在對(duì)傳主及其作品的縱橫對(duì)比解讀中,顯示出學(xué)者評(píng)析的深度與獨(dú)到性。在對(duì)傳主地位評(píng)價(jià)與意義拷問(wèn)的第一章,她考證“魔幻現(xiàn)實(shí)主義”的源流,辨析莫言與魔幻現(xiàn)實(shí)主義的關(guān)系并指出,“莫言的確受到了西方現(xiàn)代小說(shuō)的影響,但莫言小說(shuō)中的思想內(nèi)核始終是屬于中華文明的。”莫言的小說(shuō)最終還是屬于“中國(guó)的夢(mèng)境與現(xiàn)實(shí)”。[30]她解讀《十三步》的性描寫(xiě):“文章中處處提及的性欲描寫(xiě)無(wú)非在配合凌亂的敘事,當(dāng)人類(lèi)最基本的欲望都變得混亂甚至乏味的時(shí)候,就是靈魂無(wú)處安放的時(shí)候。”[31]她具有啟發(fā)意義地提出莫言《四十一炮》與蘇聯(lián)電影《第四十一》在荒誕人性方面多重潛在關(guān)聯(lián)。[32]在揭示傳主創(chuàng)作中深層次或規(guī)律性表達(dá)上,王著也關(guān)注到了莫言作品中的饑餓經(jīng)驗(yàn)、批判思想、懺悔意識(shí)和深層的孤獨(dú)感,在闡釋批評(píng)中凸顯莫言的獨(dú)特意義。但王玉整體的解讀帶有明顯的“學(xué)院派”氣息,多脫離傳主經(jīng)驗(yàn)走向純粹學(xué)術(shù)探討,讓部分專(zhuān)業(yè)內(nèi)容走向艱深,不可避免損傷文本的可讀性。由此觀之,作家傳記作者除了對(duì)作品進(jìn)行歷史性、美學(xué)性的評(píng)價(jià)外,更應(yīng)該促成作品評(píng)介與傳主經(jīng)驗(yàn)的有機(jī)對(duì)話。
三、小結(jié)
綜上所述,葉開(kāi)的《莫言評(píng)傳》在傳材搜集上具有奠基意義,細(xì)致的考辨、合理的虛構(gòu)使傳記“基于史而臻于文”。復(fù)合型的傳記結(jié)構(gòu)及“夾敘夾議”的評(píng)傳體系清晰地展示了莫言的生平、個(gè)性,作者對(duì)傳主作品的評(píng)介也兼顧了學(xué)院與民間。王玉的《莫言評(píng)傳》的學(xué)術(shù)性追求更為突出,其在史料視野、作品評(píng)介深廣度等方面有明顯的優(yōu)勢(shì),但在傳記結(jié)構(gòu)構(gòu)建方面也存在明顯的不足,“評(píng)”的過(guò)分偏重、結(jié)構(gòu)的混亂和內(nèi)容的蕪雜都導(dǎo)致了傳主形象的淹沒(méi),未能突出傳記的核心要素。無(wú)法否認(rèn)傳記作者為莫言作傳付出的精力,但傳記書(shū)寫(xiě)在傳材搜集、評(píng)論深廣度等方面仍有可拓展的空間。
莫言傳記為當(dāng)代傳記書(shū)寫(xiě)提供了參照和經(jīng)驗(yàn):“真實(shí)”是傳記的生命,豐瞻全面的傳材搜集和嚴(yán)謹(jǐn)?shù)目急媸莻饔涀髡叩幕A(chǔ)工作;遵守“傳記家誓言”,公正客觀、“善惡必書(shū)”應(yīng)是作者的基本態(tài)度;虛構(gòu)增強(qiáng)了傳記作品的文學(xué)性和可讀性,但虛構(gòu)的運(yùn)用不能突破真實(shí)性底線;在結(jié)構(gòu)體系構(gòu)建上,不同的傳記結(jié)構(gòu)和敘述有其各自優(yōu)勢(shì),但就內(nèi)容復(fù)雜的作家傳記而言,復(fù)合結(jié)構(gòu)和“夾敘夾議”的敘述往往能較好實(shí)現(xiàn)傳記書(shū)寫(xiě)的目標(biāo);而在作家傳記的作品評(píng)介方面,作者除了對(duì)作品進(jìn)行歷史性、美學(xué)性的評(píng)價(jià)外,也應(yīng)該促進(jìn)作品評(píng)介與傳主經(jīng)驗(yàn)的有機(jī)對(duì)話。
隨著思想解放進(jìn)程的推進(jìn),傳記寫(xiě)作也逐漸朝著學(xué)理化、科學(xué)化的軌道邁進(jìn),學(xué)術(shù)傳記成為更多傳記作者的選擇,80 年代后出版的錢(qián)理群的《周作人傳》、凌宇的《沈從文傳》、吳俊的《魯迅評(píng)傳》等無(wú)不體現(xiàn)這一傾向。在現(xiàn)存的莫言傳記中,兩部系統(tǒng)的傳記也都屬于學(xué)術(shù)評(píng)傳。學(xué)術(shù)評(píng)傳固然具有不可替代的優(yōu)勢(shì),但在可讀性、趣味性等方面卻是短板,因此在學(xué)術(shù)傳記之外,也應(yīng)期待有側(cè)重作家生活、傳奇軼事的莫言傳記書(shū)寫(xiě)。當(dāng)代作家的“生長(zhǎng)性”給傳記書(shū)寫(xiě)帶來(lái)了難度,也提供了契機(jī)。傳主生平史料逸聞的不斷“浮現(xiàn)”以及對(duì)傳主作品研究的不斷推進(jìn),將促進(jìn)傳記作者對(duì)傳主人生軌跡、個(gè)性性格和內(nèi)心世界的把握,而隨著傳記作者理論知識(shí)的加強(qiáng)及科學(xué)方法的應(yīng)用,當(dāng)代傳記、莫言傳記書(shū)寫(xiě)都將進(jìn)入新的發(fā)展階段。
- 濰坊學(xué)院學(xué)報(bào)的其它文章
- 《濰坊學(xué)院學(xué)報(bào)》2010-2019 年文獻(xiàn)計(jì)量學(xué)分析
- 新時(shí)代學(xué)前音樂(lè)教育:現(xiàn)狀、問(wèn)題與應(yīng)對(duì)策略
——基于山東省部分地區(qū)的調(diào)查 - 應(yīng)用型高校教師績(jī)效評(píng)價(jià)體系構(gòu)建研究
- 濰坊市寒亭區(qū)文物保護(hù)管理所藏朝鮮國(guó)王李玜謝恩表再探
- 音色的構(gòu)建與隱喻
——漢斯·季默《星際穿越》電影配樂(lè)創(chuàng)作風(fēng)格探究 - 智媒體時(shí)代新聞報(bào)道的新實(shí)踐
——以2020 年“兩會(huì)”期間智媒體參與下的新聞生產(chǎn)為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