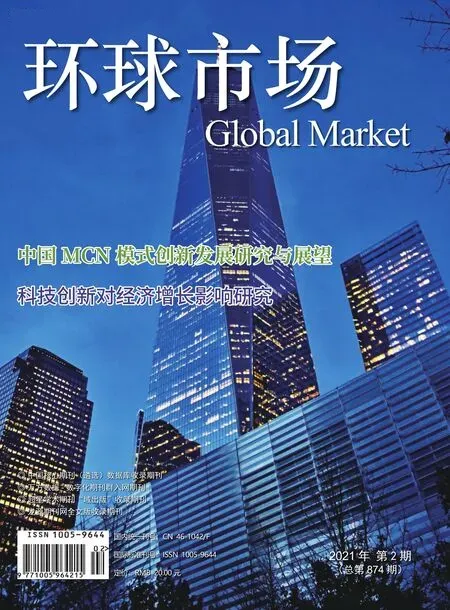綠色信貸對我國股份制商業銀行信貸風險影響研究
蘇欣 東南大學
一、引言
由于我國以往采取粗放式的經濟發展方式,使得環境污染成為經濟高速發展的巨大代價和亟待解決的重大難題。商業銀行可以通過將生態環境標準納入信貸審批的評判前提,扶持環境友好型企業發展,逐步淘汰高污染企業,從而促進我國產業結構優化,實現經濟和環境的雙重效益。我國尚處于發展綠色金融的初期,相關機制不健全,發展綠色信貸對于商業銀行來說機遇與挑戰并存。本文旨在探究綠色信貸對股份制商業銀行信貸風險的影響,既能豐富現有理論研究,又能為商業銀行更好應對信貸風險提供對策建議。
二、文獻綜述
關于綠色信貸的含義,學術界已有較豐富的研究。Marcel Jeucken(2002)認為銀行的綠色貸款業務能向企業傳遞綠色經營理念。鄧聿文(2007)認為“綠色信貸”是指金融機構遵循國家環境經濟政策,向環境友好型企業提供低利率貸款。
關于綠色信貸對商業銀行的影響,學術界主要從商業銀行的整體競爭力、財務績效、資產質量以及風險度量和管理方面來研究。孫光林、王穎和李慶海(2017)實證檢驗發現綠色信貸與商業銀行信貸風險之間存在顯著負相關性,即增加綠色信貸規模能有效抑制不良貸款率提升。高曉燕、高歌(2018)通過主成分分析法發現綠色信貸規模與商業銀行的競爭力之間呈正相關,即我國商業銀行發放綠色信貸有利于核心競爭力的提高。
三、綠色信貸對我國商業銀行信貸風險影響的理論分析
商業銀行雖不直接參加生產活動,但其貸款流向會影響特定企業的生產經營,并影響貸款回收的效率。從理論層面分析,第一,商業銀行發放綠色信貸,能夠限制資金流入高污染產業,提高資源配置,減少銀行貸款的錯位使用,降低貸款無法收回的風險。第二,綠色信貸為綠色環保的產業提供更多融資支持,促進我國產業轉型升級和可持續性發展,為未來創造更多的經濟效益提供可能。此外隨著公眾環保意識的不斷加強,綠色消費將會逐漸增加,也能在一定程度提高商業銀行綠色信貸的信貸效益,有效抑制商業銀行潛在的信貸風險。第三,綠色信貸的發放提高了銀行自我監督管理的意識,加強銀行對自身資金流動的監管,保證貸款的質量,嚴格進行貸款流程的審查和跟蹤,從而能夠增強銀行信貸風險的控制能力,有效避免“呆賬”“死賬”的出現。
四、綠色信貸對我國商業銀行信貸風險影響的實證分析
(一)變量選取及數據來源
本文被解釋變量選擇:不良貸款率(NPL),根據《貸款分類指導原則》,可以根據風險程度將貸款劃分為正常、關注、次級、可疑和損失五類,后面三類合稱為不良貸款。不良貸款率為不良貸款占貸款總額的比重。核心解釋變量選擇:綠色信貸(Gcredit)。控制變量選取:資產總額(asset)、資本充足率(CAR)、貸款總額(loan)、凈利潤(income)。本文選取的樣本是五大國有股份制商業銀行2008年-2017年的年度數據,數據來源于各銀行年度《社會責任報告》和國泰安數據庫(CSMAR)。
(二)模型設定
建立動態模型:
NPLit=γ0+γ1NPLit-1+γ2gcreditit+γ3Xit+εit
其中,i和t分別代表銀行和年度,NPLit代表i銀行t年度的不良貸款率,即銀行該年不良貸款額占貸款總額的比重,NPLit-1表示不良貸款率的滯后一期;gcreditit代表i銀行t年度的綠色信貸;Xit為控制變量;εit為隨機擾動項。
(三)實證結果
利用系統GMM模型進行測算,進行Sargan檢驗的P值為0.2993,顯著大于0.1的臨界值,表示模型不存在過度性識別的問題。AR(2)檢驗的P值為0.539,顯著大于0.1,接受無自相關的原假設,估計結果有效。在動態面板模型中,Gcredit系數為-0.00255,在5%水平上顯著,由此可以得出結論,商業銀行發放綠色信貸對不良貸款率有明顯負向影響,即增加綠色信貸能有效抑制不良貸款率的上升,降低商業銀行的信貸風險。
五、對策建議
我國商業銀行綠色信貸業務起步較晚,仍存在一些問題。結合研究結論,為進一步有序發展綠色信貸,防范信貸風險,本文提出如下政策建議:1.完善綠色信貸配套法律法規建設,提高立法層次。明確相關責任主體,鼓勵國有大型股份制商業銀行加入綠色信貸業務,并形成良好的示范作用。2.建立健全監督約束機制,同時出臺相關激勵政策,推動綠色信貸發展。加快推進商業銀行綠色評價,制定科學的考核標準。3.進一步推進信息共享和信息披露,強化社會監督。建立共享機制,搭建信息共享平臺,提高綠色信貸審批效率,引導金融資本合理有效配置。4.注重專業人才隊伍的培養,提高綠色信貸管理能力。5.合理推進綠色產品創新,建立綠色信貸行業標準。政府應明確綠色信貸發放標準,環境風險評價標準等,以便各銀行在總的工作標準下合理制定各行工作細則,完善綠色信貸管理體系,有效控制綠色信貸風險攀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