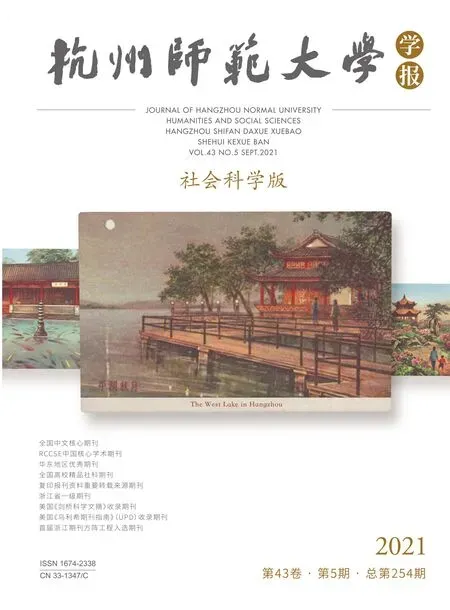儒家一本論的形成與轉進
趙法生
(中國社會科學院 世界宗教研究所;北京 100732)
儒家思想中的“一本”說源于孟子,孟子的一本說主要指人的血緣。生命只有一個本源,并由此推出儒家倫理的培育也只能有一個本源。后來的宋明理學與現代新儒家也都重視一本問題,并將一本論推進到天人關系領域。實際上,在孟子之前的《性自命出》已經具有了豐富且獨具特色的一本論思想,由此對比在同時期儒家思想史上不同的一本論形態,對于揭示儒家道德觀念的展開具有重要意義。
一
與后來的各種人性論相比,《性自命出》的人性論有其鮮明的特征,我們可以稱之為性情一本論,“一本”說本于孟子:
夷子曰:“儒者之道,‘古之人若保赤子’,此言何謂也?之則以為愛無差等,施由親始。”徐子以告孟子,孟子曰:“夫夷子信以為人之親其兄之子為若親其鄰之赤子乎?彼有取爾也:赤子匍匐將入井,非赤子之罪也。且天之生物也,使之一本,而夷子二本故也。” [1](《滕文公上》,PP.403-404)
對于孟子一本之意,朱子解釋說:“且人物之生,必各本于父母而無二,乃自然之理,若天使之然也。故其愛由此立,而推以及人,自有差等。今如夷子之言,則是視其父母本無異于路人,但其施之之序,姑自此始耳,非二本而何哉?”[2](P.262)根據朱子的解釋,孟子所謂一本包括兩方面涵義:一是從人倫血緣關系而言,人人皆由父母所生,人生之本是一非二。按照周代宗法,從高曾祖到父子構成了家族血緣關系之主軸,整個家族的血緣生命歸于一個本源,具體到家族中每個個體同樣也是父母生養,故人生之本源是一非二,這是人生血緣關系之一本。其次是倫理道德思想之一本。儒家主張愛有差等,推己及人,由親親而仁民,由仁民而愛物,最終成其天下一體之仁。夷子主張愛無差等,像對待路人一樣對待父母,在儒家看來違背情理,乖違不通。但夷子同時又要求施行道德的次序就從愛親開始,一方面主張愛無差等,一方面又要求“施由親始”,其中包含著道德法則與道德情感的不一致,故孟子稱之為“二本”。故孟子所言“一本”之“本”,如同日本德川時代的儒者西島蘭所釋:“本者,物之所從出也”(1)轉引自黃俊杰《中國孟學詮釋史論》,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4年,第298頁。,而“一本”是指人血緣關系與倫理培育皆有一個本源而非兩個本源,反映了儒墨在道德觀的基本差異。
戴震認為一本論是孔孟人性論的根本特征,并以此作為評價其他各家學說的標準。戴震還進一步提出了自然與必然一對概念,并認為孟子一本論的核心內容在于以“必然為自然之極則”。他說:
欲者,血氣之自然,其好是懿德也,心知之自然,此孟子所以言性善。心知之自然,未有不悅理義者,未能盡得理合義耳。由血氣之自然,而審察之以知其必然,是之謂理義;自然之與必然,非二事也。就其自然,明之盡而無幾微之失焉,是其必然也。如是而后無憾,如是而后安,是乃自然之極則。若任其自然而流于失,轉喪其自然,而非自然也:故歸于必然,適完其自然。夫人之生也,血氣心知而已矣。[3](P.170)
由此可見,戴震所謂“自然”,包括血氣之自然和心知之自然兩個方面,自然即人之血氣心知;而他所謂必然,就是理義。他認為,自然與必然并不是兩個不同的事物,自然之“明之盡而無幾微之失”就是必然,二者是相通的。如果不加調養節制,任其發展,則人之“自然”就會流蕩喪失,反而喪其自然;只有歸于必然,才能確保自然之實現,故曰必然乃自然之極則。可見,戴震所說的一本論,實質是將血氣心知和理義歸于一本,他認為這是孔孟人性論的根本精神,并以此為標準,批評了佛、道、告子、荀子和程朱的二本論,比如他批評荀子說:
荀子見常人之心知,而以禮義為圣心;見常人任其血氣心知之自然不可,而進以禮義之必然;于血氣心知之自然謂之性,于理義之必然謂之教;合血氣心知為一本矣,而不得禮義之本。[3](P.171)
在戴震看來,荀子雖然以血氣心知為一本,但沒有將理義與血氣心知歸于一本,故曰“不得禮義之本”。戴子還說:“茍歧而二之,未有不外其一者也。”[3](P.171)
戴震對孟子人性論的詮釋是否完全符合孟子人性論之意,學術界有不同看法。筆者以為,戴震以一本論釋孟子的道德哲學,而其一本論的基本含義是合血氣心知與理義為一本,這種一本論具有戴震本人思想的鮮明印記,而與孟子人性論本身有相當的出入,因為他忽略了孟子道德哲學中一個十分重要的內容,即大體小體之分。在孟子人性論中,小體產生了人的耳目口鼻之欲,大體代表心之所欲,即孟子所說的“心之所同然”,也就是禮義。在這兩種不同的欲望之間,孟子做了一個明確的取舍,通過心論性,將人的惻隱之心、羞惡之心、辭讓之心、是非之心定義為人之本性,而將耳目口鼻之欲排除在他所定義的人性范疇之外。可是,戴震的詮釋并沒有反映孟子人性論的這一基本區分。可以說,對于孟子人性論中的血氣心知與禮義兩方面,戴震的一本論是有見其同而無見其異。但是,通過對理學人性論的反思,戴子發現孟子的性善論與人的情感并不必然處于對立狀態,這的確又是他的洞見。這一洞見的意義因《性自命出》等楚簡資料的問世而獲得進一步證明。然而《性自命出》的一本論不是合血氣心知為一本,而是性情一本,性情一本反映了孟子以前原始儒家人性論的基本特征。
二
在性情觀上,朱熹主心統性情,其性情論又以理氣論為前提。朱熹認為事物之存在是理與氣聚合而成,氣化之物是形而下者,理則是形而上者,是事物的所以然。從構成事物的存在而言,理與氣不能相離,缺一不可,但從本質上言,“所謂理與氣,此決是二物。但在物上看,則二物渾淪,不可分開各在一處,然不害二物之各為一物也。”[4](《答劉叔文》,卷46,P.2146)。他認為“有是理便有是氣,但理是本”[5](卷1,P.114),理為氣之本,所以他又認為理在事先,“未有這事,先有這理”,“未有天地之先,畢竟也只是理。有此理便有此天地。若無此理,便亦無天地,……有理便有氣,流行發育萬物”[5](卷1,P.114),但這并不意味著理從時間上先于氣,而是從理論上說,理更根本,“此氣是依傍這理行”[5](卷1,P.116),氣為理所主導。所以,朱熹建構了“理與氣不離不雜”之形上學,將世界的生成歸為理與氣兩種因素的作用,又突出了理的根本性和氣的從屬性,構成了世界起源的二本論。這影響到性情論,就形成了朱熹性情二分即性屬理而情屬氣,而心統性情的三分架構,于是,性與情成為異層異質的存在,如此理與氣、性與情、天地之性和氣質之性均處于二本狀態。
與朱熹的性情論相比較,《性自命出》并沒有一個預設的本體論架構,“性自命出”“命自天降”肯定了性的超越性意義,但此種超越性并非源于一個形而上本體,只是將天溯源性地追溯到那個萬物由以產生的至高主宰而已。“喜怒哀悲之氣,性也”,則明確將性歸入了氣的范疇,表明此時的人性論以當時的氣論宇宙觀為基礎。由于形而上預設之不同,導致《性自命出》的性與情關系也與理學有了明顯差異,性與情同屬于氣,不是二本而是一本,構成了一種早期儒學特有的一本論形態即性情一本,它具有如下涵義:
第一,性與情在存有論上處于相同層次。錢穆先生說:“朱子本謂理氣不可分先后。但若定要分時,則理應在先。因理是形而上者,是本。及其為氣成形,則為末,應在后。如言造化,只能說造化必有理,不能說當其造化時始造化出理來。造化只是此理,古云‘天即理’。”[6](《朱子新學案(一)》,PP.271-272)因此,理為形而上是本,氣為形而下是末。“性即理也”,性自然屬于形而上;情則屬于氣,氣是形而下,故二者屬于不同存有層次,朱熹也稱之為性體情用,即“性是體,情是用,性情皆出于心”;又說:“性,本體也;其用,情也;心,則統性情、該動靜而為之主宰也。”[4](《孟子綱領》,卷74,P.3584)由于理學性情體用論的影響,一提到性與情,人們往往將二者歸屬到形上和形下兩個不同層次,性是理,情是氣,二者分屬于天命之性和氣質之性。但是,在《性自命出》中的性與情并沒有這種分野。“性自命出,命自天降”表明性、命來源于天,但性和情卻都屬于氣,由于沒有形而上學領域的理氣二分,性與情并沒有形上和形下之別,這自然與戰國時期的氣化宇宙論密不可分,同時也表明戰國中前期的儒家形上學與理學形上學的顯著差異,正如“道始于情”所表明的,這種形上學的基礎不是理氣二分而是道氣一本。
第二,性與情具有同質的內涵。與性與情處于同一存有層次相聯系的是,二者具有同質的內涵。簡文說:“喜怒哀悲之氣,性也”,將性的內涵看作是氣,早在春秋的氣論世界觀中,人的情志就已經被看作是氣。也就是說,性與情二者具有同質的內涵,它們本質上都是氣,二者的差異只是氣化過程的不同。性是潛在的氣,是一種情氣,即所謂“喜怒哀悲之氣”,當這種氣感于物而動且“現于外”時,便是現實的情。這樣,性與情便不能不被視為兩種不同質的存在物,它們的差異只是潛在和現實、未發和已發的不同,而這里的未發和已發并非理學詮釋下《中庸》的未發和已發,而是同一種氣尚未發出和已經發出的差異。在注釋《中庸》之“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一語時,孔疏曾引賀玚之說,對性與情的關系做過如下比喻:“性之與情,猶波之與水,靜時是水,動則是波。靜時是性,動則是情。”這一比喻雖是針對《中庸》,但亦可說明《性自命出》中性與情之關系,二者雖有水與波之別,但只是表現形態的差異,至于本質內涵則并無不同。另外,簡文將性與情的內涵均看作是氣,表明春秋時期已降的氣論哲學同樣是楚簡性情論的哲學依據。既然性與情處于同一層次,具有同質的內涵,故在先秦諸子文獻中,性情二字經常互用。對此,徐復觀先生曾有如下論述:
在先秦,情與性,是同質而常常可以互用的兩個名詞。在當時一般的說法,性與情,好像一株樹上生長的部位。根的地方是性,由根伸上去的枝干是情;部位不同,而本質則一。所以先秦諸子談到性與情時,都是同質的東西。[7](P.204)
第三,性與情具有相同的價值屬性。從漢儒開始,性與情的關系開始出現對立與緊張,簡文說“道始于情”,將情作為人道建構的始基,由此可見,情不僅是性之所生,而且是人道之始,情不但與性不矛盾,與道也不矛盾。可是,荀子的性惡論之后,它卻逐漸成為道德的對立面。西漢時董仲舒提出了性善情惡論,他說:“身之有性情也,若天之有陰陽也。言人之質而無其情,猶言天之陽而無其陰也。”[8](《深察名號》)董子以陰陽論性情,認為人身“兩有貪仁之性”,性生于陽,為仁為善;情生于陰,為貪為惡[8](《深察名號》),于是性為善而情為惡。董子此說深受荀子影響,其實是以欲釋情,偏離了原始儒家的情論的軌道,情的地位從此每況愈下,中間雖有劉向的性情相應說,主張“性不獨善,情不獨惡”(2)轉引自張岱年《中國哲學大綱》,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2年,第203頁。,但依然無法挽回賤情的趨勢。唐代李翱提出復性說,認為:“人之所以為圣人者,性也;人之所以惑其性者,情也。喜怒哀懼愛惡欲七者,皆情之所為也。情既昏,性斯匿矣。非性之過也,七者循環而交來,故性不能充也。”[9](《復性書上》,P.6)這里情成了障蔽人之善良本性的罪魁,于是李翱進而提出了滅情說:“情者,妄也,邪也。……妄情滅息,本性清明,周流六虛,所以謂之能復其性也”。[9](《復性書中》,P.16)這種滅情方能顯性的主張,將漢儒以后性與情的緊張發展到了極致。
朱熹雖然以心統性情安頓了情,但基于理氣二分的形而上學,情只能被歸入到形而下的畛域,性與情的價值判斷依然不同,他說道,“性無不善,心所發為情,或有不善。說不善非是心亦不得,卻是心之本體本無不善,其流而為不善者,情之遷于物而然也”[6](《朱子新學案(二)》,P.125),性無不善而情或有不善,歸根結底是因為性即理而情為氣,故情經常追逐物欲而陷于不善。但是,《性自命出》中情的價值屬性判斷卻是另一種情景。情也具有荀子所說的“本始材樸”的特征,卻不是惡的,“凡人情為可悅也”表明人情都有其可愛的一面,它對于情關注的重點不在于善惡而在于真偽,情只要是真誠就好,以至于有“雖過不惡”之論。這恰恰是周代禮樂文明對于人性的看法,因為在禮樂文明的視野中,人都是可以教化的,而教化的根基就在于人內心深處的真情之中,純真的性情才是道德的基礎與根本,也是禮樂制度本身的基礎和起點,這才是貴情說的緣起。所以,《性自命出》不僅肯定了性,而且同樣肯定了情,對于性與情的價值判斷是一致的。從儒學史上看,性與情的價值判斷確與道德形而上學的建構密切相關,如果說性情體用論與理氣二分密不可分,但在天命觀的視域下,天雖然是至上主宰,其意志卻只能通過民意、民心、民情來體現,所謂“天聽自我民聽,天視自我民視”“民之所欲,天必從之”,民實際上享有與天帝同等的地位,這樣的民,其情其性,不可能是惡的。只有當王權時代的天命觀式微之后,伴隨著儒法互補下的君主專制制度的形成,貴情主義才有了轉向賤情主義的可能。
除性情一本外,《性自命出》還包含情道一本。理學中的性情二本,同時意味著情與道對立,可是,原始儒家似乎不是如此:《性自命出》強調道義不是對性情的壓制而是性情之實現途徑,從根本上講,道與情屬于一本,情本于道;《性自命出》中“道始于情”“禮作于情”等相關論述表明,情與道義并不相矛盾,倒是道的根基所在。因為道義并不是違背人情而是順著人情,人情不但是道義之始源,而且為道義之實現提供了動力,道義不是對于人情的壓制而是人情之節文,道德的實現是通過將性情的自然表達納入到詩書禮樂的熏陶教化而臻于善的境地。
從工夫論角度看,《性自命出》的一本論,除了性情一本、情道一本外,還包括身心一本。在西方理性主義哲學中,身與心長期被視為兩個不同實體,可是,中國思想在軸心時期就已經形成了身心一如的觀念,在氣論哲學的影響下,身心被視為一體兩面的一個實體。先民在早期醫學理論與養生工夫實踐中都已經對基于氣機運動的身心一本論有了深入的體察,比如以《黃帝內經》為代表的中醫理論,以及在《莊子》《孟子》《公孫尼子》《管子》等所記載的煉氣養生資料中,對此都有闡發。儒家對于身心一如的認識有其獨特之處,就是基于禮樂文明的生命體驗,這在《性自命出》中十分突出,在它看來,禮樂教化除了能夠使君子美其情,“貴其義,善其節”之外,還能夠“好其容”,又說能“致容貌以文”,禮義何以會具有美容功效?說到底是因為禮樂能夠“美其情”,因為情是一種氣,是人心所感受表達的主要對象,而人體同樣是氣,氣機的感通貫穿身心內外,美好的情氣因此就具有了使人的身體儀容更加優雅的功效,簡文重視樂對于身心兩方面的影響,所謂“其聲變,其心從之;其心變,其聲亦然”,又說:“聞笑聲,則鮮如也斯喜。聞歌謠,則陶如也斯奮。聽琴瑟之聲,則悸如也斯嘆。”可見,樂聲會導致情緒的變化,而情氣流布與作用于人的身體,于是情緒的變化又引起身體容色的運動變化。
所以,《性自命出》的一本論,包括性情一本、情道一本和身心一本四個面向,它實現了天、命、性、情、道、心、身之間的貫通,是儒學史上第一個完整的一本論。《性自命出》的性氣一本說不同于理學的理氣二本,為性情一本說奠定了哲學基礎。性情一本是《性自命出》人性內涵,它也是儒家思想史上第一個系統的人性論形態,對于以后的儒家人性發展影響深遠。情道一本展現了情與道之間的內在有機聯系,將一本論從性情層面推進到道德實踐領域。身心一本則是其一本論的完成,它將儒家關于天人關系、人性內涵、道德法則、道德實踐的一切探索與進展落實到通過身體展現的人格氣象,突出了儒家道德的工夫論面向,也顯示了原始儒家的工夫論與理學工夫論的歷史差異。
徐復觀指出:“先秦諸大家所講的人性論,則是由自己的工夫所把握到的,在自身生命之內的某種最根源的作用。”[7](P.408)他解釋工夫說:“以自身為對象,尤其是以自身內在的精神為對象,為了達到某種目的在人性論(3)原文如此。,則是為了達到潛伏著的生命根源、道德根源的呈現——而加內在的精神以處理、操運的,這才可謂之工夫。人性論的工夫,可以說是人首先對自己生理作用加以批評、澄汰、擺脫;因而向生命的內層迫進,以發現、把握、擴充自己的生命根源、道德根源的。”[7](P.409)揭示儒家人性論與工夫的內在聯系,是徐復觀的深刻之處,足以彰顯儒家人性論與西方哲學人性論的基本差異。但是,他對于工夫本身的解讀,卻不免打上了過于濃厚的理學色彩。任何工夫修養都必然包括內在精神的面向,但這并非工夫的唯一面向。正如《性自命出》《孟子》等所表明的,儒家工夫同時包括身心兩個向度,而以身心一體交融為基本特征。另外,將人性論的工夫說成是“可以說是人首先對自己生理作用加以批評、澄汰、擺脫;因而向生命的內層迫進”,則顯示了理學式的身與心、生理與精神之間對立緊張。從早期禮樂文明的角度看,工夫的實踐并不是一味要“批評”或者“澄汰”生理的作用,更不是為了“擺脫”生理的作用,而是為了使得人生理追求的實現過程獲得節文,用戴震的話說,通過“必然”使得“自然”得以合理實現。這也反映出儒家工夫論的歷時性,不同的本體論和心性論,將對工夫論產生深刻影響。
作為一種人性論,《性自命出》的性情論有兩個前提:天命論和禮樂制度。到了戰國初期,作為人格神的天命觀念已經趨于淡薄,但依然規定了儒家對人的基本看法,既然普通民眾的心情意志都是天命的晴雨表,人性之可貴性就不言而喻了,由此而有了儒家“天生萬物,唯人為貴”的結論。早期儒家天命觀(而非天理觀)視域下的人,注定很難以與性惡論掛鉤。有此種貴人論,才可以理解《性自命出》的貴情、貴心和貴身論。同時,性情論之所以作為第一個成體系的人性論出現在戰國初期,也離不開禮樂文明的背景。可以說,性情論中的人,就是禮樂文明視野下的人。如果說天命觀下的所有人都是珍貴的,禮樂文明視域下的所有人都是可教化的,而內在性情則是禮樂教化能夠有效施展的基礎。所以,這種天、命、性、情、道、教之一本論,注定只能產生于早期儒學。
從工夫論的角度看,性情論首次將道德實踐基礎深入到人的內心世界,最終鎖定在情上,首次規定了實踐工夫的內在依據,此種依據及性情本身又賦予了禮樂制度以必然性與合理性。這是一種內外貫通融合的工夫,是建立在真性情基礎上的禮樂修身工夫,是“興于詩、立于禮,成于樂”的道德實踐,性情論下的儒家道德思想,在情與道以及性情與禮樂之間,都不存在后來的對立緊張,它具有早期禮樂文明所特有的雍容、中和與博大氣象。不過,作為儒家早期人性論,主體意識在其中并沒有得到進一步彰顯。其中的人似乎陶醉于與天地萬物共生和諧的樂章中,接受著禮樂文明的滋養與熏陶,沉浸在“大禮與天地同節,大樂與天地同和”的善與美的精神愉悅之中,那種將自己從天地萬物宇宙洪荒中區分并開顯出來的心性主體尚未形成。不過,正是在儒家關于真情的體認探索中,包含著后來心性論的因子,而一旦心性主體誕生,工夫論的視域與模式也將發生內在性轉移,身心關系以及內在精神與禮樂實踐的作用也將發生重要改變,這正是我們后來在孟子的心性論中所看到的情景。
三
儒學的一本論,到了宋明理學又有進一步發展。在宋明諸子中,牟宗三特別推重明道之一本說,他稱之為“圓頓之一本”[10](中冊,P.91)。明道曰:“道,一本也。或謂以心包誠,不若以誠包心;以至誠參天地,不若以至誠體人物,是二本也。知不二本,便是篤恭而天下平之道。”[11](PP.117-118)據牟宗三解讀,明道認為,如果心和誠之間彼此還要“包”;誠與天地之間,還要“參”;誠和人物之間,還要“體”,彼此對待,就是二本而非一本。[10](中冊,P.91)牟宗三說:“若言一本,只應:只心便是誠,只誠便是心,只心便是天,只誠便是天,只是此心此誠之形、著、明、動、變、化即是天地之化,更無所謂包,無所謂參,亦無所謂體,體亦是多余字。”[10](中冊,P.91)明道之一本,涉及天、人、心、性四者關系,他說“天人本無二,不必言合”[11](P.81),這是說天人一本,“若不一本,則安得‘先天而天不違,后天而奉天時’?”[11](P.43)大人為天道之化身,與天道為一,故能“先天而天不違,后天而奉天時”,自然不必言合了。明道又云:“只心便是天,盡之便知性,知性便知天。當處便認取,更不可外求。”[11](P.15)這是在孟子“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1](《盡心上》,P.877)的基礎上,進一步將心、性和天打通為一,將天完全內在化,而孟子還有“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1](《萬章上》,P.647),以及“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1](《盡心上》,P.878)”之說,天命雖然可與人之心性相貫通,但天并沒有完全內在化,依然體現著主宰之天的性格,而明道之說則將天完全收攝到心性之內了。
牟宗三認為,象山也是直承孟子學,不過,象山之學對于《易傳》《中庸》宇宙論的關注有所欠缺,而明道則由《易傳》《中庸》落實于《論》《孟》,將先秦儒家之主客觀兩方面的思想直貫打通,遂成其圓頓無二之一本論。他說:“所謂‘一本’者,無論從主觀面說,或從客觀面說,總只是這‘本體宇宙論的實體’之道德創造或宇宙生化之立體地直貫。此本體宇宙論的實體有種種名:天、帝、天命、天道、太極、太虛、誠體、神體、仁體、中體、性體、心體、寂感真幾、于穆不已之體等皆是。此實體亦得總名曰天理或理。此理是既超越而又內在的動態的生化之理、存在之理或實現之理。……總之,是‘即存有即活動’的這‘本體宇宙論的實體’。”[10](中冊,P.16)由此可見,在牟宗三看來,明道之一本論,是先秦儒家兩大思想源頭即《易》《庸》與《論》《孟》的圓滿融合,是主觀與客觀兩方面的“直貫打通”,也就是將天命實體直接落實呈現于人之道德本心,使得天理具有了既內在又超越,既存有又活動的雙重性格,而不再偏于一隅:如果偏于外在,將無法彰顯道德主體的意義,無法顯示儒家道德之自律屬性;如果偏于內在,道德法則將喪失其天道的客觀依據,從而有可能出現王學末流“情識而肆”或“玄虛而蕩”之病。所以,唯有主客觀兩方面的圓融相即,才是儒家義理的最優形態,也就是他說的“圓頓無二”之義。
牟宗三對于明道之一本論給予極高評價:“至明道則兩方面皆飽滿,無遺憾矣。明道不言太極,不言太虛,直從‘于穆不已’‘純亦不已’言道體、性體、誠體、敬體。首挺立‘仁體’之無外,首言‘只心便是天,盡之便知性,知性便知天,當下便認取,更不可外求’,而成其‘一本’之義。是則道體、性體、誠體、敬體、神體、仁體乃至心體,一切皆一。故真相應先秦儒家之呼應而直下通而為一之者是明道。明道是此‘通而為一’之造型者,故明道之‘一本’義乃是圓教之模型。”[10](上冊,P.38)在這一理想模型中,天命實體既存有且活動,內在又有超越,牟宗三將它與朱熹的理氣二分,心、性、情三分的模型相對照,認為后者只是將《易》《庸》的天道提煉成了存有論的理,將《論》《孟》的仁與性提煉為理,而“心則沉落與傍落”[10](上冊,P.39),也就是說心喪失了“活動義”而只具有“理則義”,所以說將后者的理只存有不活動,只超越不內在。牟宗三把朱熹的理學視為“主觀地說是靜涵靜攝之系統,客觀地說是本體論的存有之系統,總之是橫攝系統,而非縱貫系統”,并由此斷定朱子學為儒學之“歧出”[10](上冊,P.39)。可見,正是通過對于明道一本論的深入詮釋,牟宗三建立其道德形而上學思想體系,并完成了對于儒學內部不同流派之判教,一本論也成為這一思想歷程的核心概念之一。
那么,明道之一本“圓教模型”,立足點何在?他說“天人本無二”,是說人為天道所生,人道自然包含于天道之中;同樣,人道也蘊含并顯現了天道,就此而言,“天人本無二”是人本于天。那么,人如何證實天人不二?只要在心上體認即可,不必外求,故明道之一本論,是以心性論融攝宇宙論,從而確立心性本體論的地位。他形容一本的精神境界說:“若真明透了,則當下即是,當體即是永恒,當體即是一體。此亦睟面盎背,全體是神,全體亦是形色也。此種圓頓表示乃是盡性踐形之化境[10](中冊,P.22)。所以,在牟宗三看來,明道之一本是在本心呈現中,通過盡心踐形,使形色成為心性的載體,進而心、性、天直接為一,這的確是心性充其極的結果。
從明道“當處便認取,更不可外求”的話看,他的一本論首先是一種體認工夫,是本于心性的工夫論,此種體認工夫自然不是對象化的客觀認知行為,而是本心的自我呈現與證知。牟宗三在解釋明道之“窮理盡性以至于命,三事一時并了,元無次序”時說:“此即為因工夫之蘊涵而‘一時并了’也”[10](中冊,P.87),明確指出明道的一本的工夫論特征,是在工夫中蘊涵并體認出來的。牟宗三在解讀明道“不可將窮理作知之事。若實窮得理,即性命亦可了”時認為:“此即涵知行合一之意”,“窮字是徹知而朗現義”[10](中冊,P.86),所謂“徹知而朗現”,就是本心徹底的自我顯現,即天人一本以及心、性、天之合一,正是通過本心的朗現而證知的。所以,雖然明道并不否認天道的客觀實在性,但是其一本思想之建立,卻是沿著心—性—天的逆覺體證路徑,通過心來證知并顯現天命實體,所以牟宗三說這一系統是“提出‘以心著性’義以明心性所以為一之實及一本圓教所以為圓之實。于工夫則重‘逆覺體證’”[10](上冊,P.42),此說抓住了明道一本說的主要特征,從工夫論看,所謂天、命、心、性為一,是一于心。
所以,牟宗三特別強調明道一本論的實踐特征:“‘一時并了’雖不受影響,然‘至命’如是向前至,則在道德踐履上為嚴切,而有獨立之意義。如是向后至,則只是至于性之源,即喪失‘至命’之獨立意義,而亦喪失其道德踐履之嚴切義”[10](中冊,P.87),那么,他所謂的道德踐履究竟具有怎樣的屬性呢?他說,“要者是在明道所體悟之性體無論是本體宇宙論地言之,或是道德實踐地言之,皆是即活動即存有者,是心與性為一者”[10](中冊,P.57),所以,他所謂的道德踐履的本質在于體認本心并即心顯性,此種踐履之根本是一種主觀精神領域活動。所以,牟宗三又說:“客觀地、本體宇宙論地言之,是道體、天理實體、于穆不已之天命之體;而主觀地、道德實踐地言之,則是仁體、心體、性體;而主客兼攝,‘一本’無二。”[10](中冊,PP.58-59)這里將“客觀地”與“主觀地”并列,又將“主觀地”與“道德實踐地”放在一起,并非偶然,因為在此種一本論的視域下,所謂道德實踐,正是主觀領域的實踐,而所謂的“主客兼攝”,只能是通過精神工夫兼攝蘊涵客觀實踐,以凸顯人之道德主體性。這樣一種以本心彰顯性體并融攝天道的一本工夫,是基于孟子心性論的發展,不但不同于朱熹的工夫,與孔子仁、禮并重的踐履,也顯然有所不同。此種內在超越的提出并非偶然,它除了儒學內部心學一系的歷史淵源外,更與現代新儒家花果飄零的特殊時代背景有關。在這一個四無傍依的時代里,儒者除了自己的心性之外已經別無依靠,這反而極大地激發了他們的使命意識與主體精神,促使他們重新詮釋儒家思想資源以維系儒家的精神命脈。但是,為現代新儒家所特別看重的這種一本論,由于過于主觀化、心性化,將原始儒家所一向注重的道德實踐轉變為純粹內在的心性踐履,在極大提高了儒學哲學化思維水平的同時,也失去了通向普羅大眾人倫日用的途徑,構成了這一時代儒學思想發展中的重要缺憾。
另外,牟宗三還說:“它是心,是理,是神,亦是情(以理言的本情、心之具體義)。在此直貫創生之‘一本’之下,心性天是一,心理是一。心與神絕不可一條鞭地視為氣,天心本心不是氣,誠體之神不是氣。”[10](中冊,P.17)這里提到心也是情,但不是一般的情,而是“以理而言的本情”,也就是說,情屬于理而非氣。下面重申天心、本心不是氣,依然強調天命實體和心性本體與氣的分野。明道說“道亦器,器亦道”,又說“氣外無神,神外無氣”,牟先生對此的解釋是:“此只是直貫創生的體用不二之圓融說,非是體用不分,形上形下不分,雖分之,卻亦非是心神俱屬于氣,而道唯是理也。”[10](中冊,PP.17-18)這里否定“心神俱屬于氣”,其實是針對他所斷言的朱子將心、性、情三分,以為“仁性愛情,惻隱羞惡等亦只是情;心是實然的心氣”而言,他認為這樣分辨的結果是“心與性成為后天與先天、經驗的與超驗的、能知與所知的相對之二”,從而違背了一本之義。但是,不屬于氣的心和情如何具有活動功能,依然是一個需要考量并解答的問題。
本心的呈現作為工夫的本質與核心,牟宗三雖然在論及工夫時也提到身體方面之睟面盎背等,但是,身體已經失去了其獨立意義而淪為精神的附庸,身體氣象的變化似乎只是本心呈現的直接副產品,是心性凸顯的無條件的媒介。更重要的是,由于情被歸于理,被視為與氣無關的存在,這自然是繼承了宋明理學中理氣二分之基本原則,卻在實際上抽去了理的活動義,消解了道德涵養的動力因。這樣的所謂工夫,由于是運行在一片空闊潔凈的心與理的世界里,似乎天馬行空,無所掛礙。實際上,從儒家修身的本來意義上講,從孔子“非禮勿視”等四勿的意義上講,從曾子“動容貌”“正顏色”“出辭氣”的意義上講,這種工夫已經不再是原始儒家真正意義上的修身工夫,而演變為一種純粹的意識行為。這種意識雖然具有了精神的純粹性和自發性,卻失去了與身體的聯系通道。因為身體與心性,已經被割裂為兩個不同質的世界,所以,盡管牟先生將朱熹的理與氣說成是異質異層的存在,因此只存有不活動,而他本人通過詮釋明道心性論所勾勒的一本論,似乎消除了理與氣異質異層所帶來的困擾,實際上,這種克服僅僅是精神上的,它是通過阻斷心與氣的聯系完成的。但是,儒家的工夫是一個統攝身心兩面的整體性實踐,一旦將心與情提升到與氣無關的絕對形而上層面,心與身的聯系已經被隔絕,情與性的關系也已經被隔斷。而上述聯系則是原始儒家特別看重的,是儒家工夫論的實踐前提,如果沒有了它,則儒家的工夫便在實際上有被鑿空之嫌,因為心性或者性情已經找不到通達身體氣象和人倫日用的生活世界的橋梁,它從此就將淪為純粹的精神現象而無法再與生活世界建立聯系。
在這方面,牟先生甚至比孟子的心學更徹底,因為孟子的良知良能也依然與氣存在直接聯系,故有夜氣說和養浩然之氣說。從理論上說,牟先生所構建的道德形而上學是純粹的,是一種嶄新的創構,但是,從工夫論的角度看,它則意味著本來意義上的儒家工夫論的消解,這一點,不管是與孟子的心性論相比較,還是與《性自命出》的一本論相比較,都是顯而易見的。與牟先生所稱贊的明道一本論相比,《性自命出》的一本論同樣實現了天人貫通,不過,由于將性界定為情氣,它是在氣論的基礎上將天人一本落實到性情一本,進而將性情一本發展到情道一本,完成了道德基礎與道德原則、內在性情基礎與外部禮樂教化的有機統一。這種一本論是以早期禮樂文明為基礎的一本論,它雖然從外觀上缺乏明道一本論的道德主體性高度,卻在普通人人倫日用的道德踐履中具有更為切實和重要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