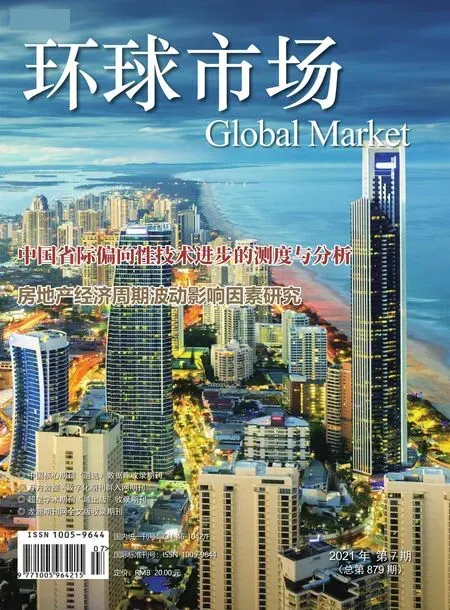數字金融緩解中小企業信貸約束研究
鄭含笑 浙江金融職業學院
一、引言
作為穩就業、促經濟、謀創新的基礎力量,中小企業是市場經濟主體中占比最大、活力最強的群體。中小企業的發展,是實現“六穩”“六保”目標的重要支撐。然而,普遍存在的中小企業融資難、融資貴問題長期以來成為制約其發展的重大阻礙,使得中小企業發展轉型難、抗風險能力差。加之新冠肺炎疫情的沖擊,中小企業普遍面臨訂單銳減、原材料成本激增的經營困境和現金流斷裂、融資匱乏的財務困境。當前,采取措施緩解中小企業的信貸約束,降低融資門檻、減少融資成本、擴大融資渠道,對于后疫情時代中小企業群體的復蘇和鞏固經濟恢復發展勢頭具有重大意義。
過去幾年中,中國數字金融飛速發展,同時也極大程度地改變了中國的金融格局。根據全國工商聯(2020)發布的《2019-2020 年小微融資狀況報告》,新冠疫情期間,80.4%被調研的微型企業和個體經營者存在融資需求,其中有40.5%已通過互聯網銀行(如網商銀行、微眾銀行)獲得信用貸融資。可見,數字金融能夠為一直以來存在突出信貸約束的中小企業提供新的融資渠道和金融服務。
二、傳統金融對中小企業的信貸支持困境
雖然國家此前已發布多項政策敦促銀行類金融機構著力幫扶中小企業解決融資難題,新冠疫情暴發期間也密集出臺一系列救助政策,但只能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中小企業的燃眉之急,難以充分、持續地滿足大量中小企業的信貸需求。
(一)融資難:觸達渠道有限,放貸成本高
之所以融資問題會成為制約中小企業發展的頑疾,是因為中小企業群體通常被排除在傳統金融體系之外。商業銀行主導的傳統金融體系通常追求服務資信等級高的大型國有企業、上市公司或知名的民營企業。獲客方式和貸款審核通常以線下網點為服務提供載體,并采用人工的方式進行操作和盡調,單筆放貸規模大、周期長、成本高,往往無法對接到數量眾多且知名度低的中小企業“短頻快”的小額貸款需求,直接導致了中小企業的融資難問題。
(二)融資貴:風控能力有限,貸款利率高
相對于商業銀行以往的目標客戶來說,中小企業大多缺乏規范財務數據、信貸記錄和抵押品。央行條法司副司長謝丹在央行2021 年1 月25 日舉行的“金融支持保市場主體”系列新聞發布會上表示,中國中小企業約60%以上的資產為應收賬款和存貨,但金融機構擔保貸款中,約60%要求提供不動產擔保,動產擔保融資不足40%。這就使得以抵押擔保為核心風控手段的傳統金融機構無法給予中小企業恰當的資信評估結果,進而導致中小企業面對的融資利率節節攀升。
三、數字金融緩解中小企業信貸約束
數字金融應用數字技術突破了傳統金融服務固有的局限性,充分發揮了“長尾效應”,對傳統金融產品和商業模式等進行數字化賦能。
(一)打破地域限制,拓寬金融服務廣度
數字金融打破了金融服務對地域的限制,拓寬中小企業獲取金融資源的渠道,從而緩解信貸約束。數字金融僅通過網絡平臺,就可以實現轉賬支付和借貸投資等功能,即便一些落后地區缺乏銀行網點及ATM 設施,仍能夠通過個人終端設備提供基礎的金融服務。這不僅彌補了傳統金融機構服務普及率的不足,使得融資更加便利可得,也從根本上解決了傳統金融機構獲客成本高的問題,有效彌補廣大中小企業群體長期以來的金融資源不足,對其改善經營狀況和轉型升級均能產生積極的促進作用。
(二)降低風控成本,繞開信用評級劣勢
依托于大數據技術,數字金融平臺能夠以較低的成本對中小企業進行風險評估,降低其融資成本。與傳統金融信用評估側重財務報表、可抵押資產等硬指標不同,數字金融更傾向利用貸款人前期在互聯網平臺上積累的如購銷、還貸、繳稅、出行、餐飲等海量行為數據描繪“用戶畫像”,通過大數據分析與評估,構建中小企業的信用評估模型。這種基于大數據的風險評估手段節約了風控成本,同時也繞開了中小企業在硬指標上的劣勢。據統計,我國三家新型互聯網銀行(微眾銀行、網商銀行與新網銀行)每年分別可以發放約1000 萬筆的小微或者個人貸款,其平均不良率保持在1.5%上下,低于2019 年全國商業銀行不良貸款率1.86%。
(三)提高融資效率,增強抗風險能力
對于中小企業來說,現金流的穩定對于企業的持續經營至關重要。因而當風險來臨時,獲得正規金融服務對中小企業群體來說至關重要。數字金融在一定程度上替代了非正規“熟人借貸”“民間借貸”,改善了中小企業的應急資金來源。特別是在2020 年春季新冠疫情暴發期間,數字金融的助力弱勢群體抗風險能力得到了極大發揮。比如一家互聯網銀行小微企業貸款的“310”模式,三分鐘線上申請貸款,一秒鐘資金到賬,零人工干預。這大大超越了傳統金融機構的放貸效率,有力地滋養和保護這些國民經濟毛細血管,也提高中小企業在突發事件沖擊中的抗風險能力。
四、結語
中小企業的信貸約束難題是國家與社會關注的重點問題,數字金融確實能從不同的層面打破傳統金融的桎梏,為中小企業的金融服務帶來突破。應進一步鞏固數字金融現有的成果,探索其未來的發展方向。一是盡快完善數字金融的基礎設施建設和信貸數據共享、保護機制;二是針對數字金融建立動態平衡的監管框架,嚴控風險;三是強化政府部門對數字金融的支持和引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