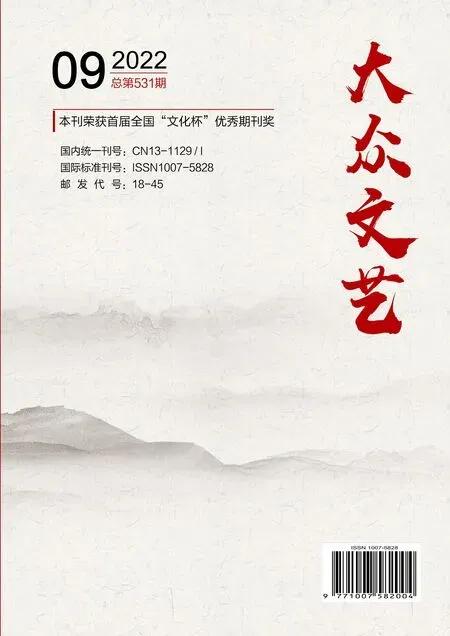明代小說中女性意識的現代性初探
劉延霞 (廣西大學 530000)
一、明代女性的現代性意識
明代文學上承元代文學的余波,延續了元代以來的敘事文學并發展為最顯要的文學特征,以《三國志》的出現為標志預示著長篇小說時代的到來,隨著思想文化趣味的移動,出現了世情小說與更富有生活氣息高揚個性的戲曲作品。小說是明代文學中最富有生命力的文學體裁。
在對明代小說的研究中,審美意識的移趣是研究的中心,明代小說創作者與讀者都被打上了市民化、個性化與趣味化的標簽,明代小說史以審美意識的移趣為變更的歷史邏輯,呈現出由雅入俗并臻于頂峰。在這種審美意識背后的生命意蘊與主體意識的研究接踵而至,研究者們挖掘出審美意識移趣背后的成因是明代個體生命意識的迸發,是禁錮于壓制之下對人欲與自由的高度向往。
隨著女性意識研究的勃發,出現了大量女性形象的歸類與研究,明代小說中對女性形象較男性形象而言運用了更多的筆墨,接連有研究者強調明代小說中女性形象的傳統一面,女德觀念的強盛并大力批駁其中的另類女性形象。隨著女性意識研究的深入,逐步有意地發覺到了明代小說女性形象中挑戰傳統,順應時代思想潮流富有現代意識的一面。
明代女性意識的現代性研究中女性主體意識的覺醒能夠被證實,對明代女性意識的研究理應從史實與現象層發展至意識層的研究,女性意識的萌動所帶有的現代性特征也理應得到正視,然而對于明代女性意識的坎坷發展以及后來的斷代發展并未有過對其萌發與斷代的分析,明代女性所面臨的困境是精神與現實之間的深度糾葛,現代性女性意識一閃而過的火花被永遠地保存在小說文本之中。
對明代女性意識的分析往往從三個層面開展研究,社會層的分析以史實為研判的基本材料,對明代女性的社會地位與觀念轉向的研究都有所成果,對史料的過度依賴很難使研究轉向女性意識自身內涵的研究。在意識層的分析往往是以他者對女性的建構中得出結論的,對女性意識的研究是從男性意識對其的壓制中最終得出男權價值取向對女性意識的強而有力的影響,反而忽視了明代女性意識根本性的變化,缺失了對女性意識的內部注視。從文化層研究女性意識有著多樣的研究模式,以各式文本中建構起明代女性形象譜系并由此窺見了明代女性意識的進步性。文本是較史實更能展現社會觀念的藝術載體,從文化層中研究女性意識形態的進展能有多樣的文本支撐也能夠較生硬的史實政策解讀出更真實的社會反映,然而單一地從文化層研究女性意識又難以扎實地推進研究。
明代女性意識的現代性顯現為自我意識、選擇意識和自由意識的進步。女性意識首先表現為自我意識的覺醒,女性意識的萌發以自我的注視為起點,與他者相區別開來。隨著社會經濟因素的調整,性別意識差距出現了變化。女性在社會意義的賦予與被賦予上有了不同以往的觀念,在區別于男性意識與附會于男性的封建性別意識外還有了進行選擇的余地與權利。自由意識是女性意識的最高層面展現,自由意識展現為在認識自我具有較高的自我意識后能夠作出忠于自我而非社會意義的選擇。從小說中能夠尋跡到女性意識的現代性顯現,然而明代女性意識的發展并非一帆風順,女性意識自身也存在著精神價值實現的困境,在現實生活中這種“現代性”卻直接造成了一系列的社會問題。
現代性是一個開放而又包容的話題,在當代對現代性的種種反思中,都致力于將現代性放置于一個更為宏大的文化背景下,而現代性一詞的內涵也在不斷地得以填充豐富。自王德威先生提出被壓抑的“現代性”,“沒有晚清,何來五四”的論斷所暗含的是對現代性這一概念的獨特領會。現代性說到底是一個時間上的概念。于文學歷時邏輯而言,明代女性意識不同于以往展現出前所未有的形態,是在封建時代的特殊環境下萌發出的群體意識卻在歷史時空的演變中逐漸湮滅。明代女性意識的現代性研究有益于對現代性的內涵進行進一步的思索與探尋。
二、社會背景分析
明代女性生活的社會宏觀結構設置仍然是男權為主的封建社會,封建專制的加強伴隨著宗教禮法的完善,商品經濟的發展與文化界的活躍是明代社會的典型特點。明代女性的社會地位從法律文書中權利賦予狀況來看并不樂觀,與前代經濟地位類似,女性并沒有占有經濟生活資料,沒有獨立的生產生活能力,明代女性相比唐宋女性的遺產繼承能力更為薄弱。然而社區經濟的發展程度不一,在江南手工業發達地區,女性的經濟生產能力更高,話語權與地位也就更高一些。據《松江府志》記載:“百工眾技,與蘇杭等。若花米踴價,匹婦洗手而坐,則男子亦窘矣。”在蘇杭等地的女性擁有了一定的社會經濟能力,社會地位有了一定的提高。
明代女性的自致地位與前代有所不同。明代統治者非常注重對女性的教化,女教書籍的編纂、出版和發行都受到了統治者的高度重視,明太祖:“觀歷代宮闈,政由內出,鮮有不為禍亂者也。”女教的設立一方面是為了加強對女性的規范,另一方面女教能夠提高女性的教育水平。根據方志列女傳和墓志銘記載,富紳和高門仕女大多鼓勵家庭女性接受知識教育,女教的盛行對女性觀念的進步有所幫助,對女性的社會互動有益無害。隨著教育的發展,明代女性在文學成就上女性作品總集的數量遠遠超過了前代,這也表明明代女性的社會地位隱形之中的提高。
人類成長是社會化的歷史,明代女性的社會化過程以共時的邏輯來看,明代女性的社會化與前代女性的社會化歷程類似,同樣是在封建社會的社會環境設置下對角色的逐步認同過程。在社會化的主要主體中,家庭的成長氛圍間接地表明了社會對明代女性的社會期望,明代的家族教育呈現出對女性的高期望,甚至出現了葉氏家族女性群體文學的盛況。社會所期望的女性較前代而言是更為才德兼備、賢惠淑敏的女性形象,家庭便不斷地在家庭教育中加強社會期望對女性成長的影響。
在社會化的過程中值得關注的是明代的女性價值賦予。在傳統權威的社會中,女性的價值賦予一直由男性執行,宗法制社會制度下男性掌握著家族的話語權,從皇帝到家族中的嫡長者他們是社會期望的搭建者,女性始終都是由男性創造的“鏡中我”,社會價值的賦予權以性別為首要條件,明代體制中至上而下落實價值賦予。然而這種價值的單一賦予在明代后期出現了新狀況。
明代政治思想的高壓與失控適得其反,心學強調“本心”,認為“此心純是天理”,李贄高倡“私者,人之心也。人必有私,而后其心乃見。”明代中期出現“獨抒性靈,不拘格套”的文學思潮,追求文學的個性特征,明代中后期戰亂四起,社會觀念更是顛簸震蕩,李贄《答以女人學道為見短書》:“夫婦人不出閫域,而男子則桑弧蓬矢以射四方,見有長短,不待言也。”認為女子的“見短”是后天所致,并且力行鼓勵自己的兒媳改嫁。不僅如此,若干湯顯祖、馮夢龍等作家在文學作品中都塑造了生活鮮明的新女性形象。大眾傳媒對女性的再社會化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女詩人項蘭貞潔臨終時說:“吾于塵世,他無所戀,惟《裁云》《浣露》小詩,得附名閨秀后足矣。”她走出閨閣,以詩歌為平生所愿,可見價值觀念的轉變已然不再囿于一閣之內,而是走向了更為廣闊的世界。而據文獻記載,那時候未婚女子可以自己選擇情郎已經是較為普遍的現象。
整個明代社會女性的社會化與價值賦予都存在著一股張力,統治者以體制的形式對其規范并屢屢通過法律、文教、旌表加強女性的意識管控,而社會結構與社會互動的變化,女性的價值逐漸有了顯現,中后期思想家“異端”言論更是對傳統權威形成了重擊姿態,而文學家們以其自身以及作品的影響力都在改變女性的價值賦予。男性不再是女性的唯一的價值賦予者,女性也有了對自身的價值認同。
三、文本中的現代意識
文學藝術既是文學家思想家對女性意識意見產生與發揮作用的重要陣地也是社會觀念彰顯的先鋒領域。文本中明代女性的現代意識體現為自我意識、選擇意識與自由意識。
“三言二拍”有著說話藝術的特色與體裁上的限制,女性形象的刻畫上創造出新的藝術空間。譬如“杜十娘怒沉百寶箱”中的杜十娘,杜十娘的形象頗有自我精神,她雖是娼妓出身卻個性十足,決不肯隨波逐流人云亦云。而在蔣興哥的故事中,即使是與人茍合被棄逐后的三巧兒面對前夫受難的境況竟選擇無論怎樣也都要幫上一幫。“三言二拍”中的女性,較之以往的女性形象被作者賜予了更多的敘事焦點,無論是從個性還是行為上都與之前的女性形象大為不同。
敘事焦點的變化與體裁的發展變化有著密切的關系,明代小說《金瓶梅》較元代話本和諸宮調而言有更為廣闊地敘寫空間。在話本和諸宮調中只能通過“回顧覷末下”簡短暗示,讀者需要屢屢猜測回味才能品獲這短短動作背后鶯鶯按耐不住的春心。在《金瓶梅》中則是一番新的表現:潘金蓮勾引武松時,敘事者赤裸裸地表現她的“淫”思,被拒絕后,潘金蓮先是覺得被羞辱而后由愛生恨由恨生怒,作者并不吝嗇地將她內心全盤托出。
在元代的話本與諸宮調中,女性并沒有過多的自我選擇意志,即使是婚戀也始終要在禮制之下,為自由戀愛魯莽又勇敢的鶯鶯也不免要聽從長輩的規勸依于禮法,在明代的小說中自我選擇的意識則大大增強。社會空間所給予明代女性選擇的權力其實并不高,不論是民風的切實反應還是敘述者的強烈愿望都表明了明代女性意識的另類與前衛。
同是講鶯鶯與張浩私定終身的故事,明代《宿香亭張浩遇鶯鶯》與元代《西廂記》的結局就大相徑庭,鶯鶯指控張浩“忽背前約”,要求法庭“禮順人情”,實則肯定了“禮”向“情”的傾斜。1兩個朝代的鶯鶯人物形象大為不同,前一個卯足了勇氣大膽地自由戀愛,卻始終畏手畏腳,后一個鶯鶯則是情之所至,無所畏懼,值得肯定的是明代女性所迸發出的自我選擇意識的超前與不可阻擋。
選擇意識的成長與社會空間的包容緊密相關,明代政治思想的高壓與失控境況下,對個性與人欲的肯定必然使得女性意識得以萌發。一面是程朱理學的強壓,一面又是對本心本欲的發現,女性得以在此空隙中重新發現本我的存在價值。
時代所特有的自由精神令敘事者創作精神也飽含自由的創作態度,所創作出的故事不避惡與欲。欲望往往是男女遮羞布下的羞處,道德枷鎖實在過重后,一聲聲重新發現人性的口號都是在為了打破枷鎖而作出的絕望呼告,本是為了釋放封建的意識枷鎖,也使得女性從中開始正視自我。
潘金蓮作為時代的世情人物代表,她身上的欲是一步步走入惡的,她最能正視自身的欲望并為之努力作出付出與犧牲。欲望與欲望之間,自我的選擇和自我權利的實現高于他人的權利,甚至高于生存權,欲就淪為了惡的遮羞布,即使欲本身而言并沒有錯,女性意識也是順應時代而產生的精神哲學,卻淪為了自由泛濫的終局。
女性意識暴露出了人性的劣根一面,過度的泛濫和毫不節制勢必造成對男性地位和家庭結構的顛覆。另一端則是女性對于個人價值精神的尋覓困難重重。在體制的重壓與封建的傳統權威之下,明代女性意識并沒有得以糾正其偏差,在清代被霸道地斬殺。文化專制與思想的高壓令元明的女性意識迅速湮滅。在清代的文學中,戲曲和小說中女性形象毫無自由自我可言。即使是古代小說的頂峰之作《紅樓夢》中的女性也都只是封建家族的陪葬品,再無明代女性“狂妄的”自由精神。
自五四以來,男尊女卑的思想漸被推翻,女性意識重新出現在中國,新的女性意識不僅有著自我自由的選擇意識,并且突破了社會制度的封閉化,物質上的獨立與精神上的獨立相輔相成,女性意識進入女權主義的新階段。
回望古代文學史,女性意識在元代有了初顯之形,在明代形成巔峰之勢,卻在清朝徹底斷代,直至五四步入新階段。明代女性意識的斷代是必然的趨勢,女性意識出現的社會環境致使女性意識畸形發展,與男性和男權社會的對立態勢必然一敗涂地。女性意識是在封建時代的特殊環境下萌發出的群體意識,于文本中所窺見的形態與脈絡變化無可置疑,種種差異致使明代女性意識成為一個特殊的歷史存在,在文學史上更是獨具現代性,這份現代性與如今的女權主義思想對應折射出些許思想的花火,在千年文學思想史上更是異軍突起的存在。
于現代性的意義而言,明代女性意識中的現代性都滋生于大時代的文化背景土壤中,現代性始終是隸屬于進行時的名詞充斥著辯證的意味,而突發意識快速泯滅的現實則告訴我們現代性也并非是永恒而不變的進步的原素,時空與意識的更替是現代性長存于歷史語境中的奧秘。
注釋:
1.袁行霈.中國文學史(第四卷)[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162-1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