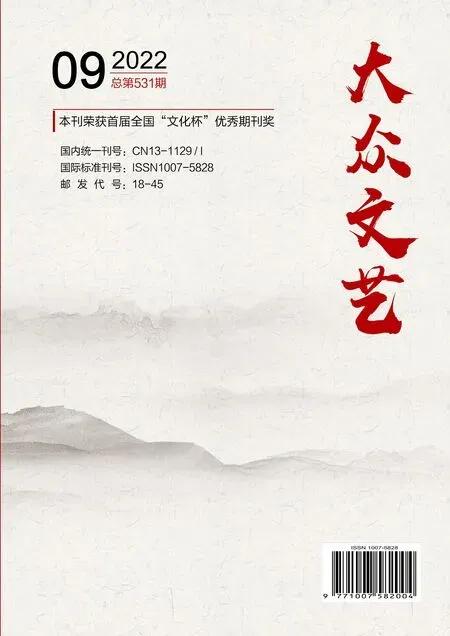“傳神者,必以形”
——以董希文1954—1961年藏區(qū)風景畫作品為例
李奕銘 (首都師范大學美術學院 100048)
一
董希文1914年出生于浙江省紹興縣光華溇村,少年時期曾先后在蘇州美專、國立杭州藝術專科學校、上海美專進行學習,對江南地區(qū)的風土人情極為熟悉,1938年因抗戰(zhàn)之故,輾轉于江西、湖南、云南、貴州、重慶、甘肅、北京等地求學生活。這樣的經歷讓董希文在1949年之前就已經有了對江南、西南、西北地區(qū)自然風貌的深入體會。董希文個人豐富的成長經歷和動蕩的時局都給他的藝術創(chuàng)作帶來了新的動力和多種表達形式,觀者能從其十九世紀三十到四十年代的作品中感受到他想要用自然表達一種民族情懷和生活感受,他從不同景象、不同民族中獲得的精神體悟在作品里不斷映照出來并在其后的創(chuàng)作中得到深層延續(xù)和開展。
新中國的成立使中國文藝界擔負起了空前的歷史責任,人民經歷了戰(zhàn)爭的摧殘和生活的艱難,他們對解放了的新中國充滿美好的向往與期待。1950年創(chuàng)刊的《人民美術》在其發(fā)刊詞中即指明新中國美術家的主要任務是配合國家進行宣傳工作并在宣傳過程中發(fā)揮各自專業(yè)特長,如何重新將自然景象納入新的歷史語境之中,如何讓表現對象與社會主義建設高度融匯,都成為新形勢下不得不面對的創(chuàng)作任務。這種時代革命要求、社會氛圍使董希文的創(chuàng)作思想獲得滋養(yǎng)、藝術精神進一步打開,他的作品逐漸突破繪畫形式的束縛,自然被滲入一種全新的意義。
建國后,董希文曾三次進入藏區(qū)寫生,其原因來自國家對于展現新社會面貌的創(chuàng)作要求,同時,畫家對民族繪畫形式語言取得的初步探索經驗和深入邊區(qū)的生活經歷也給他的藏區(qū)繪畫作品帶來了巨大的創(chuàng)作動力和情感印痕。青藏高原在進入董希文視野的時候,正發(fā)生著翻天覆地的變化,現代化建設如火如荼地開展,建設過程中各族人民團結一致、不怕苦不怕累的精神,將個人的理想注入到新社會事業(yè)之中的執(zhí)著追求,都賦予了董希文藏區(qū)繪畫作品更豐富的思想性內涵。
1954年2月5日,董希文開始了首次進藏寫生活動,他參加了全國人民慰問人民解放軍代表團第三總團前往四川康藏。新中國成立時西藏是唯一沒有近代道路和近代交通工具的地區(qū),自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后,中央人民政府為促進西藏地區(qū)發(fā)展調動了巨大資源建設公路,幾十萬筑路大軍冒著生命危險在懸崖峭壁上開山劈路,董希文慰問途中將解放軍的堅強意志收入眼里,記錄著建設的狀況。
《春到西藏》是這一時期的重要作品,它并不著意表現開車典禮或施工狀況,而是選擇大片自然景象。觀者可以從畫面中感受到西藏這片古老土地上散發(fā)出的新鮮氣息。作品構思之初與傳統山水畫就有內在關聯性,畫家不僅采用中國畫里常見的之字形構圖,并大膽使用類似“平遠”式的表現方法把畫面切割成土地、遠山和天空三部分。畫面中隨著公路的伸展能看到運輸車隊、雪山、天空,層層傳遞十分流暢。
董希文此畫的構圖處理、空間表現都融入了古代傳統繪畫手段,他想要拋開自然景觀的表象向傳統繪畫學習,去追求對象的生命本質,董希文早在少年時期就形成了深厚的文人畫素養(yǎng),他在技法上追求“油畫中國風”的同時,更在作品中融入傳統文人“寄情于景”的情懷,他希望創(chuàng)作出飽含真摯情感的作品。
二
董希文通過《春到西藏》把他對于新中國的精神體會借助自然景觀獲得抒發(fā),而這種通過自然流露出的人文主義溫情也更加飽滿地展現在他二次進藏的寫生作品中。1955年,中國軍事博物館向董希文發(fā)出創(chuàng)作“長征題材”革命歷史畫的約稿,同年,董隨八一電影制片廠攝制組沿當年紅軍長征路線進行寫生,歷時半年之久,寫生創(chuàng)作達二百五十余幅,這段歲月也成為了他個人藝術生涯的鼎盛時期。從現有資料來看,長征路線風景寫生作品,可分為革命歷史題材的風景畫創(chuàng)作和單純風景寫生。可以說,在二次進藏過程中董希文通過自然風情重構了歷史精神和中國的新形象。
董希文在上世紀50年代初進行了一系列革命歷史畫創(chuàng)作,《北平入城式》(1949)、《抗美援朝》(1951)、《開國大典》(1952)等作品都是根據主題需要而設定的形式語言,主要目的在于揭示主題,因此更具理性意味。與此不同的是,他的長征路線寫生作品從現場感受出發(fā),將革命足跡和自然風景結合起來,把大自然的意象轉化為一種歷史的訴說和民族精神的體悟,正是通過這種對景寫生我們能夠看出他彼時內心情緒的迸發(fā)。
瀘定橋位于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瀘定縣的大渡河上,位于此地的瀘定鐵索橋是四川入藏的軍事要津,飛奪瀘定橋更是紅軍長征途中的決定性戰(zhàn)斗。從《大渡河瀘定鐵索橋》的構圖上看,橋身貫穿整個畫面透視非常深,橋面上有許多來往的行人,近處的藏民背著背簍,有些三兩成群的交談著,頗具生活氣息,對岸房屋瓦舍中紅旗迎風飄揚,種種展現都是典型的新中國模樣。畫面河水近景的筆觸帶有強烈炫動感,使人感到水流滾滾、湍急異常,畫家仿佛把紅軍強渡時內心的堅定勇敢和理想信念訴說給了觀者。
長征題材創(chuàng)作中針對瀘定橋的主體表現產生過一批作品,李宗津和劉國樞在1950年代也進行了同樣的嘗試。兩者的《強奪瀘定橋》和《飛奪瀘定橋》都將戰(zhàn)士們的舉手投足做了精心安排,且更傾向于展現戰(zhàn)爭發(fā)生時的壯烈境況,以最大限度去強調主題性和敘事性。同樣描繪瀘定鐵索橋的董希文卻把昔日紅軍長征的足跡轉化為祖國山河圖景,把革命性轉化為抒情性。“長征”在中國革命史上的重大歷史意義與董希文寫生作品所呈現出的剛健、純樸、明朗格調交相呼應,形成了生機磅礴的民族精神象征。
董希文的長征路線寫生,除了有對紅軍歷史足跡追溯的革命題材作品外,還有通過同時代事件展現新中國氛圍與人心面貌的歷史畫作品。毛兒蓋位于四川阿壩藏族自治州松潘縣的西部,曾是千里無煙的荒草地,經過藏族兒女的辛勤勞動,已然變成了郁郁蔥蔥的麥田和漫山遍野的牛羊。《毛兒蓋盛會》表現了藏族人民為慶祝豐收在寺院廣場上舉行集會的場景,畫面中人聲鼎沸,寺院、服飾、帳篷以及正在表演的藏戲都充分體現了少數民族地區(qū)的情味。江豐評價:“它那闊筆涂刷的強烈對比而又顯得十分和諧的色彩處理,非有高明老練的技巧和大膽果斷的魄力,是絕不能辦到的。”
“抒情性小品”是二次進藏風景畫作品中另一種重要的內容表現形式,相對于歷史性題材的畫作,這類作品傾向于作者自身感情的抒發(fā),獨立性更強。從這些畫作里觀者可以更多地讀到董希文的“造化”與“心源”,風景畫無論是色彩語言還是形式結構,都展現出了他對藏區(qū)風物和高原凈土的向往,他不斷地用手中的畫筆塑造著自己的“心跡”。
董希文的風景小品雖為寫生也畫得十分細膩。他在《班佑河畔高草地》和《草地爛泥坑》這兩幅小品中有意忽視了西洋畫法里復雜的色階變化,特別抓住了草地和天空的鮮明本色。畫家并不在意描繪的是不是或像不像眼前的景物,而是傳達一種情緒,這種不在意形象客觀逼真性的處理方法,在《二郎山看日出》《二郎山遠眺大渡河》《大雪山倉德梁子》等作品中也同樣體現出來。長征路線的寫生不僅是一次對革命史的追憶,對董希文來說,則更是審美情感、思想境界的提升,他以無比的熱情和執(zhí)著的精神將風景畫創(chuàng)作與藝術感情成功融匯,并表現在自己的作品里。
三
如果說,首次進藏作品是董希文風景畫抒情的發(fā)軔,長征路線寫生是一次生動明朗的詠唱,那么時隔6年之后的第三次進藏寫生作品,就是董希文藝術創(chuàng)作中的一支豪情壯懷的浩歌。1961年7月,“董希文與吳冠中、邵晶坤一同參加中國美術家協會組織的西藏寫生活動,第三次到達藏區(qū),深入日喀則、江孜、帕里、亞東等眾多牧區(qū),”此行藏區(qū)情況發(fā)生巨大變化,自1959年西藏民主改革后,社會風氣煥然一新,畫家的主要任務是表現翻身農奴,歌頌他們成為主人后的社會新氣象。董希文在西藏地方政府的協助下,深入了解當地農村、牧場,和藏族人民進行了廣泛的接觸,歷時三個多月,創(chuàng)作作品40余幅。
翻看這次寫生中為數不多的風景畫,可發(fā)現作品的造型更概括,筆觸厚重有力,色彩單純濃郁,畫面內在表現更具張力,表現內容融入了更多的浪漫主義精神。《喜馬拉雅山朵瓊湖邊》在簡單廓形中,畫家更注重抓取特點,西藏陽光很強,自然景觀的遠近感就弱些,所以董把色彩處理的肯定、結實,加強明暗對比,畫出雪山的透明感。通過清新爽朗的畫面效果,觀者可以想見董希文在經歷了家庭和工作雙重困擾時的剛毅態(tài)度,面對寬舒的自然,他的心靈感到撫慰。
董的另一幅作品《喜馬拉雅山頌》更具一番意味,真實地反映出他對西藏非一般的感情。他的學生劉秉江對此畫做了如下回憶:“董先生凝視這畫稿說了許多話。但是只有一句我記得最牢:‘我的感情始終是與這樣的情調相通的’。”喜馬拉雅山下清澈的雅魯藏布江,草原上成群的藏羊似在聆聽笛聲,每只羊都有著黃色的眸子,是那么明亮,整幅畫面顯得如此靜謐,只有那藏民的笛聲悠揚。董希文在藝術中融入了他深邃的情感,真實的表現卻在動靜中充滿了浪漫主義色彩。藏區(qū)那自然與人文天然親近的關系,令他動容。
觀者能從董希文的風景畫作品中體會到他超越敘事性的個人狀態(tài),以及他對民族情韻的捕捉。他在真切的自然景觀和平凡的現實生活中發(fā)掘自我情感,入藏期間的多幅作品皆能體現出他的“寄情”意圖。這些作品能促使我們思考新的繪畫語言與傳統繪畫精神之間的關聯性,更令人感受到自然風景畫帶給觀者精神上的感受力度。這樣的作品能體現出早期新中國藝術家們對畫作刻苦鉆研的精神品質,和他們勇于承擔時代要求的決心與魄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