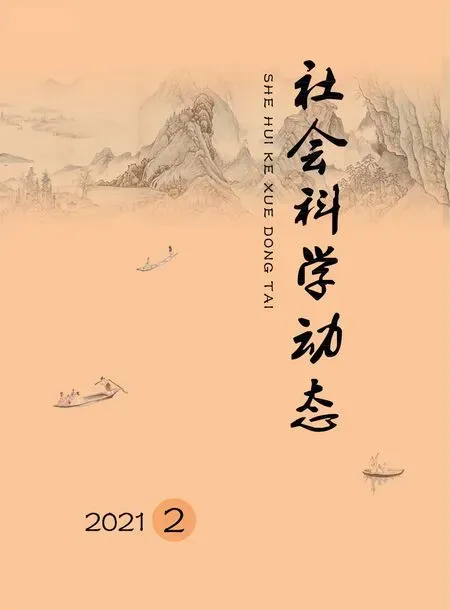中國母親文化建構70年回眸
——以邊沁古典功利主義理論為視角
馮 林
母親文化建構①是家庭發展任務完成的歷史起點和邏輯終點,其建構過程是人力資源培育和社會價值孕育過程。杰里米·邊沁的古典功利主義強調:人類最重要的特質是感受快樂(即善,應被追求并達到最大化) 與痛苦(惡,應被減少至最小化) 的能力,立法的過程應該且必須配合“善”的實現。法的效用應當是創造某些善、滿足、幸福或利益,同時又能避免或減少痛苦、災禍或損害。影響母親文化建構效用的四個重要變量——自由、財產、安全和反抗壓迫,與新中國法治體系的發展變化密切相關,在70年來呈顯“V”型曲線變化。
一、自由水平影響母親文化建構成果和善
70 多年來,中國母親的自由指數不斷變化,這主要是因為新中國立法之中的“善”:旨在為全體社會成員提供富裕和安全,力爭減少不平等的立法。其自由水平與母親文化建構績效呈正相關,我們具體可從婚姻自由、生育自由、遷徙自由、就業自由四個維度來予以考量。
(一) 婚姻自由提升家庭幸福指數
1950年《婚姻法》的頒布實施,不僅是中國傳統婚姻家庭制度的深刻革命,同時也是一場涉及個人生活、社會秩序乃至國家制度安排的重大社會變革,更是中國社會婦女人權發展史上的一座里程碑。《婚姻法》強調中國公民男女平等、婚姻自由受到黨和政府高度重視。1954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出臺,婚姻自由、一夫一妻制及其相關的權利、義務成為明確規定。中國女性自此遠離買賣婚姻、包辦婚姻、一夫多妻制的侵權,大幅提升了女性的生活滿意度,使得母親文化建構具有了良好的起點。婚姻自由的提升過程,與新中國政權權威產生、維持、加強的過程同步。婚姻自由具體表現在四個方面:結婚自由、不結婚自由、一夫一妻自由、離婚自由。
結婚自由提升人格資本。結婚自由是新中國公民的權利之一,“中國婦女運動從階級解放走向社會解放,1950年新的《婚姻法》推行并開始產生廣泛影響,帶來了婦女婚姻家庭的巨大變化”②。法律“禁止破壞婚姻自由”,“禁止包辦、買賣婚姻和其他干涉婚姻自由的行為”等,成為引導性的標準和評價所有行為的基礎。或者說,結婚自由成為女性婚姻行為的基本標準,使其做母親、擔母責、完成家庭發展任務時具有獨立人格,進而成為自己核心家庭生活的主導者、配偶的積極合作者,由此提升了母親文化建構的人格資本。
不結婚自由保障人格獨立。新中國成之后,由于憲法法律主張、政治社會推動,舊的婚姻陋習被深度沖刷干凈,婦女在公有制語境之下最大限度地參與了社會生產勞動,很多女性得以經濟獨立,因此有權決定自己是否結婚,這使得與婚姻相關的人權判斷能夠產生、持有和表達,而且強調任何社會組織、個人不得干涉。當時女性不結婚有兩種情況:其一,未婚女性是否結婚由自己做主,即女性有做妻子、做母親的自由,也有不做妻子、不做母親的自由,除了法律賦權之外,婦女不結婚自由的關鍵變量是公有制體制下其相對的經濟獨立;其二,喪偶母親是否再婚可以自己做主,喪偶后選擇不再婚的母親,可以對抗來自家庭成員、家族成員的侵權,而解放前的寡婦則很可能被婆家人當作財產賣掉。
一夫一妻制自由捍衛人格尊嚴。早在辛亥革命時期,1912年南京臨時政府頒布的《中華民國臨時約法》就規定了實行一夫一妻制,但實際上一夫多妻制依然在當時的中國社會大行其道。1950年《婚姻法》的頒布,才真正兌現一夫一妻制度。這使得大部分的母親能更加充分地支配自己的收入、占有和使用家庭的資源,排他性地擁有配偶(情感、身體、時間、資源),進一步提高了家庭任務完成效率。
離婚自由保障婚姻質量。離婚自由是度量婚姻質量的重要指標之一。新中國的女性離婚自由度也是變量,可分為主觀自由、客觀自由兩維,不同時空自由度不同,根由是政治自由、經濟自由的水平不同,法律對婚姻當事人權利的保護程度不同。主觀自由,又表現為過錯離婚和無過錯離婚兩個時期。在過錯離婚時期,必須是母親或其配偶一方、或者婚姻當事人雙方具有過錯行為時方可離婚。在無過錯離婚時期,夫婦可在婚姻中沒有明確過錯行為,只是感情破裂時即可申請離婚。《婚姻法》中即確立無過錯離婚。比較而言,過錯離婚可能經過長期情感折磨、心理重負,往往嚴重影響母子(女) 身心健康、家庭發展任務完成效率。無過錯離婚則相對地節約了母親的離婚成本。從過錯離婚到無過錯離婚,得益于立法的善、對人權的尊重。客觀自由維度上,存在離婚必須經過夫妻雙方各自所屬組織的同意、不經過對方同意、不經過各自所屬組織同意且可協議離婚三個階段。從第一階段至第三階段,離婚自由度逐漸提高,離婚成本逐漸降低,相應增加了母親文化建構的投入,增加了母親的快樂總量,減少了母親痛苦總量,彰顯出制度理性與人權水準。
(二) 生育自由提升下一代培養質量
新中國的母親生育自由有兩種特征,即技術性生育自由、法律性生育自由。生育自由的正價值是生育率得到控制、家庭規模減小、子女受教育程度提高、母親勞動力參與率增加、家庭收入提高、家庭發展任務完成效率提高。母親的社會經濟地位提升與生育控制密切相關。法規強制性計劃生育,為母親帶來最大福祉,而那些社會經濟地位較高、文化資本較高的母親由此得到的福祉最多③。
技術性生育自由指向少生優育。技術性生育自由指避孕技術在中國社會的普及。避孕技術使用大體分為三個時期:制度引導—少數人主動使用期、制度引導—多數人被動使用期、制度引導—多數人主動使用期。新中國的女性能夠享有技術性避孕自由,得益于法律法規的善,即將計劃生育、優生優育、生活質量相聯系。母親由此影響著生育率控制快樂的強度、持久性、純度,并預期了控制生育率帶來的經濟價值。具體而言:制度引導—少數人使用期,即控制生育率的技術、社會和意識形態對母親或其配偶施加影響初期,城鄉母親既可免費實施計劃生育手術,免費領取避孕工具,又可因此受到獎勵,這一時期避孕技術的先鋒使用者,都是人格相對獨立的母親;制度引導—多數人被動使用期,法律法規將計劃生育作為國策,符合條件的育齡婦女實行計劃生育常態化、制度化,開啟了獨生子女時代、農村二孩時代,優生優育帶來人口素質整體大幅提高,母親勞動力市場參與率攀升,家庭收入水平、生活質量迅速提升,與生理相關的需求(新陳代謝—維生系統、繁殖—親屬關系、舒適—住房、安全—防衛、運動—活動、成長—培訓、健康—保健等) 逐漸得到滿足;制度引導—多數人自覺使用期,生育率控制制度已內化為公民的內在需求,進入家庭策略,只生育一孩成為大多數中國母親的內在要求。現在即使政府引導二孩生育,絕大多數母親仍然選擇只生一胎,此時與計劃生育相關的法規既是目標又是行為,從而創造了結果的善④。
法律性生育自由帶來人口紅利。法律性生育自由是指通過人口政策進行計劃生育,母親可借法律強力主導節育,而不因宗教、習俗、家規脅迫無法控制自己的生育率。1982年9月,計劃生育被定為國策,同年12月,計劃生育被寫入憲法。中國母親整體上告別多子女時代,開始逐步建構中國特色的母親生育幸福/快樂函數,免受了“母親懲罰”。母親懲罰指由于母親身份而導致工作中斷、收入中斷或者降低的問題。計生政策對所有中國母親都是相同的、確定的、可操作的,這提高了每一個家庭、整個社會的幸福感安全感,體現了國家意志對公民個體與社會結構的態度和假設。《憲法》第25條、第49 條,《婚姻法》以及2017年國務院印發的《國家人口發展規劃(2016—2030)》,都反復強調計劃生育。其結果是,獨生子女的養育投資更多,進而創造了更多家庭資本疊加優勢,并能適時跟進和促進國家人口、經濟、社會、資源、環境的協調可持續發展,使得人口紅利惠及每一個中國母親。可以說,計生法規體現了中國立法水平、行政效率,保障了農業的、低收入的、人口最多的中國的母親和兒童的發展權。當然,不可否認的是,邊緣群體內文化資本較少的母親非理性生育現象仍然存在⑤。
(三) 遷徙自由嵌套發展權利
遷徙自由是世界絕大多數國家憲法都有規定的一項基本人權,例如日本憲法、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判例、聯合國的《公民權力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等都有相關規定。1954年至今,中國的法律沒有規定自由遷徙,農民母親的低社會經濟地位、低人力資本⑥相應被強制固化,城鄉二元制戶口曾長期固化公民的終身、世代身份,并通過憲法列定嚴格的等級制度,將不平等法律化、政治化、結構化、公開化。這是政治建構時的明確經濟議程⑦。中國城鄉母親的文化資本有三種鴻溝:文化資本具體化狀態(精神和身體的長期配置,比如處理問題的特定方式) 差距、文化資本物化狀態(通常可以轉化為經濟資本的文化對象) 差距、文化資本制度化國家(擁有社會認可的證書,如學位) 差距。
(四) 就業自由影響勞動報酬
70年來,中國就業可分為非自由就業、自由就業兩個階段。
計劃經濟時期,人口就業主要由國家計劃安排,通過公民的出生地、居所地、父母職業、戶口四個變量被強制規定。母親就業常與原生家庭的社會經濟地位緊密關聯而具有地域性、先天性、階層性、連帶性,根本變量是中國就業的政治化、憲法化。首先是地域性,母親出生何地,終其一生往往于該地就業。考量結婚變量,鄉村母親遷徙范圍多在一縣之內,多數在一鄉一村之內,城鎮母親則多在一城鎮之內。其決定因素是二元制戶口。母親就業地域的固化嚴重制約中低階層家庭的資源配置效率、生活質量提高,限制了下一代的發展空間,客觀上造成地域不平等和職業歧視,甚至使貧困、歧視代際傳遞。而且母親的居住環境在營養結果方面發揮重要作用:農村家庭成員發育遲緩的發生率始終高于城市。赤貧和低社會經濟地位直接帶來計劃經濟時期農村母親及其子女的高權力距離:權力不平等、地位和級別被他們視作“自然的”現象,認為這些差異應該得到承認和強調。其次是先天性。母親的職業在其出生前已基本確定——母親是農民,其子女基本上仍是農民,母親是工人身份,其子女往往仍是工人,等等。高考可以改變低位階青年人的命運,但一度被長時間按下暫停鍵。而全民所有制、集體所有制等非農體制內職員的職業,在計劃經濟時期可由子女接班而將收入水平、工作環境、社會身份、社會福利,以及由此構成的政治歧視、職業歧視、收入差距在代際傳遞。再次是階層性。70年來中國階層分野顯著,原生家庭成了早期法規形塑公民社會和經濟關系的關鍵場所,占中國人口總量82.1—87.81%的農村人口痛苦總量增值大于快樂總量增值。改革開放后,城鄉母親均可不斷追求更高勞動報酬的職業,從而打通了階層之間的壁壘。此外是連帶性。母親就業的連帶性集中表現為越軌與就業的連帶。母親越軌與就業的關系分計劃經濟階段、勞動力市場階段。如在計劃經濟消極連帶階段,被打成右派的母親會受到政治懲罰,是垂直向下社會流動的。一種是由高聲望職位被強置于低聲望職位,比如由教授被將降級為掃廁所的;另一種是由優勢地域被強置移動到邊緣地區,比如從大城市被貶至中小城鎮參加體力勞動,或從城鎮被遣返回邊遠的農村老家。這種垂直向下流動直接降低了母親的社會經濟地位,導致子女自我意識、自我形象建構受到重創,比如子女被剝奪上大學的權利等。
自由就業時期具體包括:
勞動力市場化自由。改革開放后,為追逐更高勞動報酬而遷徙,成為母親生活常態,主要表現在終生就業自由、階段性就業自由、兼職自由三個層面。終生就業自由是母親一生的就業都是自由的。階段性就業自由是母親可以根據家庭生命周期適時改變職業、居所、社會經濟地位。兼職自由是母親可在同一時期從事兩種甚至兩種以上職業。
就業去家庭化自由。新中國成立之后,黨和政府提倡男女平等,保護女權。由于經濟獨立、人格獨立,母親不再從屬于父權、夫權,不再依附于家庭,而是可以自主參與勞動力市場。去家長制自由,是母親通過接受教育獲得勞動力市場所需專門技能、能參與勞動力市場自由擇業,從而擺脫家長的控制。去夫權制自由,是隨著意識形態更新、生產資料公有制確立、產業結構變更、義務教育普及等,母親職業選擇已不再受其配偶所鉗制。去幼兒照護自由,則是指中國母親的生育率變化經歷四階段——自然生育時期、計劃生育時期、獨生子女時期、二孩政策時期,四個階段對應著四種生育政策、四種公民權,使中國母親照護幼兒和有酬工作日益兼容。
去雇主自由。隨著我國勞動力市場的充分發育,女性受教育程度的整體提高使其就業去雇主自由成為可能,而母親作為具有獨立人格尊嚴的人力資源,會不斷選擇雇主和從事更高勞動報酬的工作。這可從四個維度來考量。其一,去鄉村管理者自由。鄉村母親不再仰賴村干部計劃經濟下的“恩賜”,可自主選擇去全國各地勞動力市場競爭就業,甚至去高收入國家營商。其二,去公有制雇主自由。市場經濟語境下中國法律法規表達出更多正義和經濟效率,母親可自由辭掉公有制雇主而尋找更理想的工作。其三,去私有制雇主的自由。在法律賦權之下,母親通過勞動力市場淘汰不公平甚至侵權的私人雇主。其四,去家族雇主自由。母親對勞動力市場的參與對抗了來自家族、家庭就業的剝奪和侵權。四種去雇主自由,是母親在各自家庭遺產和當代生活條件的交叉點上,基于各自的能力方法與社會、市場進行的身份談判⑧,而這種談判直接影響到其子女的身份和歸屬感的預設。⑨
二、財富水平影響母親文化建構質量和滿意度
新中國母親文化建構在財產上的表現分為兩階段:一是無私有財產或者有極少私人物品時期;二是憲法保護私有財產時期。第二個階段的滿意度、幸福感明顯高于第一個階段。
(一) 無(極少有) 財產則無(極少有) 人格和自由
改革開放之前,母親無私有財產或者少有財產。母親文化建構表現為層內經濟資本均衡、層間人格資本波動兩種特征。
層內經濟資本相對均衡。母親沒有或者極少有私人財產,在各自經濟共同體內經濟社會地位大體平等,這是社會主義國家的重要特征之一。由于不依附于特定私有生產資料,同一階層內比如農民階層母親個體在財產維度下達到較高平等,建構母親文化的經濟資本均衡。
層間人格資本波動。在幾乎沒有私有財產的情況下,母親的人格資本,由于外部政治環境的影響出現三種情況:增值、不變、貶值,“直接影響許多母親經濟行為和社會行為的提前計劃”⑩。如,在“窮光榮”年代,以前低收入階層的母親,因屬“人民”,其人格資本、社會資本得到提升,可產生獲得更多收入、更高福利、更好崗位的預期,比如“貧下中農”身份的母親有更多入黨、提干、招工進城的機會,以及不被社會隔離、政治排斥的預設,其子女因此“根紅苗正”。作為以前中等收入階級的母親,在此階段的人格資本基本上未發生較大變化,能夠較有效地應對環境壓力。這一階段,那些在新中國建立之前屬于高收入階級、精英階層家庭成員的母親,尤其是其中的高文化資本者反而可能受到政治排斥、社會隔離,導致其人格資本的貶值。
(二) 有私有財產則有人格有自由
改革開放后,母親的收入、私有財產不斷增加,保護私有財產被寫入憲法,市場經濟逐漸繁榮,GDP 上升,人均GDP 提高,家庭收入水平增長,養育孩子的投入增加。
經濟資本較快積累。母親人均GDP 的上升得益于中國市場經濟的繁榮、對勞動力市場的廣泛參與。收入增加解決的不僅是母子(女) 的溫飽問題,而且有了更多的獲得感幸福感。
社會資本迅速聚集。隨著九年制義務教育和互聯網自媒體的普及,女性整體受教育程度提高,母親勞動力市場的參與穩定且提高,跨地域就業率不斷提高。社會資本迅速積累聚集,遠超各自生活、就業的地理邊界,進一步增加了其營商機會。各種社交媒體跨地域跨階層深入、廣泛的存在,幾乎涵蓋了所有地域,傳播的點與點之間處于完全平等狀態,不同區域、階層的人可能由陌生人變為線上的熟人、親密朋友,進一步擴大了母親的社會資本。
母親的社會資本按照時間分為婚前獲得的、婚后獲得的、社會配置的三類。婚前獲得的社會資本包括母親原生家庭擁有的、母親自致的兩種。母親原生家庭的社會資本是母親的父母、祖父母、外祖父母、兄弟姐妹等直系或者旁系親屬擁有的、且可為母親利用的社會資本。改革開放前農村女性被政治、經濟、社會隔離、性別歧視,原生家庭社會資本較城鎮女性的經濟價值要小得多,比如農村母親的金融機會要遠低于城市母親,因為其直系親屬基本上都被束縛在土地上。婚前自致社會資本,是通過母親自我努力獲得,主要通過交換獲得,包括友誼、勞動、情感、精力、時間投入獲得的社會資本。自致社會資本量通常與其人格資本量成正比,受法律、居所地、文化資本、經濟資本等變量影響。婚后社會資本,包括母親自己取得和通過婚姻存續所得兩個方面。自我取得社會資本,是母親婚后通過自己交換所得,包括新人際關系的建立、舊人際關系的加強等。通過婚姻得到的社會資本,是母親從配偶及配偶原生家庭、旁系親屬方面中獲得的社會資本。社會配置的社會資本,是通過法律法規、公權力、公共福利系統專門配置的社會資源,包括相關福利、政策、法律、組織等,比如鄉村托兒機構、婦女免費體檢、免費避孕工具、免費心理咨詢等這些福利一旦被母親對其進行有效利用,就可轉換為其社會資本。
文化資本逐漸豐厚。新中國帶來的革命性變化的表現之一是母親的文化資本大幅提升。文化資本有三種形式:具體化的狀態(精神和身體的長期配置,比如處理問題的特定方式)、物化的狀態(通常可以轉化為經濟資本的文化對象)、制度化的國家(擁有社會認可的證書,如學位)。我們主要集中在具體化的狀態和制度化的國家。?從具體化形態來看,母親的文化資本從獲得方式上分為社會配置、母親自致、家庭成員獲得三種。
社會配置的文化資本包括社會配置、可轉化為經濟資本的文化對象即物化狀態的文化資本以及擁有社會認可的證書的制度化的國家文化資本兩種形態,直接配置了母親文化建構的資源。區域配置差距直接構成母親文化建構的環境不平等和孩子教育效率的不平等,以至于當母親有機會獲得足夠的城市化成本時,總是急不可待地從農村遷徙城市,從小城市遷徙大城市,或者從中國遷徙到高收入國家。自致文化資本是母親精神和身體長期配置的、處理問題的特定方式即具體化的狀態。如母親從夫家的、配偶方面獲得的文化資本越多,自己的家庭發展任務完成效率往往越高,對抗環境壓力的能力越強,家庭的組織和互動效率也較高。另外,母親自己通過受教育學習獲得的文化資本,通過對高等教育的融入有了大幅提高。從互聯網技術與文化資本之間的關系來考量,互聯網和自媒體是當下母親獲得虛擬和現實文化資本的最主要工具、路徑,這種技術使用已經打破了城鄉壁壘。有數據顯示,2015 至2017年,中國手機擁有者比例由92.48%上升至104.58%,互聯網接入技術由50.3%上升至54.3%。子女的文化資本,是子女所擁有且可以為母親所利用的文化資本。文化資本由子女向母親傳遞的效度和向度分為三種情況:當母親和子女的文化資本水平相等時,這種傳遞是雙向的;當母親的文化資本水平高于子女時,傳遞的方向主要由母親指向子女;當母親的文化資本水平低于子女時,主要由子女指向母親即反哺。新中國建立至改革開放前,這種傳遞主要由母親指向未成年子女。改革開放以后主要由成年子女指向母親,對于農村母親尤其如此。
三、安全水平影響母親文化建構基礎和體量
安全主要通過人身安全、政治安全、社會安全、經濟安全、生育安全五個維度來考量。母親安全的系數影響著母親文化建構基礎和體量。70年來,中國母親的安全系數大體成“V”型曲線變化。
(一) 母親人身安全嵌套下一代安全感
母親的人身安全可以從生命、健康、行動自由、人格、名譽、住宅六個維度來考量。70年來母親的六個指標呈現出“V”型曲線變化。改革開放之前,中國人趕走外國侵略者,結束外戰內戰,有力地避免了戰爭對婦女兒童的殺戮、搶掠,但十年政治動蕩可能影響了部分母親的人身安全。改革開放至今,食物充足、行動自由、人格獨立、住宅安全、身心健康、人權入憲讓母親安全系數不斷提高,對養育效率發生了積極溢出。
(二) 母親政治安全決定新生代獲得感
母親的政治安全指數即母親在政治方面免于內外各種因素侵害和威脅的客觀狀態指標,在70年來呈“V”型曲線變化。改革開放前,政府通過行政命令而不是法律法規令母親的政治安全指數(政治意識、政治需要、政治內容、政治活動等) 變動。決定母親命運的標準是政治影響,甚至是家長制領袖的個人意志、個人行為和個人預設、個人偏好。改革開放至今是母親政治安全系數全面提升時期,社會整體開始逐步關注城鄉居民的獲得感、幸福感。
(三) 母親社會安全反射政府行政績效
母親的社會安全包括與其相關的社會治安、交通安全、生活安全和生產安全。70年來,母親的社會安全系數成倒“V”型曲線。在新中國成立后的一段時期內,社會治安水平不斷提高,犯罪率較低,交通事故偏低。公有制和計劃經濟使非農公有制體制內的母親生活安全、生產安全水平逐步提高。而十年動亂期間則急劇降低了社會安全系數。市場經濟繁榮、經濟自由系數提高之后,經濟犯罪率逐步提高,各級公務員中貪腐現象嚴重,火災發生率、工傷事故死亡率、交通事故與刑事案件開始上升。整體而言,安全社會環境關鍵取決于黨和政府的危機決策支持系統與政治意志的方向。?這實際上是社會開放、經濟繁榮、GDP 迅速提高的結果。
(四) 母親經濟安全保障家庭任務完成效率
母親經濟安全是指母親能夠獲得穩定收入或者其他資源,以確保目前及可預見的將來能夠維持一定生活標準,包括潛在的持續償付能力、就業安全或者工作安全、未來現金流的可預測性等金融安全。母親的收入水平、就業安全能夠測量其未成年子女的經濟安全。50 歲以上母親的經濟安全取決于其退休金、存款、收入、就業、醫療保險、社會安全福利,中國母親的經濟安全涉及個體未來正面和負面的事件的實際可能組合,都對其所涉階段生存質量密切相關。?
改革開放前,相對于城鎮母親,占中國母親群體絕大多數的鄉村母親的經濟極不安全,尤其50歲以上鄉村母親在此期間幾乎都是四無人口:無退休金、無存款、無現金流、無公費醫療,有農業卻入不敷出、營養不良,在養育未成年子女時期完成家庭任務的效率相對低下。在養老時則因子女同樣貧困而無就醫能力,以至于晚景慘淡。這一時期,城鎮公有制體制內就業母親經濟安全系數相對較高,有“鐵飯碗”和養老金、公費醫療。改革開放之后,母親經濟安全指數整體上不斷提高,鄉村50歲以上母親雖然仍無退休金,但逐漸有了一些存款、醫療保險和社會福利。與此同時,其子女的整體收入水平則相對更高。這一時期城鎮高收入母親的經濟安全指標提升較快。
(五) 生育安全提升母子(女) 健康水平
70年來,中國母親的生育能力安全、生育過程安全、生育健康安全和生育保障安全水平逐步提高,總體呈現出逐步上升的變化,這主要得益于公有制、公費醫療和義務教育廣泛、深入、持續展開,尤其是改革開放40 多年來,隨著計劃生育、獨生子女政策的積極推進,女性的生育安全進一步得到家庭和社會的保障。
四、反抗壓迫水平關涉母親文化建構風險規避效率
農業社會的性別歧視和性別壓迫曾對中國母親產生過深刻的破壞性影響:她們的真實經濟身份、主體性被忽略。對于母親文化建構而言,反抗壓迫包括反抗政治壓迫、反抗社會壓迫、反抗家長制壓迫、反抗夫權壓迫、反抗成年子女壓迫五個維度。
(一) 反抗政治壓迫的可能和現實增加
母親反抗政治壓迫,指在遭受政治侵權時能捍衛自己的人權。在過去70年中,男女平等被法律列舉并強調,中國女性比歷史上任何時期都擁有更多的參政權。但十年動亂期間,當社會以政治價值作為考量公民行為的標準時,大量出身于高文化資本、高社會資本家庭的母親的行為一定程度上受到政治打壓、社會隔離,而鄉村母親則遭二元制戶口侵權而無力抗爭。改革開放之后,城鄉二元制戶口逐漸淡化,農村女性也可通過市場參與,不斷提升社會經濟地位,甚至逐步增加政治影響力,有機會走上參政議政的大舞臺。
(二) 反抗社會壓迫的情感與力量均衡
70年來,母親生產、消費、政治、教育行為都是社會主義社會化的結果,對抗來自社會侵權的力度、向度、頻度、效度具有濃烈的中國特色。計劃經濟時期,母親的階級地位固化,財富、聲望、權利極不平等,子女享受的政治、教育、環境、經濟、保健機會差異巨大。對母親的結構性社會壓迫主要表現為鄉村母親世代為社會制度所桎梏,一直與貧困、恐懼相伴,通過巨大工農業剪刀差被剝奪,而且將被壓迫看成是理所當然。城鎮公有制內就業母親的社會壓迫,則與政治強制關聯的物質匱乏和資源低效配置相關。改革開放后,一方面結構性的社會壓迫因為法制建設、經濟自由、階級對抗的消除逐步得以解決,另一方面卻又造成新的社會壓迫,以致出現了70年來罕見的女性反抗社會壓迫:通過自媒體、互聯網等進行的公開揭露和聲討,如女權主義運動旨在人類成員之間共享權利,以便進一步提升幸福感。
(三) 反抗家長制壓迫關照打開能力方式
70年來中國女性反抗家長制壓迫成績斐然,這首先得益于政治強力對傳統家長制基礎的瓦解。由于女性生存不再從屬于家長所有的私人財產,而是更多依賴于公有制生產資料、市場經濟,女權主義的新唯物主義以及母親文化觀點通過確定各種母親與情感力量之間的關系而認可了母親文化、母親和技術的能力作用,認識到母親主體獨立的情感力量對于打開或關閉自身以及子女能力的方式至關重要。
(四) 反抗夫權壓迫增加母親文化建構主體性
新中國以來,女性反抗夫權一直比較成功,根本原因是憲法法律對男女平等的強調、政治運動對傳統夫權的摧毀和威懾。但相對于配偶,女性往往投入更多時間精力在家務勞動以及對子女的無酬照護。傳統的工農業更多依賴于重體力勞動投入,母親直接經濟收入往往低于配偶,致使夫權現象廣泛持續存在。但獨生子女的法律政策建構和社會化、生活化,讓夫權的生存空間大為縮減:獨生子女較之于多子女家庭出生者的人格往往更具自由、平等、獨立和民主意識,對正義的期望也相對更高。伴隨個人受教育程度、收入水平上升和經濟獨立的離婚率、銀行存款女性戶主數及房屋女性戶主的不斷攀升,尤其是母親的經濟獨立,使得母親文化建構的效率更高。
(五) 對抗子女侵權保護母親養老資源
母親對抗成年子女侵權表現為兩個形態各異的時期,一是改革開放之前,二是改革開放至今,都體現了低文化資本的母親在社會政治和心理現實之間的身份危機。改革開放之前,不僅居住于城鄉母親對抗成年子女的狀況不同,即使同類性質地區,公有體制內外母親對抗成年子女壓迫的方式也各異。這個階段鄉村母親畢生務農而入不敷出,無存款、無醫保、無現金流,因此無養老金,一旦年老重疾,即成為低收入成年子女的生活重負,常常受冷遇甚至虐待,財產和人格尊嚴受侵。這一時期城鎮公有制內就業的母親,擁有公費醫療、退休金等,有政府規定的節假日休息權利和相應的社會福利,身心往往較農村母親更為健康,相對更具有自我養老能力,無需成年子女經濟支持,因而對抗成年子女侵權效率較高。而其子女往往因其母親文化建構遠較鄉村同齡人優越,因而在勞動力市場上表現出較強的競爭力和較多經濟機會,收入水平較高,對老年母親的經濟壓迫性相對較低。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母親的人均GDP 普遍上升,老年母親的子女往往比自己收入高,一般與母親分開居住,對母親的侵權行為大為降低。而大多數母親因參與勞動力市場和市場經濟發展,開始具有一定養老儲備。尤其是近些年農村母親逐步受益于國家社保制度的人口全覆蓋,既減少了養老對子女的依賴,也減少了子女侵權行為。
五、中國母親文化建構展望
第一,以法律為根本,建構兼顧公平正義、經濟效率的法律體系。無論憲法、法律還是法規,在制定過程中應該、而且必須配合“善”的實現:所有的立法都應該旨在為社會成員提供富裕和安全,力爭減少不平等。相關領域的學者應進一步研究與母親文化建構相關的技術、社會、意識形態問題,尤其是中國鄉村母親的家庭任務完成問題。立法者應在專業學術成果的基礎上進行立法,如將遷徙自由入憲、徹底廢除城鄉二元制戶口等。執政主體應基于相應的法律基礎,配置可操作性的政策體系,以提高母親家庭任務的完成效率。
第二,以母親為主體,增加能力方法,提升機會、財富、聲望、權力水平。應當不斷提升母子(女) 的社會化和社會互動水平即能力水平,充分行使法律法規賦予的各項權利,以獲得更多經濟機會。社會階層存在是必然的,由此可能產生剝削、無序、動蕩、情感疏遠與社會不滿,但市場經濟語境下層與層之間是開放的。母親只有成功社會化,將家庭發展任務與國家發展任務緊密結合,充分參與市場經濟、勞動力市場,不斷追逐更高的勞動工作報酬,獲得更多財富、聲望和權力,才能提升家庭任務完成效率。
第三,以公權力為客體,加強制度配套,推進母親文化建構水平。政府管理者應當充分評估母親文化建構的基礎性、戰略性、重要性——母親文化建構是人力資源和社會價值同構,涉及社會所有成員生存質量的保持和提升。公權力應以法律配置,優化母親文化建構必備的政治、經濟、社會環境,比如保障勞動力市場的充分發育和持續繁榮,確保母親遷徙自由、就業自由。優先配置與母親文化建構相關的基礎設施,尤其是農村地區的托兒機構,避免學齡前兒童的母親陷入育兒期貧困陷阱。正如社會學法學之父耶林所言,法律是最廣泛意義上的社會生活條件的集合,并由國家權力通過外部強制的手段保證實施。
第四,以配偶為聯盟,優化家庭策略,提升母親文化建構等級。社會應當對母親文化建構和文化價值予以不斷宣傳,以促使社會整體認知水平得以提升。女性應當使配偶充分認知到母親經濟社會地位對于家庭發展任務完成的基礎意義,以期獲得有效支持,使女性能有更多的資本(時間、精力、情感) 投入勞動力市場競爭。母親應當善于與配偶進行爭論和對抗,以確保自己經濟獨立、人格獨立、充分就業,不斷追逐更高勞動報酬。母親應當在配偶支持或者無阻遏的情況下獲得財富、聲望、權力的分配,以便在自己生命歷程中盡早、盡快地完成向上社會流動,因為已婚者普遍認為,配偶提供的支持是他們所獲得的社會支持中最重要的一種。?
注釋:
①馮林、關培蘭、王開敏:《大眾傳播、母親文化與行為空間的法理學建構》, 《法制與社會》 2015 第4期。
②鄧紅、王利娟:《1950年新〈婚姻法〉的推行及其影響》,《河北大學學報》 (哲學社會科學版) 2019年第4期。
③?Karaolan Deniz, Saraolu Dürdane Irin, Women’s Socioeconomic Status and Choice of Birth Control Method:An Investigation for the Case of Turkey, Journal of Biosocial Science, 2020, 4, pp.1-20.
④張萬洪、郭漪譯:《最新大不列顛法律讀本·法理學》,武漢大學出版社2014年版,第165頁。
⑤Kathryne M.Young, Katie R.Billings, Legal Consciousness and Cultural Capital, Law & Society Review, 2020,1, pp.7-32.
⑥ Sofia Vasilopoulou, Liisa Talving, Opportunity or Threat Public Attitudes Towards EU Freedom of Movement,Journal of European Public Policy, 2019, 26 (6), pp.805-823.
⑦J.C.Sharf, Equal Employment Versus Equal Opportunity: A Naked Political Agenda Covered by a Scientific Fig Leaf, Industrial and Organizational Psychology, 2011,4(4), pp.537-539.
⑧Jennifer Drummond Johansen, Sverre Varvin, Negotiating Identity at the Intersection of Family Legacy and Present Time Life Conditions: A Qualitative Exploration of Central Issues Connected to Identity and Belonging in the Lives of Children of Refugees, Journal of Adolescence, 2020,10(1), pp.1-9.
⑨ De Munck Jean, Human Rights and Capabilities:A Program for a Critical Sociology of Law, Critical Sociology, 2018, 44(6), pp.921-935.
⑩ Paul Anand, Ambra Poggi, Do Social Resources Matter Social Capital, Personality Traits, and the Ability to Plan Ahead, Kyklos, 2018, 71(3), pp.343-373.
?Stanislaw Drosio, Stanislaw Stanek, Building a Safe Society Environment: A Summary of Hybrid Approaches to Crisis Decision Support Systems, Journal of Decision Systems, 2018, 27(1), pp.181-190.
?Marek Kony, Maria Piotrowska, Assessment of Economic Security of Households Based on a Scenario Analysis, Economies, 2019, 8, pp.20-24.
?[美]魯道夫·F·韋爾德伯爾、凱瑟琳·S·韋爾德伯爾、迪安娜·D·塞爾諾:《傳播學》, 周黎明譯,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4年版,第93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