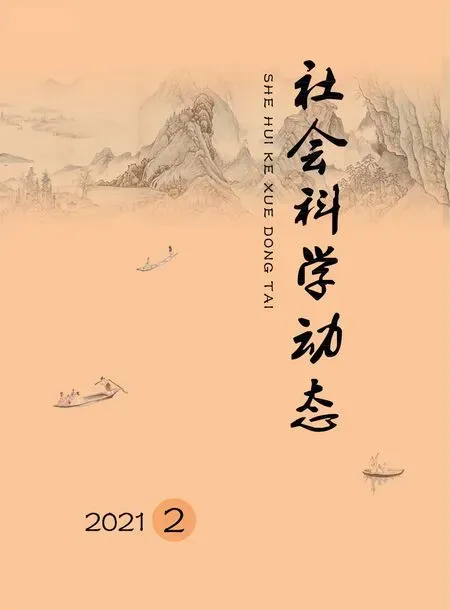敬重知識 從容治學
金德萬
第一,像敬重生命那樣敬重知識
如果我們將過去100年至今教育界學術界的人分為三代:“第一代”主要是那些教學發端于20世紀20—30年代的群體;“第二代”是指50—60年代的群體;“第三代”則是80—90年代的群體。在湖北省社會科學院,李達、朱劍農當然屬于第一代,夏振坤老和榮開明老是第二代,金清研究員和我應該都屬于第三代。事實也是這樣,我對榮老執弟子禮,只是未得親炙而已。
榮老那一代知識分子由于國際和國內環境的限制,雖然學術視野和學術成就整體上不及第一代,但他們承先啟后,與時俱進,在新的學科建設上同樣有開辟草萊、以啟山林的重大突破和貢獻。我院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學科建設,榮老和鄧劍秋一樣是有創建之功的。
榮老這一代學人有一個共同的特征敬重知識。我已喪失了讀書查筆記的能力,請諒解我不能一一地縷述榮老的科研業績。我要說的是榮老的學術方法。這個方法我稱為“概念話語歷史分析方法”(Discourse-historical Approach)。就是說在對理論經典的研讀中始終注重經典文本的實際和社會歷史的實際,強調將話語置于各種社會歷史背景中進行概念剖析和闡釋,以解讀經典語篇與政治實踐和社會意識之間的關系。概念話語歷史分析方法的關鍵是話語歷史分析與面向歷史真實語境緊密結合,而絕不是以文本分析、話語分析為學術包裝袋而回避或有意遮蔽歷史的內容和真相。學術方法是體現理論生命本質的。
榮老的每一篇文章都是應社會的需要而撰寫的,每一部著作都是思想理論指導群眾激勵發展的理性證明。面向真實、面向歷史、面向社會。榮老的這一學術方法是榮老學術生命“壽比南山”的體征,也是我長期閱讀榮老著作的體會。他像敬重生命一樣地敬重知識。
“先生之風,山高水長”,足以傳世。建議金清研究員可以與學科組珍生研究員商量設定一個榮老學術方法論的學科題目。
第二,意義在從容生活里顯現
70年學術生涯,90年人生歷程,榮老仍然健康地、穩定地前行。在社科院東西院兩邊的便道上,我們每天都能看見這位老人的身影,提著裝滿書籍和筆記的包袋。
有一天,榮老把四大卷新版馬恩全集交給我。“怎么拿得動喔?”“拿得動拿得動。”這位可敬的老人。觀念意識決定著每個個體的行為方式,存在決定意識,而價值取向則決定著每個個體特別有異于他人的偏好。
榮老之所以能夠像敬重生命那樣地敬重知識,是與其價值觀不無關聯的。
如果說經濟學家一般關注資源利用的效率,政治學家關注社會生活的公平,哲學家則關注公平和效率蘊含著價值的取向。榮老的價值取向是什么?我以為是從容,從容治學、從容處世、從容生活。這是敬重知識的必然,也是敬重生命的必然。
如果榮老沒有矢志不渝,艱苦備嘗地求知問學,怎么可能不疾不徐地把自己的學術人生過成了誠實的坦途?怎么可能不孜孜于名利、不計較榮辱褒貶,總是那樣優雅自在地把前行的每一步進取走成了詩?
榮老是平和的,幾乎不疾言厲色,但也有劍拔弩張、拍案而起的時候。那次榮老大聲對我說:“鄧小平理論不能丟!怎么能丟呢?”近十年前社會上出現一股逆流,要走邪路,否定黨的領導、否定鄧小平理論。榮老對我說的那句話,擲地金聲。
榮老將一位離休干部老知識分子平凡的人生意義在自己從容處世從容治學的經歷中顯現出來。“仁者壽”,我們常常恭賀老人福如東海,福是什么?福是人生的意義,在獨特的有價值的勞動生活方式里體現出來區別于一般性的價值意義。
榮老人生的價值意義在從容生活中顯現。我們是那樣向往,達到一定高度的人生境界,而且有大海那般遼闊的氣勢。